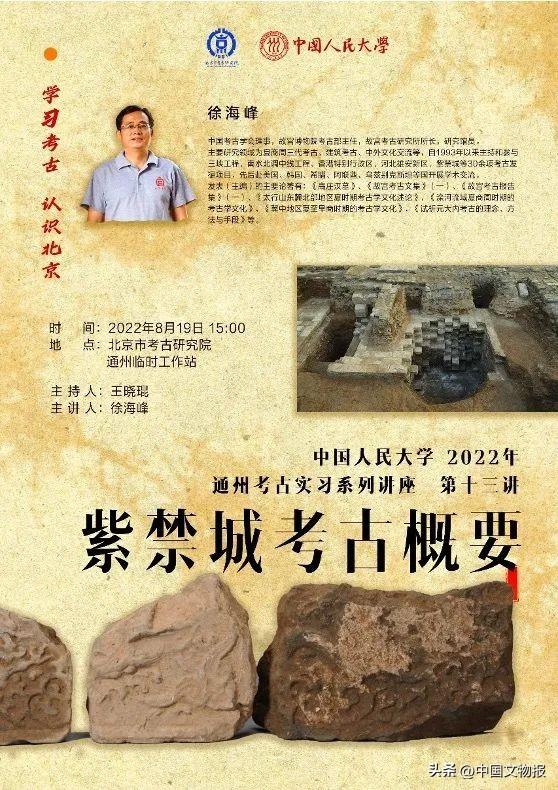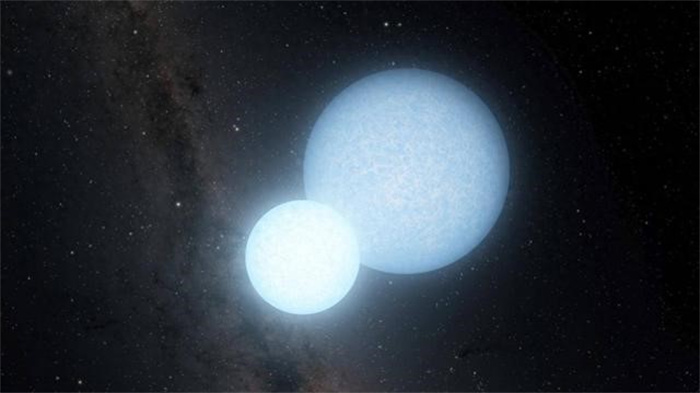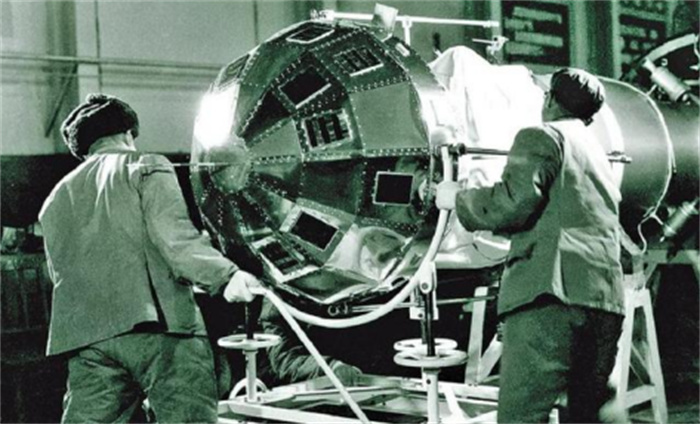令狐若明:20世纪以来的埃及学研究
埃及学是一门研究古代埃及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建筑和科技的综合性学科,它的诞生是以法国学者商博良1822年成功破译埃及象形文字为标志的。[1](P244) 这门近代新兴学科发展至今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但埃及学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对人类文明做出重大贡献是在20世纪以来逐渐取得的。
一、20世纪以来埃及学的重要成就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后,在埃及学研究规模较大的德国、美国、英国和法国都先后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埃及学家,他们在考古发掘、历史和语言文字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对埃及学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
20世纪初,在德国东方学会名义下,由博查德率领的德国考古队赴埃及进行一系列的调查与发掘活动。1912—1914年,他对埃及的阿玛尔那古代建筑遗址进行了发掘。1912年12月,博查德在清理古代雕塑家图特摩斯住宅里的专门作坊时,发现了著名的涅菲尔提提(古埃及第18王朝法老埃赫那吞的王后)石灰岩胸像(现藏于柏林博物馆)。[2](P55) 继博查德之后,英、美等国的考古工作者于20世纪30年代、90年代先后在这里进行了几个季节性的发掘,使古代埃及这座昙花一现的显赫城市展现出一幅颇为细致的生活图景。
美国的埃及学研究起步虽晚,但从20世纪初以来,发展十分迅速,越来越多的美国埃及学家直接参与埃及的考古发掘工作,赖斯纳就是他们当中最为杰出的一位。赖斯纳在埃及吉萨地区从事考古工作达40年之久,重视对发掘和记录系统的处理方法。1907—1909年间,他在吉萨勘察了平顶金字塔和孟考拉金字塔。1926年12月,他又发现了埃及第4王朝(约公元前2613—2494年)法老胡夫之母希泰费雷斯王后的陵墓,为研究古埃及文化丧葬习俗的演变提供了直接的材料。[3](P164) 赖斯纳曾先后任哈佛大学埃及学教授、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埃及馆馆长,被公认为美国考古事业的鼻祖。1920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埃及学家文洛克在靠近底比斯古城的戴尔·巴哈里进行发掘。他在埃及第11王朝(约公元前2033—1991年)贵族梅克特法官的陵墓中发现有正在劳作的佣人小雕像、船只及粮仓模型。[4](P3) 这一发现,从侧面记录了古代埃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场面。在美国埃及学研究领域,布雷斯特德也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1894年,他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教授埃及学;1905—1907年,曾领导赴埃及、苏丹的考古工作队,拓印了许多正逐渐消亡的古代铭文。1919年受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资助,筹建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在他指导下,该研究所于1895—1896调查了埃及和努比亚的古迹,从而开创了美国的埃及学。布雷斯特德将他所辑录的埃及象形文字铭文译成了英文,编辑成5卷本的《古代埃及文献》(1906—1907),为研究古代埃及史提供了基础性的资料。他根据古埃及文献资料撰写的通史性的《埃及史》(1905)流畅易懂,享有盛誉,至今仍为学者们所引用;他所撰写的《古埃及宗教与思想之发展》(1912)一书仍为专门领域中的开拓性著作。
20世纪初,对埃及考古学贡献最大的是英国埃及学家卡特。1922年11月,卡特在底比斯附近的王陵谷发现了埃及第18王朝法老图坦卡蒙的秘密陵墓,是当时埃及唯一未遭破坏、盗劫的王陵。在这个秘密陵墓的4间墓室里,发现有图坦卡蒙本人的木乃伊和大批精致的随葬物品:镶金的大小箱柜,雕镂精美的金床和靠椅,镶有宝石并包金的木制狮腿宝座,精致的雕像和壁画,包金战车,大小共3000余件。图坦卡蒙本人的木乃伊置于三重棺内,最内棺用纯金打制,次二层为贴金木椁,木乃伊的头部和肩部盖着一具面具,由镶嵌着天青石和绿松石的黄金制成。[5](P103),精工制成的面具复现了这位青年法老的英俊面容。图坦卡蒙木乃伊身上的裹布有大量珍宝和护符,已发现的各类宝石就有143件之多。[6](P218) 卡特花了10年功夫,才将堆在陵墓4间墓室的中的全部珍品登记、清理出来,后交由埃及博物馆收藏。图坦卡蒙陵墓的成功发掘,使公元前14世纪前后埃及法老的殡葬情况公之于世,这是20世纪20年代轰动世界的重大考古成果。
从20世纪初开始,来自欧洲各国的考古学家曾在靠近底比斯王陵谷的戴尔·美迪纳村落进行长期考察发掘。这个小村落是埃及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567—1085年)在王陵谷为建造法老陵墓的工匠们的居住地,始建于第18王朝法老图特摩斯一世当政时期。村落在建造500多年后被人遗弃,很快就被风沙掩埋起来。1922—1951年间,法国考古学家布吕耶尔在戴尔·美迪纳发现了街道、房屋以及工匠及其家人的坟墓。这个小村由大约70座错落有致、保存良好的房屋构成,房屋的周围环绕着围墙。在戴尔·美迪纳的一个垃圾坑里,布吕耶尔发现了数千块被当作方便廉价书写材料的石灰石或陶器碎片,上面载有村民日常生活的记录,已被证实为村民的信件、收据、工作记录、诉状、洗衣店里的单据等。[7](P73) 根据这些信息,埃及学家才有可能勾勒出清晰的古埃及人生活的图景。正是由于村落本身的完好无损、居民坟墓以及有关居民日常生活文字记录的存在,这三个因素的结合,才使得戴尔·美迪纳成为一处研究古代埃及普通人生活方式的重要的遗址。1939年,法国埃及学家蒙泰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塔尼斯发掘的王室墓葬,是20世纪30年代最富有成果的考古发现。塔尼斯城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东北部,是埃及第21王朝(约公元前1085—前945年)和第22王朝(约公元前945—前730年)诸法老修建的都城,这两个王朝在新王国倾覆后一直统治着北部埃及。1939年2月,蒙泰在清理神庙院墙时,发现了一口深井,井底与一座带有4间墓室的石砌陵墓连在一起。其中,在第21王朝法老普苏塞奈斯一世的墓室里,发现一口巨大的红色花岗岩石棺,外棺里面是一具木乃伊形状的黑色花岗岩套棺,套棺内还有一口银内棺,盛敛着业已腐烂的法老的木乃伊,脸上覆盖着金面具,遗体则由贵金属和珠宝制成的护身尸衣包裹。[8](P40) 蒙泰在塔尼斯发掘的王室墓地,随葬品虽不如图坦卡蒙墓丰富,但仍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它揭示了埃及第21王朝和第22王朝时期王室的丧葬习俗,为这两个没有太多资料留下的王朝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史料。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埃及史前文化遗址的发掘和古埃及文明起源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德国的容克,英国的布伦吞和卡顿—汤普逊先后对梅里姆达、法尤姆、巴达里、塔萨等遗址进行了发掘。英国埃及学家鲍姆伽特根据埃及史前考古发掘材料,出版了2卷本的重要著作《埃及史前文化》(1955,1960)。这些史前考古发掘材料的积累,为考古学家建立埃及前王朝文化序列提供了基础,把古埃及文明起源的年代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埃及的一切发掘活动都被迫停止了。战后,欧美各国在埃及的发掘活动逐渐得到恢复。大规模的国际协作对古代遗址进行拯救性的迁移和发掘,是战后埃及学发展的特点,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60年代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拯救努比亚遗址国际行动”。由于修建阿斯旺大水坝,洪水将淹没位于埃及和苏丹之间的一大片地区,(这一地区自古称为努比亚),直接威胁到沿岸的许多古代遗址,其中包括最著名的阿布辛拜勒神庙和菲莱神庙。于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埃及政府共同制定了一项使神庙遗址免遭淹没的庞大计划,由51个国家出资、22个国家派出工程师、考古学家和科学家参加了一场国际考古大会战。[9](P292) 大会战中最激动人心的场面是从阿布辛拜勒把两座大小神庙(大庙即埃及第19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岩窟庙,小庙是为其王后涅菲尔塔丽奉祀哈托尔女神所建)完整地移往较为安全的高地。当时采取的方法是将两座神庙切割成许多约重30吨的石块,迁移到200米外高于新水平面的一个安全地点,到了那里后又重新按原方位进行组合。1968年9月,两座神庙在新址落成。菲莱神庙位于尼罗河的一座小岛上,是一组相互呼应的寺庙群,其中的伊西丝神庙是希腊、罗马统治埃及时期最著名的朝觐圣地之一。同解决搬迁阿布辛拜勒神庙的方案一样,即采取切割方法,把神庙搬迁至500米外,与该岛走向相似,但高出水面数米的阿吉尔基亚岛上,重新组装复原。1979年8月,搬迁工程全部完成。至此,第一次通过国际间的共同努力,拯救古埃及文化遗址的庞大工程获得圆满成功,成为考古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20世纪80年代,现代科学技术开始被引进和运用到埃及学的研究中。1986年8月,法国建筑师多尔米庸和古瓦丹在胡夫大金字塔的王后走廊里,采用小孔探针技术,以寻觅胡夫隐秘的墓室。他们在王后走廊的西墙上钻了3个小孔,伸进装有袖珍照相机的内窥镜,拍摄墙壁后面的景象,结果发现里面堆满着晶莹的沙子。[10](P191) 探测工作虽然没有取得新的进展,但他们的工作实际上已为埃及学的研究开辟了一种新的门径。借用现代科学技术,考古学家可以进一步了解古埃及人的建筑设计。
20世纪90年代,埃及考古工作已不只局限于田野发掘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水下潜水考古领域。位于尼罗河三角洲最西边河口上的亚历山大里亚,是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32—前30年)统治时期的繁华国际大都市。公元前5世纪中叶,亚历山大海港内的王宫和建筑物毁于一系列的地震,沉没到东部海港水下。为了确定托勒密王官遗址的位置,设在巴黎的欧洲海底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水下考古部合作,从1992年起,开始绘制沉没在东部海港水下遗迹的地图。考古学家采用先进科学技术,通过GPS(地球测定系统)接收器,在探测出托勒密王宫的大体轮廓后,将所取得的数据合在一起绘制成地图,到1997年时亚历山大东部海港地图基本绘制完毕。[1](P275) 专家们确信已经掌握了托勒密王室区的准确位置,并完全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所著《地理学》中的描写相吻合。
上述新的研究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引进,为埃及学研究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根据,并有助于埃及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在语言文字和历史研究领域,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成就也十分显著。1924年,英国埃及学家冈恩在巴黎出版了《埃及语句法研究》一书,表明埃及语语法研究有了出色的进展。德国的斯皮格尔别格更是一位有突出贡献的文献编纂者,他先后出版了《科普特语指南》(1921)、《世俗体文字语法》(1925)和《劳埃布世俗体文字纸草》(1931)等著作。由德国埃及学大师埃尔曼和他的同事格拉波编纂的5卷本《埃及语词典》,于1926—1931年间问世。这部词典内容丰富,注释详尽,是20世纪初埃及语言学研究的巨大成果,至今仍是学习古代埃及语言文字的基本工具书。1927年英国埃及学家伽丁纳尔出版了《埃及语语法》,1950年再版,1957年第3版,是埃及学界一致公认的重要经典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版了一批有关古代埃及的重要历史著作和发掘报告。14卷本的《剑桥古代史》和8卷本的《非洲通史》中的有关内容,反映了国际埃及学界知名学者的共同研究成果。1947年英国埃及学家爱德华兹出版的《埃及金字塔》、1961年伽丁纳尔出版的《法老时代的埃及》,1979年大英博物馆埃及馆馆长詹姆斯出版的《古代埃及介绍》,都是很有影响的埃及学著作。英国考古学家肯普整理出版的5卷本《阿玛尔那报告》以及詹姆斯主编的《埃及发掘100年:1882—1982》也都是有相当学术价值的埃及考古学资料。
二、埃及民族考古学的成长
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埃及本国的考古事业长期被西方列强所控制,1952年埃及获得独立后,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其本国的民族考古学逐渐成长起来,并培养出了一批跻身世界学术之林的优秀埃及学家。
1955年,埃及考古学家马拉赫在清理胡夫大金字塔南侧附近的小沙丘时,发现了两个石坑。当时只对第一石坑进行了发掘。在这个石坑内发现一条大木船的完整船体部件,共1224块。[12](P104) 埃及文物复修专家经数年努力后,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恢复了大木船的原貌:船长43米,最宽处5.9米,船头高6米,橹桨齐全,首尾高昂,形态优美。整艘船是用上等的黎巴嫩杉木制成,出土时杉木的香味仍依稀可辨。据研究,这是胡夫国王的“太阳船”,与古王国时期太阳崇拜有关。太阳崇拜的说法认为,国王死后,其灵魂升天,乘坐着太阳的大木船,随着太阳神昼夜在太空和地下航行。胡夫“太阳船”的出土,是20世纪中叶埃及考古学的重大发现之一,对于研究古埃及造船、航行以及古王国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埃及政府特地在胡夫大金字塔南侧修建了一座太阳船博物馆,并于1982年3月6日正式对外开放。1985年由埃及古物局和国家地理学会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对第二石坑进行了考察,发现坑内也有一艘同样的太阳船的松散部件,按照船体的形状、顺序堆放着。当时,考察队采用先进的氨塞装置,对坑内散落的船体部件没有搬动,只作了考察和详细记录,让它们继续埋在沙堆里,以便长期保存。1985年发现的这艘太阳船与1954年发现的第一艘太阳船极为相似,可见它们是姊妹船,只是第二艘船保存得不够完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民族考古学的主要成就是对西部沙漠绿洲的发掘,这一地区向来不被西方考古学家所重视。西部沙漠从尼罗河岸开始,向西伸延到利比亚,向南与苏丹接壤,向北直达地中海,占埃及领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这片沙漠看似荒凉,却并不缺水,雨水虽然稀少,却有丰富的地下水源,形成一串零零落落的绿洲分布在空旷的沙漠里。西部沙漠绿洲的历史极其悠久,而且内容丰富。这些地方在古代即有人居住,罗马时代这里处于联结利比亚各行省的贸易道上,成了繁荣的货运枢纽。埃及学者费克里在这一地区进行过开拓性的工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费克里就发掘了达赫拉绿洲的墓葬,并出版了两卷本的《埃及的绿洲》(1973,1974)。
近年来主持西部沙漠绿洲考古工作的是当今埃及最著名的考古学家、埃及古文物最高管理委员会主任哈瓦斯博士。1999年3月,哈瓦斯博士领导的一支考古队在位于开罗西南205英里处的拜哈里耶绿洲开始发掘,寻找沙漠墓葬遗址。考古队在4个地方同时进行发掘,结果每处都挖出一个堆积着木乃伊的坟墓,共挖出放置在家庭墓穴里的142具尸体(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2000年5月,考古队又开始进一步发掘,发现了另外7座墓,里面共有100具木乃伊,其中一部分木乃伊戴有黄金面具。这就是在西部沙漠绿发现的非常罕有的“黄金木乃伊”,它们大多数是罗马化的埃及人木乃伊,年代属于公元1、2世纪。[13](P207) 西部沙漠中的重大考古发现,令埃及考古学家们兴奋不已,沙漠绿洲的考古也因此被纳入埃及考古学,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99年到2000年的世纪之交,哈瓦斯博士主持了吉萨金字塔区的一次重大考古活动。1999年3月3日,美国福克斯电视台与埃及考古部门合作,通过卫星向全世界现场直播了哈瓦斯博士主持的这次考古活动。[14](P12) 在这次别开生面的发掘过程中,哈瓦斯博士亲自在电视镜头前进行了现场解说。这次发掘取得了三项成果:打开了古埃及第4王朝大祭司凯的及妻女的2个墓穴;重新找到了国王孟考拉的王后卡蒙若内比悌的小金字塔人口;同时还首次发现了古埃及冥世主神奥西里斯的象征性墓穴。
2002年9月17日,哈瓦斯博士主持了胡夫大金字塔“机器人探索之旅”的大型考古活动。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现场直播了机器人沿胡夫大金字塔的一条秘密通道探秘的全过程。被称作“金字塔漫游者”的机器人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探测,爬过了200英尺的狭长通道,在通道尽头的第一道封闭石门上钻了个小洞,然后伸进一台用细电缆连接的摄像机,借助高清晰度探头,结果发现石门后是另一堵封闭的石墙。在直播期间,哈瓦斯博士又在大金字塔附近一座古墓的石棺中发现了一具4500多年前的男性骨骸,保存非常完整。[15] 据哈瓦斯博士分析,这位沉睡了4500年的石棺主人,就是当年建造大胡夫金字塔的监工。哈瓦斯博士宣布这次考古活动暂告一段落,探秘工作以后还要继续下去。这次大型考古活动虽然没有像媒体事先炒作的那样会揭开金字塔建造之秘,但电视观众和考古学家同步观看了“金字塔漫游者”探秘的场面,全世界有142个国家和地区同时现场直播了这一举世瞩目的考古挖掘活动。这次大规模的活动,是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向全球直播了埃及现场考古发掘的过程,其意义已超过了这次重大考古发掘活动的本身。
半个多世纪以来,埃及的民族考古工作已逐渐成长与发展起来。埃及民族考古工作者所发掘的文物,不断地充实埃及博物馆的馆藏,他们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引起国际埃及学界的重视。现在的埃及博物馆的藏品总数已达30万件以上,拥有世界上同类博物馆中数量最多、最有价值的藏品。作为金字塔的故乡的埃及,已成为世界埃及学研究的中心之一。
三、埃及学研究的全面扩展
埃及学发展至今已是门类齐全,分工精细。埃及学的主要分支有:语言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碑铭学、艺术学、宗教学、建筑学与科学技术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语言文字学,因为它是埃及学研究的基础。随着埃及学的发展,大的专业还可细分,以语言为例,按其发展情况可分为以下5个阶段:
1.古埃及语,是埃及第1—8王朝(约公元前3100—前2160年)时期的语言,经研究象形文字的原文证明,其中还包括有金字塔文(宗教文献)的语言。这一阶段的其他残存文献,主要是公文或正式的殡葬文和墓志铭。
2.中埃及语,是埃及第9—11王朝(约公元前2160—前1991年)时期标准文学语言,由古埃及语稍加修饰后演变而成。它的文学语言是以公元前2000年左右通行的口语为基础的。中埃及语的较早形式只残留作为宗教语言,它的较晚形式保存在一些碑文和文学作品中,一直流行到公元前1000年代希腊、罗马统治埃及时期。
3.后埃及语,是埃及第18—24王朝(约公元前1567—前715年)时期的俗语广泛应用于文学作品、日常书信和商业文契中,而在一定程度上还保存在第19王朝以后的公文中。后埃及语和它以前的各个阶段有重要区别,如使用定冠词和不定冠词,有若干语音变化等。
4.世俗语,这一名称不严格地应用于第25王朝至后期罗马帝国(约公元前730—公元470年)时期以通俗文体写成的书和文献中所使用的语言。这一时期用世俗体写成的大部分是法律文献,间或有文学和宗教作品。
5.科普特语,古埃及语的最后发展阶段是大约从公元3世纪起用科普特文字写成的语言;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是古埃及人的基督教徒后裔科普特人的口语。科普特语采用希腊字母表,并增加了7个溯源于象形文字的特殊字母。[16](P5—6) 在公元642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后,科普特语逐渐被阿拉伯语所取代。到了16世纪阿拉伯语在埃及已十分流行,科普特语仍保留了下来,至今只在教堂中作为宗教语言使用。
古埃及文字按其书写方式又有象形文字、祭司体文字、世俗体文字和科普特文字之分;在语法结构上也有相应的变化,如科普特语的词汇中包括许多希腊的外来语,出现了语法上的小品词,与以前各阶段的词汇大不相同。
目前,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都建立了埃及学,使埃及学真正成为了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在发达国家中,埃及学规模最大的是美国、法国、英国和德国,其次是前苏联、瑞士、意大利等国。而在埃及学研究对象的国度——埃及,由于历史的原因,其本国的埃及学规模还不能与西方相提并论。1952年埃及获得独立后也曾派出留学生到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埃及学,尽管培养出了一批埃及学家,他们的埃及学研究总体水平比之美、英、法、德仍有逊色。但是,埃及有遗址,埃及博物馆藏有大量珍贵的文物,包括浮雕、石雕、石棺、纸草文书、随葬艺术品等。20世纪初是埃及考古学最活跃的时期,当时,埃及政府允许挖掘者可保留半数的出土文物,大大激励了外国博物馆投资于埃及考古发掘。因此,世界各大博物馆都不遗余力地收藏古埃及文物,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官博物馆所藏古埃及文物堪称一流。由于20世纪之前英国的霸权地位,使该国考古学家得以最大限度地在埃及收集到各类文物,大英博物馆因此成了除开罗博物馆以外收藏古埃及文物最多的地方,据不完全统计,大英博物馆的古埃及藏品数量达7万件以上;埃及学发轫于法国,法国人在埃及获得的大量文物,多收藏于卢浮宫博物馆,所以该馆的埃及藏品也相当丰富。从19、20世纪之交开始,美国各大博物馆开始增设埃及收藏品的陈列,而在埃及的发掘又充实了博物馆的藏品。到20世纪中期美国的埃及学已名列前茅,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布鲁克林博物馆的古埃及藏品已蔚为可观。此外,意大利都灵博物馆、德国柏林博物馆、荷兰莱登博物馆、前苏联莫斯科美术博物院和列宁格勒国立博物院也收藏着数量不等的古埃及文物。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著名的综合性大学都开设有埃及学专业课程,如伦敦大学、巴黎大学、海德堡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开罗大学等。这些大学实力雄厚,已成为当今埃及学教学与研究的中心。专职的埃及学研究机构,如德国东方研究会、法国东方考古所、埃及英国考古学校、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等,以资格老、研究水平高在国际埃及学界久享盛誉。上述各国的博物馆、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埃及都设有研究所,领导本国考古队常年在埃及挖掘,主持整理、发表研究成果,并兼以宣传本国文化,与各国埃及学同行交流和互换资料,成为真正的文化交流中心,其工作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得到一些大基金会、大公司的经济赞助。目前,来自100多个国家的专业考古队正在埃及境内的500多个文化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新的发掘成果不断问世。
早在19世纪,各国的埃及学家就已互通信息,交换资讯与心得。进入20世纪后,随着埃及学在许多国家的建立,这一学科已具有相当大的国际规模。到了20世纪70年代,世界各国的埃及学家共同组成国际埃及学家协会,定期在不同国家召开国际埃及学会议,广泛进行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1976年第一届国际埃及学家大会在开罗举行,以后每3年召开一次会议,使全世界埃及学研究者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埃及学的权威性刊物是1914年在英国伦敦出版的《埃及考古学杂志》,每年出版一期。这份杂志所刊登的论文并不限于埃及考古学领域,已涉及到埃及学的方方面面,包括古代埃及的语言、文字、文学、历史、经济、法律、建筑、天文、数学、医学等内容。还有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主编的《近东研究杂志》,以刊登亚述学和埃及学的论文为主,其埃及学论文水平高、亦有相当的学术分量。自埃及学诞生以来,世界各国出版界就热衷于出版与古埃及文明有关的书籍。全世界每年出版的埃及学书籍平均在800部以上,供研究的埃及学图书资料(包括学术专著、铭文等)就有5000余种,其中以英文最多,德文、法文居次,阿拉伯文亦占有相当的比重。
除出版专著、发表学术论文外,埃及学家们还负有撰写通俗读物、举办展览,普及古代埃及文化知识的任务。目前,世界各国出版的古埃及画册、通俗读物已多得难以记数。20世纪70年代,“图坦卡蒙随葬品环球展”在美国和日本曾掀起了一阵“埃及热”;1999年夏,大英博物馆先后在中国的上海和香港举办“大英博物馆藏古埃及艺术珍品展”,观者如潮;2003年10月至2004年1月,埃及博物馆又连续在上海和北京举办“埃及国宝展”,更引来了大量参观者,人数最多的一天达到了15000人。最近这次展览里的展品共143件,是埃及政府提供外展文物最多的一次(20世纪70年的“图坦卡蒙随葬品环球展”只展出70余件文物)。埃及政府这次向中国提供的文物的等级在外展中也是最高的,展出的文物均为埃及国宝,十分贵重,总价值在2亿6千万美元以上。跨入21世纪的“埃及国宝展”,在上海和北京又掀起了一阵“埃及热”,同时也为埃及学在中国的普及工作增添了新的光彩。现在,每年专为寻访名胜古迹而涌入金字塔故乡的游人竟成了埃及国民经济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上述情况,足以证明世界各国人民对古埃及文化的浓厚兴趣,这正是古埃及文明本身的魅力所在。埃及学自1822年创建以来,经过数代埃及学家的共同努力,已有很大发展。古埃及文明是属于全人类的,日新月异的埃及学的研究成果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参考文献:
[1] Schulz,R and Seidel,M.Egypt,The World of the Pharaohs[M].Cologne,1998.[2] Bierbrier,M.J.Who Was Who in Egyptology[M].London:Whitstable Litho Printers Ltd.,1995.[3] Baines J.and Malek J.Atlas of Ancient Egypt[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4] 戴尔·布朗著,迟俊常译.埃及:法老的领地[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5] 彼得·阿克罗伊德著,冷杉,杨立新译.死亡帝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6] 西拉姆著,刘逎元译.神祇·坟墓·学者[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7] 梅芙·肯尼迪著,牟翔,王强,金国林,朱娥巧等译.考古的历史[M].太原:希望出版社,2003.[8] 保罗·G·巴恩著,郭小凌,周辉荣译.考古的故事——世界100次考古大发现[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9] 保罗·G·巴恩著,郭小凌,王晓秦译.剑桥插图考古史[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10] 维库特尔著,吴岳添译.古埃及探秘—尼罗河畔的金字塔世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11] 布赖恩·费根著,黄中宪译.法老王朝[M].太原:希望出版社,2006.[12] 阿尔贝托·西廖蒂著,彭琦,陈甜,郑振清等译.古埃及——庙·人·神[M].北京: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2006.[13] 安德鲁·亨弗莱斯著,王尚胜译.埃及[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14] 理查德·艾尔曼著,杨傲多译.众神的宫殿[M].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1999.[15] 美联社开罗9月17日电[N].参考消息,2002—09—18,第8版.[16] Gardiner,A.Egyptian Grammar[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
来源:《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
我在故宫做考古——徐海峰:紫禁城考古概要
我要新鲜事2023-05-06 19:03:290000古墓发现:六名少女陪葬,墓葬文物价值高
2004年冬季,湖北省钟祥市接到了一个电话,声称村旁的明代郢靖王墓可能又被盗了。这座大墓已经不是第一次被盯上了,自1998年起,墓中就发生了多次盗墓未遂和被盗事件。虽然盗墓贼的手段高明,但是当地群众在对抗期间也在不断的成长,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抓获了多名犯罪团伙。我要新鲜事2023-04-11 21:23:060000荐书 |《风雅中国——杨泓说文物》:不朽的笔力 精彩的讲述
翻开文物出版社新书《风雅中国——杨泓说文物》,清新诗化的文字、珍贵鲜活的图片扑面而来,让人不由自主踏上一条文物鉴赏之旅,在对一件件精美文物的流连品味间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磅礴气韵与生动气息,邂逅属于中国人的清朗与壮阔。《风雅中国——杨泓说文物》作者:杨泓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年3月定价:78元我要新鲜事2023-05-06 19:52:390000【考古词条】铁器时代 · 白沙宋墓
北宋末赵大翁及其家属的3座墓葬。位于河南省禹县白沙镇北。1951年12月发掘,报告由宿白编写,题名《白沙宋墓》,因而习称这3座墓为白沙宋墓。我要新鲜事2023-05-25 20:11:040000过去有四种特殊婚姻,三种已被禁,有一种不只未禁还被当婚姻自由
过去有四种特殊婚姻本文作者倪方六买卖婚、换亲、私奔结、阴亲,是过去存在、且流行的4种特殊婚姻形式。前三种已被当成陋俗给禁了和废除了,但“私奔”却一直存在。(婚礼)买卖婚我要新鲜事2023-05-27 07:04:0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