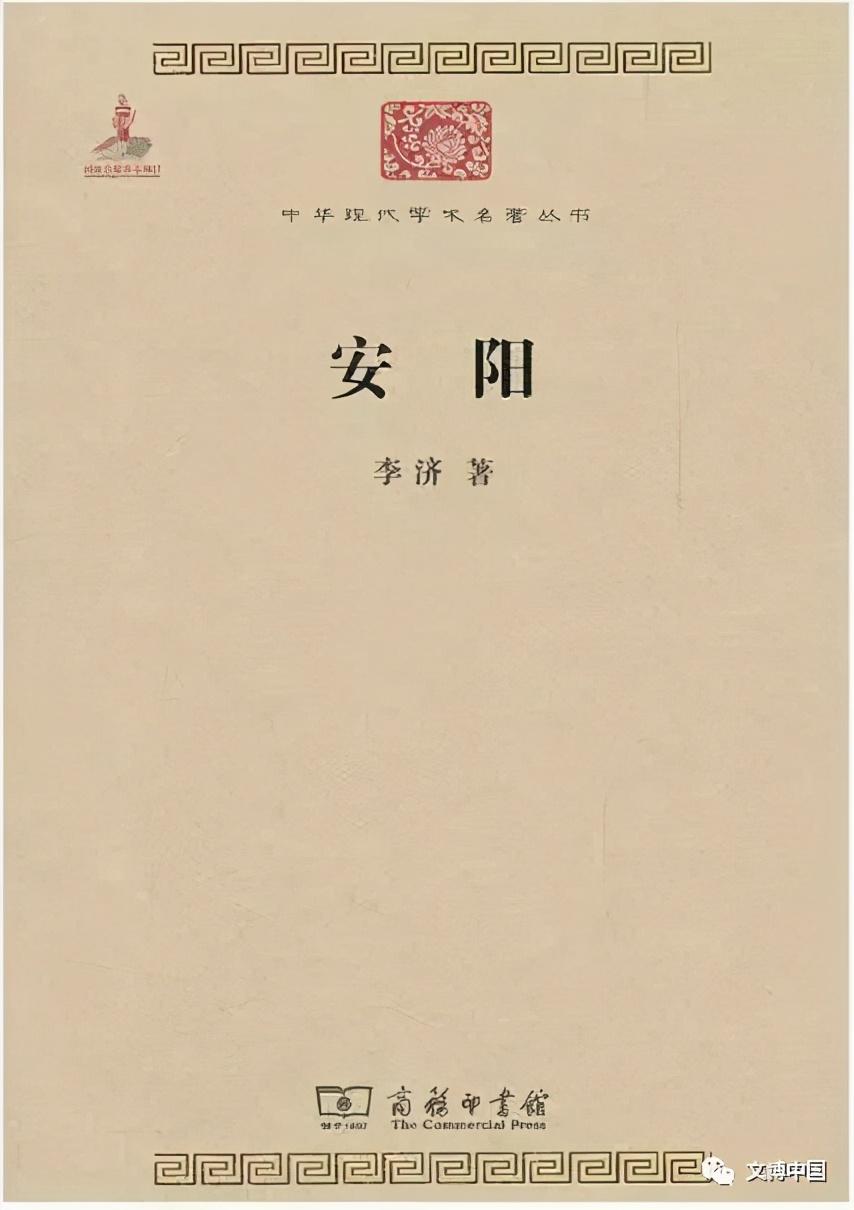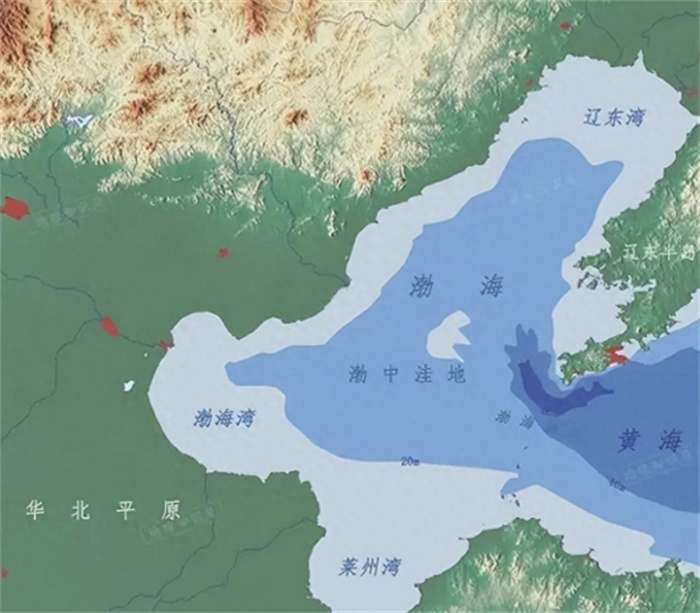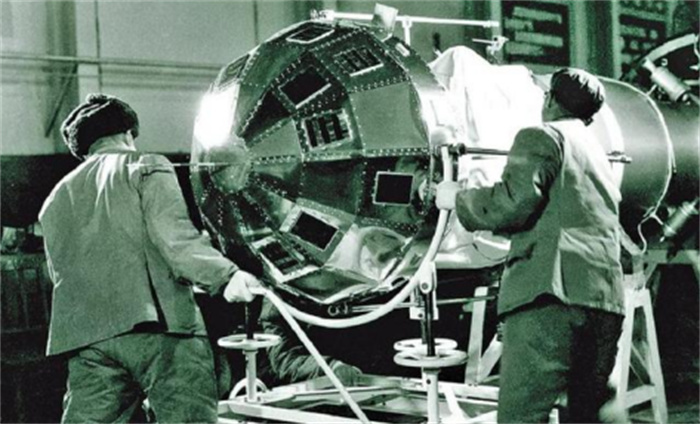马敏:耶鲁怪杰史景迁
#点亮真知计划#Jonathan D.Spence,中文名字史景迁。1936年8月11日出生于英国,耶鲁大学历史学Sterling 讲席教授,是公认的16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在过去半个世纪西方看中国的过程中,史景迁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和“头号中国通”费正清齐名,对西方所有想了解中国的人来说,他的著作都在必读之列。作品包括《曹寅与康熙》(1965)、《改变中国》(1969)、《康熙自画像》(1974)、《王氏之死》(1978)、《利玛窦的记忆宫殿》(1984)、《胡若望的疑问》(1987)、《皇帝与秀才》(2001)以及《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2007)等等。2009年,史景迁从耶鲁大学退休。2021年12月26日辞世,享年85岁。

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史景迁,他身材修长,头发微秃,穿着随便,不刻意修饰,但又洒脱自如,和蔼可亲,颇具风度;他不爱写严格的学术论文,不出席大型的学术会议,不培养自己的学术"梯队",不作系统的学术规划。他只是非常投入地教书,教书之余,则读书、写书和旅行。教书、读书和旅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写书作准备。教书、读书、写书是他生活的中心内容和归宿,几十年下来,在他的笔下,已汩汩流出了近十部文学味道很浓的有关中国清代及近现代历史的著作。深得美国读者的欢心。
史景迁系J.D.Spence为自己所取的中文名字。他景仰中国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的成就,悉心追求司马迁的叙事式史学风格,故取本名的谐音而名之。已届耳顺之年的史景迁于一九三六年出生于英国伦敦郊外的萨瑞郡,大学时代曾分别就读于温彻斯特学院和剑桥大学,受到英国史学的严格训练。一九五九年他因获美仑奖学金,得以从英国到美国耶鲁大学攻读研究生。在耶鲁,史景迁深得斯坦福大学的著名女史学家芮玛丽(Mary C.Wright)的器重和赏识,招为门下弟子。史景迁则不负师望,刻苦问学。一九六五年,他获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曹寅与康熙皇帝》获荣誉极高的一项论文奖:The John Addison Porter Prize。史景迁本人也因此而破例留校任教(美国名牌大学一般不留自己的毕业生任教)。一九七○年芮玛丽辞世,史景迁继承乃师在耶鲁的位置,一路升到"亚当斯历史讲座教授",并兼任耶鲁大学Timothy Dwight学院的院士。
史景迁身居耶鲁教授的高位,却不摆架子。经常于课余饭后或伏案写作的间隙,抽空溜到New Haven(耶鲁大学所在地)街上的咖啡馆泡上一阵子,与同事、研究生或本科大学生高谈阔论。记得当初我将由普林斯顿转到耶鲁当访问学者之前,曾手持余英时先生的一封介绍信前往耶鲁找史景迁探路。抵达耶鲁后,心里老犯嘀咕:如此一个大牌教授,会不会从百忙中抽时间见我这个来自异邦的无名小卒?犹豫半天,终于还是横下心拨通了他的电话。当我说明来意之后,史景迁不仅满口答应见我,而且于晚间亲自冒雨驱车到我的住处找我。顷刻间,那种陌生和紧张感全部烟消云散。以后在耶鲁我一直得到他的照拂。
在古堡高耸、春藤绕墙的耶鲁校园,史景迁的讲课堪称一绝。他主讲的从明末到目前四百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课程,每两年才开一次,一次一学期。按理说,一个遥远的东方古国的近现代历史,是很难引起养尊处优的美国私立大学学生兴趣的。他们有那么多新奇有趣的课程可以选择,干嘛偏要去听一个老学究唠叨陌生国度、陌生时代的陈谷子烂芝麻呢?然而在耶鲁却恰恰例外,史景迁的中国近现代史课是最叫座的课程,每次选修的人数都超过五百人。换言之,差不多每两个新生就有一个选过他的课。
史景迁的中国史课程缘何有如此的魅力呢?带着疑问,进了史景迁的大课堂。第一感觉是这课堂可真正是大!约几百人济济一堂,迟到者只好坐在过道上,甚至爬到窗台上听课。几堂课听下来才恍然大悟:那些枯燥的史实,过耳即忘的人名、地名,经史景迁浓重的英国腔英语娓娓道出来,似乎马上就有了血肉,赋予了活力,充满了形象,可以触摸、可以感觉、可以品味,可以与之交流对话。几百年前的历史穿越时空的阻隔,鲜活地来到你的身旁,使你如身临其境,这真是令人称奇的讲演艺术!史景迁的讲演同时又是一种表演。诙谐的语气,生动的表情,炽热的激情,加之大段引用背诵的诗歌、散文或小说,用作教学辅助手段的幻灯和录像带,总之,他用一切可以调动的形象手段,把毫无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的学生带入了特定的史境(historical context)。如同史景迁的教学风格,他的著作不像其他历史学家那样拚命追求学术性和科学性,企图在局部或有限范围内精确地描摹历史、还原历史,或发现历史中所隐藏的"规律性",简言之,以求真求实为史学的生命。史景迁也利用第一手材料甚至原始档案资料写书,但他的长处却不在凭借对史料的占有"科学地"研究历史,而主要在于借助于二手资料生动地叙述历史,再现历史的全幅式场景。这正是他以中国史为主题的历史著作能获得如此广泛的美国读者青睐的根本原因。
写人是史氏历史著作最突出的特征,也是他永恒的主题。除近年所出版的一本大部头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寻求近代中国》(一九九○)而外,史景迁的每一本书都是一本独立的传记,或若干交错的传记。这些传记的主人翁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有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康熙自剖》,一九七四);有手持圣经的传教士(《利玛窦的记忆之宫》,一九八四);也有激情浪漫的革命者(《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一九八一);甚至连姓名也弄不清楚的乡村妇女(《王氏之死》,一九七八),等等。史景迁以极大的同情心和丰富的想像力讲述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他并不在乎传主们有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丰功伟绩,而只是平等地将他们视作历史长河中曾经生活过的一个人或一群人。他想告诉人们的,无非是这些人如何以自身的禀赋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中去生活,去思考,去实现其生命的旅程和存在的价值。对人的探讨实际上也就是对生活和生命意义的探讨。写康熙皇帝,实际上已超越了康熙自身,或者说要想去探寻康熙内心的世界和他背后的世界,如《康熙自剖》开头所言:
本书的目的是探索康熙的内心世界:何种内在的力量使他能够承负统治中国的重任?他从周围世界学到了些什么?又如何去看待他的子民?什么使他快乐,什么惹他恼怒?在岁月流逝中,他记忆犹新的究竟是些什么?
那个曾在广州替教会看门,后来被耶稣会传教士带到欧洲,受尽屈辱后又返回家乡的江西人胡若望的种种疑问(《胡若望的疑问》,一九八八),归结到底,还是史景迁本人的疑问:人的生命旅程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种对人及生命本体意义的深厚的关怀,使史景迁的史学著作如同他的讲课一样,充溢着人文主义的气息。
优美的文字风格和高超的写作技巧,构成史氏历史著述的又一突出特色。时下一般史学著作因追求严格的科学性,往往忽视了可读性。相反,史景迁格外注重叙事的技巧,如写康熙,借康熙本人之口,从"游"、"治"、"思"、"寿"、"阿哥"(儿子)、"谕"等六个方面,把康熙的生平行述和内心世界写得声情并茂,多采多姿,可读性极强。胡若望的生平也充满了传奇色彩:一忽儿广州,一忽儿巴黎,一忽儿好望角,一忽儿罗马,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文化和风俗,以及主人翁的幻想、期待、受骗、沮丧、获救、回乡等不同的心理活动和遭遇,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但史景迁却写得从容不迫,错落有致,随胡若望的命运沉浮而星流云转,道出了一个早在一七二二年就到过欧洲的中国人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以及他在穿越不同地理与文化空间时内心的种种冲突、疑问。
史景迁文笔的优美,状物写景的深湛功力,在当代史学家中实属罕见,以致有人断言,只要熟读史景迁的若干著作,英文写作就能大体过关。也有人称他为"当代史学家中的语言文学大师"。如他写塞外的夏日:
步出长城之外,清新的空气和湿润的泥土令人为之一爽;舍山间小路,策马跃入粗犷的莽原,森林覆盖的群山起伏,犹如密密匝匝的青纱帐。愈往北行,视野愈加开阔,数百里内一览无余。......虽时值盛夏,但树上有露珠闪亮,一些树叶已开始变黄,宛若深秋的景色。(《康熙自剖》)
尽管我的拙译很难准确传达原著的神韵,但也可以看到:这是一幅优美如歌的塞北风景画,跃动于内的是活泼、旺健的生命力,是对自然的由衷礼赞和热爱。在史景迁的史著中真、善、美融为一体。正因为如此,麦克阿瑟基金会在颁发给他一笔为数甚巨的奖金时,说史景迁是一个"有着特殊才华、有前途的人士",他"将原创性的史学见解与叙述故事的文学禀赋相结合,使其著作在描绘人物与情境方面予人以小说式的感觉"。这已准确地道出了他历史著述的根本特色。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新史学的兴起,史学的科学化一直是现代西方史学的主导潮流。实证主义史学家希望把史学变成自然科学式的科学,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爵士曾充满自信地宣称:"只要把全部史料给我,我就能把整个历史还原出来。"这不禁使人想起牛顿的名言:"只要给我一根杠杆,我就能把地球举起来。"而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型史学,则试图整合历史学与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等学科,以"总体史"代替"事件史",探寻历史深层结构的变迁。他们一以贯之的理想,即是让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科学主义是这一主导思潮的本质。由此观之,史景迁的史学追求乃是游移于西方主流史学之外的异数。
尽管属于非主流史学,但丝毫不可降低史景迁史著的意义。它至少在两方面构成对主流史学的挑战与补充。其一,它承续了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的西方古典叙事史的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使历史学重新变得多姿多采,令人读来有趣。其二,它注重历史的人文价值,着意发掘史实中所包涵的文化意蕴,在研究历史中寻找人生的终极关怀,使历史再度成为"人"的历史,人重新占据历史的中心舞台。在这一意义上,它可称之为人文取向的史学,而与科学取向的史学相对应。后者注重求真,前者则侧重"化人"(以史为鉴,以史育人)。最后,无论是恢复史学的叙事功能,还是重振史学的人文精神,其根本指归,仍在于使史学走出学术专门家的象牙塔,贴近普通民众,贴近生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人文史学也就是"平民"史学。为平民而写,同时又写平民,写那些"在士大夫教育水准之下的普通人"。如果说科学主义史学重在"研究",那么,人文史学或"平民"史学则重在"普及",它体现了一部分历史学家对历史知识传播的关心和重视。这些历史学家旨在通过重建大众史学,使历史这门古老的学问重新焕发活力和青春,重新赢得社会的重视和普通民众的关心、喜爱。目前传记史学的再度受到垂青,便反映了史学发展中的这一新趋势。
史景迁正是以其特有的才华和禀赋,在美国东亚史研究领域中开辟了人文史学即"平民"史学的先河,架设了一座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一九九六年六月
原文发表于《读书》1997年06期
盗墓笔记九龙抬尸棺,东夏国万奴王的巨型蚰蜓棺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个棺材的规格和豪华程度,就显示了其主人的地位所在。早前,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个来自东夏国的九龙抬尸棺,而在小说《盗墓笔记》中也曾提到过这个神秘的棺材。据说这个棺材的主人是东夏国万奴王,上面的九条龙其实是巨型蚰蜓。九龙抬尸棺,东夏国的帝王之棺我要新鲜事2023-05-07 13:40:590000中国考古百年 | 一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典范巨著——《安阳》读后
巩家楠2021年,中国考古学迎来诞生100周年。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开始对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进行发掘,中国考古学由此诞生。1926年,李济主持西阴村遗址发掘,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首次田野考古发掘,也奠定李济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地位。我要新鲜事2023-05-07 17:14:400000超龙:北美洲超巨型恐龙(长42米/世界上最长的恐龙)
说到大型恐龙,大家都会想到霸王龙,毕竟它是恐龙之王。但是单论体型,霸王龙在恐龙中并不算特别大,因为比它大的有很多,比如今天要介绍的超龙,它体长42米,生活在1.45亿年前的晚侏罗世,是世界上最长的恐龙,接下来就随小编一起去认识看看。超龙基本资料我要新鲜事2023-05-08 03:57:52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