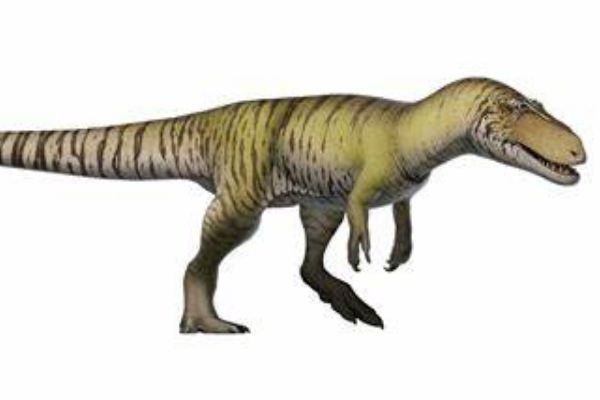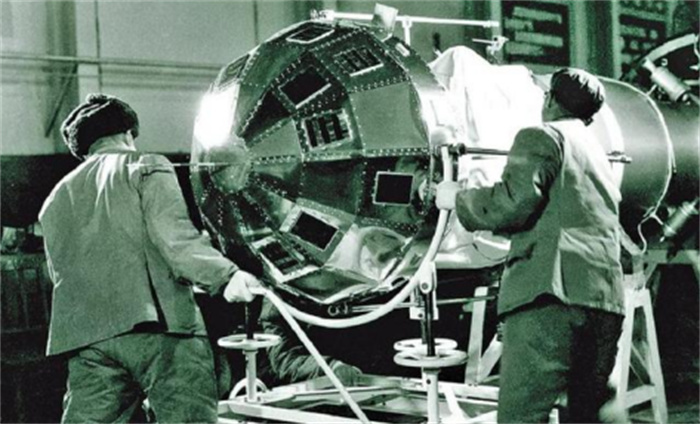郭静云:殷商以前的人牲斩首礼
【编者按】大约二年前,在实地考察石峁遗址后,郭静云先生首先提出石峁遗址很可能会发现马骨,并将这一认识写进其著作《天神与天地之道》,最近有报道在石峁遗址确实发现了马骨,印证其说法。现将郭静云先生相关论述摘要如下,以飨读者。
1.长江流域
在殷商之前,新石器、青铜时期的长江流域遗存中,已发现将人牲斩首祭祀的传统。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无躯人头骨埋葬个案见于长江中游地区湖南高庙祭祀遗址中,几具男性头骨与鹿角、野猪下额骨合葬于祭祀坑中,其年代距今6700-6000年[1]。目前我们对该时代的文化脉络尚不大清楚,相较而言,高庙祭祀坑似为狩猎仪式的遗存,但因为发掘及研究不足,目前仍难以提出更成熟的推论。
其实,不仅在长江流域,在渭河流域与高庙文化时代大约相同的北首岭遗址也发现随葬品很丰富的无头骨成年男人的墓葬[2],依笔者理解,此为献巫的墓葬,可能与高庙文化的仪式接近。但是,新石器中晚期猎民献巫的资料极少,目前只能提出前述高庙和北首岭两处个案,所以很难作系统的分析。江汉地区的资料虽然也颇为零散,但至少同一区域发现了几个遗迹,所以学术界对其已有初步讨论。此外,如在淮河上游贾湖遗址晚期(距今7700-7500年)的遗存中,发现几座随葬品丰富并随葬巫师法器的墓,其墓主为被砍头非自然死亡的壮年男人[3]。因此献巫斩首礼或许可以溯源至新石器中期。
不过,只有从新石器时代末期、青铜时代早期以来,我们才能看到一些人牲文化的规律,并且除了献巫之外,亦开始出现有殉葬者的墓,显示人牲的两种作用:第一,最为古老的是整体社会献巫的活动,社会特选自己的成员赠送给神以祈祷对整体社会的保祐;第二,在已有君臣关系的国家化社会中,在高等贵族逝世之后,使某位人陪他下葬升天及在永生中作他的伴侣。
在大溪文化晚期仅有第一种斩首礼,如中堡岛遗址发现的一座墓坑,坑里有七具被斩首的人骨架。杨华先生认为,这可能与聚落之间的战争或冲突有关。[4]但笔者以为,这应该是一种仪式性的埋葬,源于上古时以人祀神的传统。同时期的桂花树遗址中也发现一座四人墓,尸体被肢解,头部被斩断而分开放置。[5]直至石家河时代,上述两种意义的的斩首礼都可见,如石家河邓家湾32号墓的墓主,是个10岁男孩,随葬品十分丰富,墓中还有一位遭到斩首的殉葬者,其枕上有三角形的豁口[6]。房县七里河石家河遗址发现两座具有土台阶的半穴居式房屋76H40和76H10,里边遗留的文物很丰富,且有几具无身躯的人类颅骨放在台阶下的正中央;另发现一座78Y1陶窑,火口放置一具人类颅骨,火门外也有一颗,空间里还置有一根肱骨;此外,还有76M1号墓,是以一具人头骨殉葬的10人合葬墓;76M19号墓合葬有7位成年男性,其中一位无头骨;78M19号墓独葬着一位无头骨的男性。[7]肖家屋遗址也发现三座屈家岭二期无头人骨的墓葬(即19、21、33号墓),皆有相当丰富的随葬品[8]。
郭立新先生将这些死于非命而葬的人,都视为在战争中被杀的敌方俘虏或猎头遗存[9],然而,我们从上述情况看起来,明显可发现是仪式性埋葬,且具有祈求神明庇祐的作用。将人头放在陶窑里,象征着保护窑坊的意义,在七里河发掘出来的两座房屋可能便是祭堂,其中所放置的头骨也含有同样的神祕意义。不作殉葬者而专门献给神的人牲,可能具有巫师的身份,这在学术界中早已从各方面被论证,并且因上列的证据相当充分,在学术界均获得共识。
若是杀掉在战争中所俘虏的敌人以献祭,虽然不无可能,但是敌方的人头不会具有保护我方的作用。古代建城、建坊或准备进行重要大事之前,常以巫师贡献祈祷来祓灾攘祸。石家河无头者的墓葬有随葬品。在上古文明中,丧礼属于神祕的精神文化,是助于族人神祕永生。所以,这些被斩首以献祭于神的人,并非俘虏和外人,而应是身份地位高的靈媒和巫师,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将祈求上达于天神,求得天神祐助。
孙其刚先生搜集各地零散出土的无身躯的头骨或无头骨身躯的埋葬案例,并加以研究,发现新石器、青铜时代各地都有这种现象,包括河姆渡、良渚、半坡、大汶口、齐家等,不过笔者不能赞同以“猎头”的习俗解释这些神祕的埋葬。[10]“猎头”活动是晚期的狩猎民族所有,如太平洋原住民等,这绝不是农耕大文明的传统,严文明先生早已指出这一点[11]。
比起渔猎社会,农耕社会更加需要团结不可分的观念,共同管理灌溉,面对水灾、火灾、虫灾等等的自然灾害。农耕文明中,普遍存在着共同的神婚以及血祭的活动,都有巩固社会团体的作用。在实行神婚礼的社会中,所有的孩子都不属于父母自家所有,而是社会共同所有,所以用小女孩或少女祭献给水神,或者将青年男子当作共享农田、塘坝、建筑、作坊之人牲,献给保护神等,都是社会共同决定而实行,以共同的精和共杀的血巩固其团结性。
虽然,从各地零散发掘之独头或无头埋葬之例,目前尚难以看出完整的信仰,但笔者假设,如果将仪式性埋葬之墓葬形式,与礼器造型互为参照,从其关连性中,或许我们可以推论出,使用人牲并加以斩首祀神的信仰活动,在江河农耕文明已得到了系统性的发展。
2.西辽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
邯郸涧沟村夏家店下层时期所发现的房基内有四具头骨,是被斩首而死,之后又经剥除头皮;而同一地点的上层,也发现了身首分离的五人男女墓葬[12]。同样的,灰坑和陶窑里也发现了几具被斩首的男、女头骨,年龄为青年或中年,部分有剥皮的痕迹。可见夏家店下层先殷文化也曾有人牲斩首祭神的礼俗。严文明先生认为,剥皮可能是用来作饮器的指标性行为[13],可是剥皮与作头骨杯并不具有必然性关联,虽是经过剥皮的头骨,但其作用也可能有所不同,况且斩首祭礼不可能仅是以作头骨杯为目的,而是具有更深入的精神意义。笔者对头骨饮器的考证认为,该文化的起源偏晚,在殷商之前的时代难以被论证。[14]
学者针对殷墟中所发现的鼎里人头,做过科学检测,发现这颗人头曾被煮过。可惜学界对涧沟头骨未作这种检测,因此我们尚无法判断出确切的情况如何,但笔者推测,涧沟头骨与殷墟头骨的用法或许相同。
以人献祭,并将头骨埋在房基下,这是许多古文明都有的传统,用意是希望得到神对建筑的保祐、祓除灾厄。但在不同的文明中,这些礼俗又有所不同,新石器时代中期南安那托利亚地区ÇatalHüyük文化是将婴儿献祭后才建造房子,并将婴儿的尸体埋在房基下[15];古乔治亚文明用最好的青年兵,活活砌死在堡垒的城墙里,以保障堡垒不被外敌攻破。河北平原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人们,用青年头骨作奉献给神的祭礼,亦应是求神明保祐房舍。这与石家河人用头骨护祐窑坊和祭堂的传统是极为相似的。
夏家店下层文化与石家河文化用人牲献祭的传统虽然大同小异,可是这“小异”却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夏家店未见有如石家河那样埋葬无头的骨架并用珍贵器物随葬的情况发生,这种差异表示出人牲的地位有所不同。石家河的上古农耕文明有浓厚的巫师祭献信仰,被献的人牲被视为是社会与神之间的联络者,意即虽然将其当做献给神明的牲礼,但被献祭者本身亦成为崇拜的对象。这种信仰到了殷商时代尚未消失,因此甲骨文的“巫”意指高地位的人牲,同时也是被祭祀的对象。然而,殷商中央用人祭祀的礼仪却是遵循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传统:对巫师的尊敬和景仰已开始下降。
3.草原地带:以石峁遗址为例
陕北神木石峁遗址的发掘资料尚未完整公布,其地层、年代、分期、遗址布局、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还难以确定,但基本可知这是文化混杂的遗址,既包含本地长居的农耕和渔猎族群的聚落,也包含有数波来自草原的流动的游战族群。这种生活方式不同的族群的“共生”现象,在距今4000余年前的南草原地带(即欧亚大草原南缘)颇为普遍,从铜石并用时代的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ievo)直至青铜时代的安德罗诺沃(Andronovo)文化都有,形成了以米努辛斯克盆地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大文化体系。
这种“共生”现象起因于游战生活方式的形成。由于气候冷化,在亚洲大草原地带,原在本南缘就很脆弱的少量农耕衰退,采集狩猎者赖以维生的食物资源亦变少,一些原本以游猎为主兼少量农耕的族群转变到以掠夺维生,努力发展战争技术而成为专门的游战族群。游战族群逐渐发展出军力政权,以游战掠夺或远程贸易营生。他们在历史上发展青铜兵器技术,并逐渐掌握用驯马交通技术。
我们不能以为游战族群只是不停地流动,不定居更加不会建城。正好相反,他们因以战争维生,一定需要有掠夺后回来的保护区,也在活动范围中需要建筑几个据点。换言之,他们的生活方式是部分流动,同时亦有定居点或根据地。所以,在从里海到渤海及日本海的广大区域内,在亚洲草原丘陵地带出现了非常多的大、中、小型城池,它们均属于为军城,作为掠夺、游战族群的城邦和堡垒[16]。这类族团甚多,但是他们自己不耕地,不养猪、鸡等,不生产定居生活族群的产物,所以其日常所需严重依赖农耕和畜牧的定居聚落,尤其是在建城时,需要与本地原居的农耕或放牧族群建立“共生”关系。

石峁地形
在此要说明的是,这种“游战”族团未必有血缘关系,往往依据某种势力或凭首领感召而混杂组合为一群,群体分合变化纷繁。从青铜早期以来,这类族群组团结合很多,他们不仅依靠掠夺农耕或牧业生产者维生,彼此之间也互相竞争,不断互斗和战争。尤其是在选择栖息地点方面,每一游战族团都会追求尽可能占据有利之处。
这种“有利之处”有几个指标,其中最关键的有二:便利于建堡垒的破碎地形(陡峭山丘与山谷),包括能用作远望塔的地点;周围一定有定居的以农耕和养家畜为生的聚落,能提供部分食物来源。因为当时掠夺族群不少,所以本地农耕聚落也面对必须接受这种共生关系,以免被众多游战族群不断轮番地抢劫,而是专养一群强人以保护自己,或许还可以从固定庇护人的强大与获胜中获得额外收益。
石峁所在地点和其它一切条件都完全符合游战族团栖息所需,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理想的选择。其地点恰好在鄂尔多斯草原与黄土高原交界带,南下掠夺路线于此开始,当时生态条件比现在好,故周边亦有农耕、畜牧和渔猎聚落存在,山上可狩猎野兽,因破碎地形而形成的诸多陡深沟壁等自然障碍成为修建坚固堡垒的自然基础,使工程量大大减少,坚固堡垒的修建成为保护自身安全并存放战利品据点。因此当时这应该是很多族群都希望掌握的地点,应该有很多不同的族群早晚占据过石峁军城,屡被沿袭使用且不断地补建(这从石峁群城的建墙技术不同且明显可见多次补建的痕迹可以看出)。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大族群的大聚落,而是很多族群在某段时间掌握,互相纷斗或被竞争驱赶的中转站和据点。
简言之,在青铜时代早期,亚洲草原南部与山丘交界之地构成了一个大的文化体系,这是一个定居与流动、农耕与游战“共生”的地带,是游战生活方式的发祥地。石峁遗址的地点恰好在鄂尔多斯草原与黄土高原破碎的蚀沟梁峁地形交界之区,是族群流动、互斗和掠夺并存放战利品最频繁的地带。游战生活方式的发展,到了殷周时代时期,生计逐渐转换为以远程贸易为主。黄河水系从北往南下来的部份会有游战族群短期的据点,但是到了后期随着贸易的发展,成为草原与殷周贸易的联接地带(如马匹贸易),从事远程贸易的族群与本地农耕、畜牧居民“共生”(以陕北清涧县的李家涯、辛庄遗址为例);而黄河水系“几”字形的上段北游是游战族群栖息、安排较常用据点的地带(以神木县石峁群城为例)。也就是说,在共生社会中掌握权力的族群,在不同的地带和历史阶段中,或是以远程贸易为生计的贵族,或是以战争掠夺为生计的贵族。
石峁遗址已发现几个人头骨坑,其中一个坑埋葬几十具人头骨。石峁人头骨坑的意思与农耕文化明显不相同,这是不同游战族团之间斗争的遗迹,这些坑虽也有祭礼的内涵,但这明显是战争文化的仪式,而被献的人是敌对族群的战俘。
献用本国的巫师、王或王子与献用敌族战俘的意思完全不同,所以长江流域与草原地带的人牲斩首礼,虽然外观遗迹相似,内在涵义却完全不同。以笔者浅见,石峁人头骨坑或许是中国境内迄今所见最早的军事虐待和杀俘遗迹,也是殷墟人头骨坑的先驱前奏。
石峁遗址的头骨与殷墟还有一种关联:明显有不少白种人,比殷墟的比例可能还高,笔者也认为,石峁遗址在偏晚期的地层很可能会发现比殷墟略早的游战族群用马的遗迹。也就是说,不仅是战俘头骨坑的现象,还有石峁遗址的其它特点,均使笔者推论,相当于早商时期在河套周围流动的族团与后来南迁至安阳统治的族团,虽然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但其族团类型基本相近。不过,殷商族团在安阳定居后,更加深入地吸收了江河古文明内在的观念以及外在的祭法和礼制。
4.小结:殷商帝国人牲斩首礼的多元性
殷墟甲骨文记载献巫、拜巫的神祕之礼,但与此同时从考古来看,祭祀坑的人数颇多,并无随葬品。因此可知,殷商斩首礼应该属于对人牲尊重并不高的信仰脉络,并且已处于巫师的信仰开始变得薄弱的阶段。殷墟殉葬人数也很多,部分可能是配偶、侍从等家属身份,同时也用战俘祭祀祖先。在这一发展阶段上,斩首礼虽然已可完全确定其存在,但同时也失去了部分的神祕性,因为大量杀死战俘来献祭,在宗教意义上比杀死巫师并加以崇拜的信仰,其神祕性确实要低得多。
殷商新贵族来源于与石峁城主同类的游战族群,但与此同时他们强调自己是农耕大文明的正统继承者。这种双面性也在殷商献人牲的礼仪中有所反映。一方面,甲骨文和礼器继续表达,献人斩首属于献巫的神祕之礼;另一方面他们的人骨坑和用战俘的卜辞,符合早期草原游战族群献战俘的军礼;同时,殷商王族大量扩展献人的规模,而且使它变成统治者军力政权的表现。
因此基本上可以说,献战俘的习俗源自草原游战族群生活方式,非定居的族群不需要长期用战俘作奴隶,所以被抓住的敌人,男人一般被杀死,而女人保留作配偶。至于献巫的传统,其起源时代远比献战俘早,且滥觞于定居文化的脉络里,而在定居社会国家化的时期,形成了完整的礼仪。在这类礼仪中每一形象和步骤,都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但是由于神祕仪式很少留下痕迹,所以我们很难详细了解其仪式流程。例如,虽然饕餮造型甚多,但只有极少数在饕餮嘴里造型人头,从而给我们提供宝贵的解读钥匙。
礼器上大部分人头造型很小,没有细节刻纹,所以大禾方鼎、侯家庄和琉璃河面具的每一细节都重要而不应忽略,包括眉毛与人中的刻纹应该隐藏面相意义,但不是按照晚期的相面术象征长寿,而是在“长寿”之前的观念里,隐示巫师再生通天的能力。从这一角度来看,巫师面孔造型文化信仰的根源应该还是长江中游远古文明体系。下文拟从巫师神杀的造型,进一步分析此信仰的细节。
[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贺刚、向开旺,《湖南黔阳县高庙遗址发掘简报》,页4-23。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页84—85。
[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舞阳贾湖》,页656—701。
[4]杨华,《三峡新石器时代埋葬习俗考古与同时期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四川三峡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页10-18。
[5]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松滋县桂花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6年第3期,页187-196、160、216-218。
[6]石河考古队,《湖北省石河遗址群1987年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页1-16。
[7]湖北省博物馆、武大考古专业、房县文化馆、王劲、林邦存,《房县七里河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页1-12。
[8]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硏究所石家河考古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著,《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页63-,图四二
[9]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研究(4300B.C.-2000B.C)》,页157-161。
[10]孙其刚,《考古所见缺头习俗的民族学考查》,《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8年第2期,页84-96。
[11]严文明,《涧沟的头盖杯和剥头皮风俗》,严文明,《史前考古论集》,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页335。
[12]北京大学、河北省文化局邯郸考古发掘队,《1957年邯郸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10期,页531-536、588。
[13]严文明,《史前考古论集》,页234-338。
[14]参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页192—193。
[15] James Mellaart. ÇatalHüyük: aneolithic town in Anatolia.
[16]郭静云,《透过亚洲草原看石峁城址》,《中国文物报》2014年1月17日。
参见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页554-560。
科技考古视野下的二里头遗址生活制造业
虽然二里头遗址制铜和制玉技术在当时已相当先进,但青铜器和玉器依然属于稀有物品,主要作为祭祀的礼器以及随葬的贵重物品。而社会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兵器仍然主要是石器、陶器和骨器。我要新鲜事2023-05-26 23:17:550000张经纬:张光直:考古学领域最后的巨人
巨人之躯2013年时,三联书店再版了张光直先生系列作品(全九册),是迄今国内出版先生作品最全面的一版。作为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考古学界最富国际声誉的学者(曾任哈佛大学人类学主任,荣膺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光直先生这些作品大多写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在八十年代以来便陆续译成中文。时值先生去世十二年之际,重读作品,历久弥新。我要新鲜事2023-05-28 05:09:260000大龙:欧洲大型恐龙(长4米/最早的坚尾龙类恐龙)
大龙是一种兽脚亚目下的坚尾龙类恐龙,生存于1.75亿-1.67亿年前的侏罗纪中期,体长虽然只有4米,但是在侏罗纪中期的时候,大龙也算是所有肉食恐龙中体型最大的品种之一,体重可达200公斤,在当时算是一方的霸主。第一批大龙化石出土于英国。大龙的体型我要新鲜事2023-05-09 18:33:320000王羲之故居惊现古墓,墓主人是三个小孩,疑似与“冥婚”有关
王羲之故居之下惊现一座神秘大墓,墓葬之中竟有三具孩童尸骨,他们究竟是谁?与王羲之有没有关系?层出不穷的随葬器物,意外牵扯出一段离奇的“冥婚”事件,这座墓葬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别着急,关注小古,带你一起了解古墓里的那些事儿。我要新鲜事2023-06-15 20:17:36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