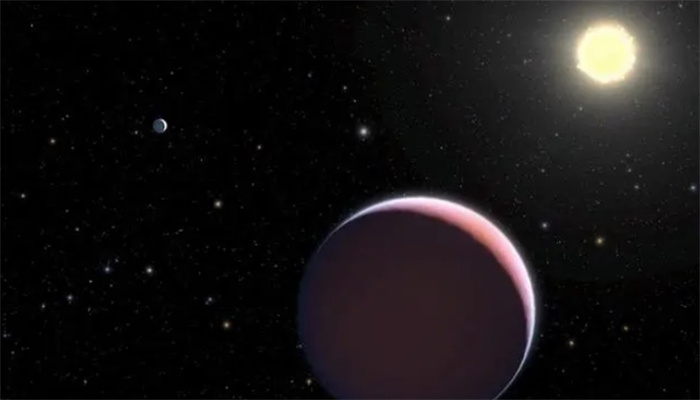郭静云:从信仰到哲学、从哲学到新的信仰
【编者按】本文摘自郭静云著《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下编之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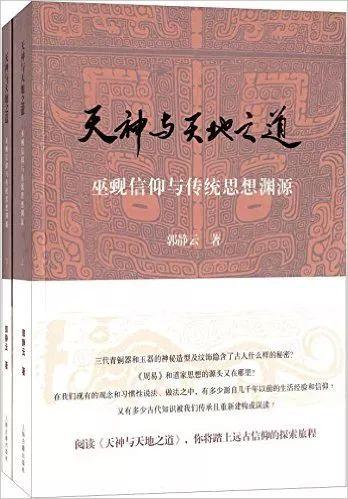
下篇讨论很多抽象概念,发现战国百家所争鸣的命题,实际上都源自上古信仰的脉络。我们的讨论尚不全面,除了我们所提出的几个概念,还有其它,如“德”、“圣”、“礼”等等也有甲骨金文的根源,在这方面还需要作更细致全面的研究。
不过这一套论述,我们可以归纳出几项要点。
第一,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易和道的传统似乎最源远流长,滥觞于先商时期的精神文化。至于早期儒家和法家,因为多集中于社会问题,所以更符合讨论当时的社会背景,即便如此,还是蕴含了一些源自上古的观念[1]。其余百家思想渊源的问题,都需要很多功夫作细致研究,也未必能回答很多问题,但是一定会发现原来没有想到的问题的存在。
第二,上古信仰中有很多形象和偶像,其中很多有神兽的形状,能组成很多造型。但与此同时,已形成了一套不可造型或造型不具象的概念。用形象思考的方式是上古观念的特点,但其并不排除用概念范畴的思考方式,这两种方式互补相成。所以一方面商文明塑造很多龙的具象造型,以描绘天神的存在,而同时用抽象的“神纹”,将龙形象以符号来表达;另一方面塑造龙和龟的相对造型,用来表达从上者降、从下者升以相交的概念;同时将“明纹”符号刻在高处表达上升,或创造抽象的“神明纹”寓意天地之交;并且用祭礼活动也表达“神”与“明”相辅的目标,从安排祭礼的时间、到所用祭牲的颜色和种类等方面,都是在用不同的象征语言表达信仰的重点。这种语言中有造型形象、刻纹符号、字形、礼器和牺牲的颜色、祭礼的时刻、采用的祭法以及其它我们已难以厘清的作法。从卜辞另可见,商王经常向先王祈求对事情的支持,同时也会祈祷抽象的“下上”,又向无名的对象祈求引導,这些祈祷与祭礼并不抵触,而是构成一套历代虽有变化但仍可以看出其连贯性的信仰和祭礼体系。
第三,通过一步一步地分析我们发现:商文明的信仰重点在于均衡相配。商文明并不是崇拜独一无二的大神的文明,一切神力都需与其它神力搭配才行。包括独一无二的帝,也必须祭拜其周围的四方;独一无二的“中”的权力并不具有独一的极端性和主宰性,只能通过与“方”的搭配,才获得其重要性。天浩大,但是没有决定生命的权力,只是天与地相配才重要,并且如果天的神力过大,需要多祈祷,用各种神祕方式控制天而加强地的力量,天地相符、相合,才是万事成功的条件。这种均衡相配并不意味着恒定均衡,而是指相对力量弹性机动、互相胜败,但总体还是产生互不可胜的均衡相配的理想,这才是死生、衰兴不绝的循环。这种信仰从各种祭礼活动中都可以看到。
例如殷墟甲骨占辞中屡次出现“下上若,授我祐”祈祷套语,请求上下护祐授权,商王祈祷“下上若”的重点不在笼括祭祀上下所有的神祇,而在于祈求天地交互,以上下共同授祐,来保障王事的成果。甲骨文又载:“呼神耤于明”,即表达神降而明升之相对性以及相辅作用,进行此礼仪之地称为“明”,恰恰相对于卜辞所呼祈的“神”;在神祕的占卜记录里,很多细节并非偶然和无意义,所以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此处之“明”,大约是指某种空间概念,同时也指太阳初升时段,借助太阳升起之力与天相交通,带去人间的祈求;并且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天神地明相辅才有“生机”,所以亦保证有受年。甲骨文另有很多用不同颜色牺牲的记录,其中的幽与黄相对,显示了殷人以幽、黄牺牲来象征天地相配的神力,追求天地平衡相合的状态。《易‧坤》“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用形象语言表达天地相配,而殷商用幽和黄牺牲的祭礼,以牺牲的血体现这一形象。
从这些祭法可见:“相配”是商文明信仰的崇高理想,其也影响整个先秦信仰及思想。两极之间所产生的“和”是中国文化传统思想的核心所在。虽然从殷商以来经过多次集权帝国时代,但多元的中国文明始终没有放弃上古文明观念的基础,即“和”的均衡概念;虽然历代帝国张扬天子的崇高位,但君臣“合德”的理想一直被看作是社会思想的重点。
必有下才能有上,如果不重视下,上也无价值,上下不合根本无生。必有四方才能有中,以四方的价值确定中央的价值;各有其权,各有其责,中与方相合才是稳定的空间。必有子才能有父,重视子才能重视父的地位,互相各有其责任。必有臣民才能有君,重视臣民才能重视其君的地位,君臣互相各有其责任,君臣为一德才能有稳定的国。这是从自然到社会一套完整的观念,在先商时期已可见其滥觞,所以非常古老、非常深刻,而一直未曾被完全打败。也正因为有如此意识,过度极权的秦或新朝不能长久。当然,汉武帝极权的程度不弱于秦,但是他还是必须得保持上下平合的包装,而采用很多非直接的政治手段,这就是文化基础的需求:直接极端不能成功,一定要达成上下之合的中庸。
虽然迄今所能看到的较完整的资料只是从殷商才开始,我们却不能依此以为上下合的概念源自殷商。殷商只是中国最早尝试建立帝国的王朝,反而强调一元概念,所以上下平衡与相合的观念不可能是殷商所创造,而是孕育于早商或更早的长江中游上古文明的深厚土壤中。此一基础始终在礼仪中留下痕迹,直到战国时期进一步成为百家讨论的重点。
商王祈祷“下上若”,用“”(上者在下而下者在上)的顺序,而后来在《易》的传统中用结构相同的泰卦(——上干在下而下坤在上),表达“上下交,而其志同”的理想。可见,不仅在观念上如此,所用符号也表明这是一脉相承的文化。
清代段玉裁讨论《易》的“天乾”概念,假设:“上出为干,下注为湿。”甲骨卜辞也基本上证明他的假设,并显示上与湿的相对概念,也应源自上古,最初所表达的应该是长江中游的自然地貌:上为干的岗丘,而下为湿的低地;在文化整体化的背景下,形成《鹖冠子》所言:“天燥而水生焉。地湿而火生焉。”天气不湿但生雨露;土地湿润,但生日火。在易学传统中“乾”、“坤”二字正好构成天干地湿的相对意思,象征完整的天地宇宙,以及《易》经中自然现象彼此相对而互补的规律。
天生水地生火的形象,实际上可能是表达上古信仰与思想中最关键的概念:“神明”概念。在今人看来,“神明”即指神靈或大神的概念,但是,在先秦观念中,“神明”是以两个相对范畴组成的复合词,以此表达一种自然造化的过程,而并不是作为某种祭祀对象存在,也不表达神祇和鬼神的意义。古人认为,天地万物化生是因为神明的存在,但并没有因此而将神明视为崇高神,因为“神明”指的是天地之交、天地之间的媒介,是天神与地明的相合与交流。其“神”的范畴涵盖恒星神光与天所降神靈雨的神气,而“明”的范畴涵盖出自地的日月明形,二者互补相辅才能生育万物,所以“神明”所反映的实际是古人的“生机”概念。天地不交,则无生机;有神明之交,天地之间便有了生机。所以天地万物化生皆奠基于神明、由神明来决定,但绝不能因此而认为神明是个大神。“神明”之结合表达天地“合德”状态,天地合德才有万物之生机。
古人观察大自然而得出这样的认识:自然“神”是养万物之甘露、神靈雨,而自然“明”是温暖万物之日火;天的生物都是水性的精气,也就是所谓的“神”;而日月二明皆有凝结的火性的形体。如果天的力量强,而地不足,则由天所降的神水质霖霪暴洒容易造成水灾;如果地的力量强,而天不足,则由地所出的明火质如太阳过强干旱容易造成火灾。在这两种情况下,对生态都会有很大破坏。也正因为如此,上古信仰并不是寄命于天或寄命于地,而是追求天地之合、与其志同,相配天地“神明之德”。所以“神明”概念与“下上若”、“泰”和“乾坤”概念是同一套大体系。笔者甚至认为,先秦宇宙观是以神明观念为基础的。
不仅宇宙观以神明为基础。古人认为,人生与社会皆取法于大自然,所以无论是在自然、人生或社会生活中,“神”与“明”均是上下互不可缺的范畴。神明观从大自然扩展到社会,乃成为礼制与孝道的神明观,其观念的滥觞亦可见于商周信仰礼仪中。
宗庙青铜礼器的铭文皆表达祖孙关联不断的目标。子孙祭祀祖先,以实现其“明德”(概念“明”表达通天的能力,所以“明德”是能够通天达神之德),供献“明器”(具备通天达神能力的祭祀之器),以此从下面的立场实现上下之交;并同时祈祷祖先将神德(元德、懿德)保祐子孙。先祖之靈降福于子孙,而子孙“治宗庙”、“秉(供)明德”,以追孝于先人。此“礼”因为以宗庙为出发点,故其功能与“孝”的功能一致,人们秉执明德而孝于神,故在守持神明之德的“节事”、协龢方面,孝有颇关键的作用,此即《孝经‧感应》所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从西周以来,礼制“神明”观取法于自然“神明”观,且其目的是:社会学天地,保持象天地一样永久的生机。礼制神明观强调:配天地神明之德,以追求家族世世昌盛之生机,并将此概念从家族的生机,扩展到跨血缘关系的社会与国家。从战国到两汉儒家礼学,仍沿着西周礼制取象于天地的作法,而模仿天地“和德”的规范,追求天与天下的沟通以及国家的调节和稳定。
这一套是自然与社会合为一体的“神明”观。商周时期人们通过各种礼仪表达它们的神明观,并追求天地之合、通天达神而获得天恩保祐。例如在象征天的幽与象征地的黄两种颜色之间,另加白色以象征地的产物有升天的能力,作地与天之间“明”的媒介。因此,古人采用白毛与幽(青)毛的牺牲以祈祷升天的成功,如死者升天(为此而普遍以白色为丧色)或祭礼到达天界的目的。“白幽”的意思,乃祭礼犹如白日通天达神,明火在天上,因此自天上回降天祐的“大有”,即大有卦的《象》传所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从天所降的保祐神恩,是人们所不能掌握和管理的;人们所能掌握的只是通过从地祭天之礼,以祈祷其礼能有象日一样的升天能力,因此白色为人与天之间的媒介。同时,在商文明祭礼中,黄色与白色的相配,乃象征从黄土中白日升天;死者乘日升天,以及晋卦的《彖》传所言:“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到了汉代以后,“黄白”一词专门表达升天,指出成仙方术。
可见,上古信仰在战国文献中被思想化,从此前的祭礼系统演变成为思想理论。战国时期是百家争鸣的哲学时代,百家思想不一,但他们形成的背景一致:即奠基于商周文化观念,所以百家所讨论的命题一致,这样才能够辩论、争鸣。但是,信仰与该信仰所衍生的思想,两者之间有核心的差异。首先信仰只能遵从、实现礼仪,而不能被讨论;思想对信仰的命题则可以开放讨论。其次,信仰使用形象、象征等语言,既神祕又具象,可以造型和偶像化;思想则是用概念表达,不为偶像。第三,因为使用概念,所以逐渐脱离其原来形象的具象性,循着思想逻辑推理,从概念又发展出新概念,概念之分合已不会再顾及原本形象之间的关系。
这样,在上古信仰的基础上,便形成了百家哲学思想。以神明为例,哲学“神明”概念很快跨越了其天降神、地出明的本义,而进一步塑造出很多哲学理论。礼制神明观在儒家礼学中得以发展,自然神明观则被易学与道家着重讨论。战国早中期思想家的讨论,还是接近于原始神明观的意旨,但是循着抽象概念的演化,战国晚期所讨论的神明观,其内涵越来越丰富,远超其本义。
例如在道家思想脉络中,“神明”从“天地”所生的范畴,发展为“道”所生的“一”概念,又跨越天地而成为天地之前的“本体”概念,成为天地、万物合德的榜样。另外,在道家黄老学派思想中,神之要素,虽仍相关于天界,但不再被视为位于自然世界之从天降地,而更多用于指涉位于万物之内心;明的要素,虽然仍相关于地界,但不再被视为位于自然世界的下地而升,而更多用于多指涉万物之外状,强调明显可见的形体概念;由此而将神明概念从原先用于指涉天地合德状态,发展为指涉万物内外表里一体的状态。
战国晚期以来,思想的发展均有两种方向:宏观总体化和微观各物的观察,“神明”观念也同时经过这两种变化。在宏观化的思想中,“神明”成为天地宇宙的榜样、至上的本体;而在微观化的思想中,“神明”成为各物的内外结构。不过,由于内与外互为表里,不可单独存在,故可谓神以明创气,明以神造形,二者相辅而为万物生机之本。既然神明既在内又在外,故其既能隐藏精神,同时亦能作了解奥祕内精的依据。从此,在进一步推理下,形成了黄老学派和荀子所发展的神明认知论。荀子发展神明认知论,将神明囊橐于人心里,以此为基础,至汉代演化出“神明在人”的思想。
不过,到了汉代,百家思想已然退缩,而上古信仰中关于“神明”的本义已被忘记。神明作为无所不及、无所不包的“本体”,在汉代不知其根源的人眼中,已变成为崇高神祕的对象;“神明在人”的说法更显神祕。是故,在上古神明观的残迹上,重新出现了新的信仰观念。但这种新的信仰已与上古毫无相似之处,神明变成为圣人、仙人或崇高神圣偶象,如成语所言“敬若神明”、“举头三尺有神明”。这又反过来使后人完全遗忘上古神明观念,以至于对先秦文献中记载的上古神明观变得不理解,而对先秦文献的解读有落差。在此情况下,只有先秦一手文献资料的出土才有助于我们理解神明之本旨。
从上述关键演化过程可见:上古信仰经过哲理化后,又重新回到信仰的形式,但早期和晚期的信仰,形同而实异,用字相同,用义相异。这种从信仰到思想后又到新的信仰的演化,可能是中国大文化的特点。例如在同时期地中海文化中,也有上古信仰哲理化的趋势,但罗马时代新兴的信仰已较少用前期思想概念,反而强调全新的“真理”,严格否定以前所有的信仰,虽然在观念上仍然有很多传承自远古,但在表达方面却避免用以前的思想范畴。而在同时代的中国大文化中,虽然佛教进来后也带来了全新的“真理”概念,但与此同时对远古圣王的崇拜、对儒子的崇拜等过去文化的理想并没有被扫除,而重新被信仰化,思想概念也循此而发展为新的信仰范畴,表面上声称这信仰是自古传承,实际上新义与原义离得很远。
在从信仰到哲学,再从哲学到信仰的转化过程中,道文化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商文明中“道”的信仰重点是“上導”,即强调来源不明的“導”,一种崇高的指南,可以引導商王选择准确除灾的正道,商王祈祷出行之前能掌握“導”的指南。以此信仰为基础,老子学派建立其思想体系。因奠基于上古信仰的土壤,道家思想从一开始就以神祕不可解通的概念为基础,但是循着思想化的发展而试图讨论他,追求更加了解他。这种讨论提出了很多不同的假设和解释,老子思想的继承者也因此而逐渐分成不同的派系,各派坚持不同的看法和角度,所以对原本“道”概念的理解趋于多样化,并经过不断的逻辑推理,越来越忘记其本义,而形成无所不集、无所不包、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本体”概念。其“本体”概念与其它概念联合,并在统一思想的思潮下与其它“本体”概念混合和等同,如“太一”、“元气”、“恒”、“阴阳”、“神明”等。“道”的概念从一开始就有神祕不可知的成分,后来又不断用于涵盖那么多不同的概念和理解,而使“道”的概念变得更加不明,进一步演变成为与上古完全不同的新信仰。
上古道信仰绝不为象,这是商王祈祷获得来源不明的正道之“導”,是一种没有具象化,所以不能被祭祀的神祕真理。在商文明的信仰中,“導道”的信仰最抽象。老子的“導道”亦如此,掌握正道的理想,了解事情的内理,绝对不会有偶像的崇拜。但是汉以后的道教是多种偶像崇拜的信仰,虽然继续用“道”字作信仰的崇高范畴,但其信仰内容已完全不同。这就是从信仰到哲学,再从哲学到新信仰的演化:外在与用词虽然仍旧相同,内容却已大相径庭。这种情况最容易造成以后期的现象去误解上古的含义。
[1]有关儒家从上古传成命题的探究,笔者曾经做些讨论,参郭静云,《亲仁与天命:从缁衣看先秦儒家转换成“经”》。
俗话说,“人点蜡,鬼吹灯”,考古人员在盗墓现场真看到了这现象
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本文作者倪方六俗话说,人点蜡,鬼吹灯。有部盗墓小说便以“鬼吹灯”为名,文学化地讲述了盗墓故事。真有此事么?“鬼吹灯”我没看到,但“人点蜡”确是存在的。这在现代考古中,不只一次看到过这种现场——盗墓现场出现了点过的蜡烛。这篇“梧桐树下戏凤凰”头条号要说的被盗古墓现场,便看到了这现象。我要新鲜事2023-05-26 16:59:150000唐际根:《真假铭文:商周青铜器铭文辨伪》序
我要新鲜事2023-05-26 10:04:290000查洪德:全辽金元笔记(第一辑)总序
《全辽金元笔记》是辽金元笔记文献之汇集整理,汇编、点校全部现存辽金元三代笔记文献。所谓笔记,是指那些没有严格体例、信笔记录摘录而成的著述,是古代文献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其中蕴含有大量信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历来为研究者重视。辽金元三代笔记,特别是其中的元代笔记,又因其历史文化的特殊性而具有独特价值。我要新鲜事2023-05-25 16:48:490000湖北“芈月哥哥葬地”发现古墓,盗洞刚好挖在棺室,出土特别之物
一块有墓趣的墓砖本文作者倪方六今天来说一座墓,如果不是葬地特殊,又出土了特别之物——一块字砖,估计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座墓发现于1977年的湖北,当时正是中国农村转型的前夜,如今的村、组编制,当时还叫大队、生产队,农民仍是大集体,重视平土整地。我要新鲜事2023-05-26 18:11:270000与四大文明并称的玛雅古文明,是怎样灭亡的?
关于玛雅古帝国[1]的衰落和灭亡,各方面的专家提出了诸多不同的原因——地震;极为剧烈的气候变化;疟疾和黄热病的反复流行;外族征服、内战。在建筑和雕塑方面经过一段时期的强制生产之后,古玛雅人的智慧和审美能力枯竭,随之而来的是相应的社会衰败、政治衰落和政府解体;最后,由于古玛雅人的农业体系未能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而导致经济崩溃。让我们更仔细地研究每一种说法,然后再在它们之间选择取信哪一种观点。我要新鲜事2023-05-26 03:49:29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