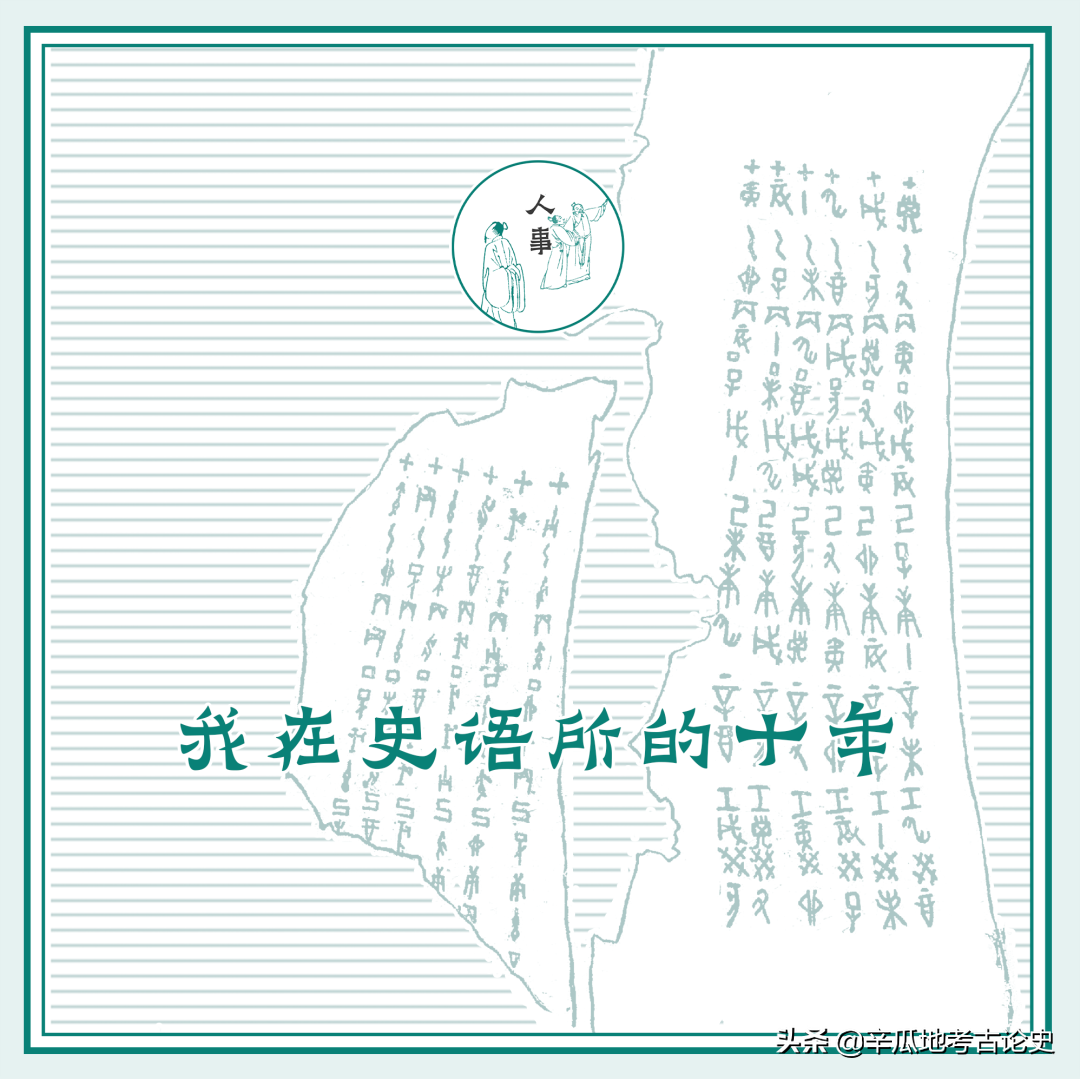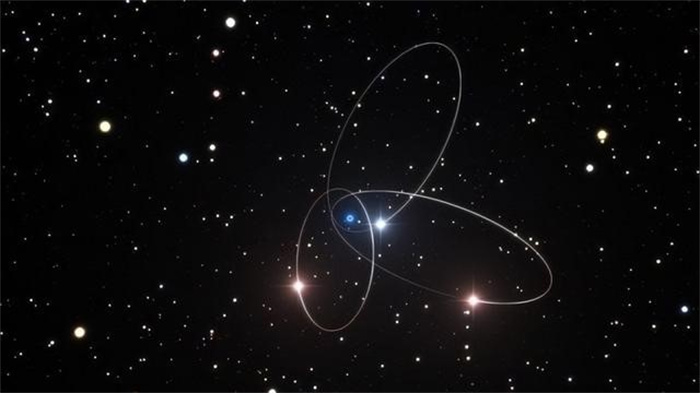史念海:河西与敦煌
黄河自青海东流,至甘肃境内即斜向东北流去,故甘肃西北部历来就被称为河西。敦煌居河西的西端,与武威、张掖、酒泉并列,为赴西域的门户,在历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数千年来亦颇有演变,今略论其递嬗之迹,谅为关心这一地区的人士所乐闻。
一、远古时期有关河西的记载及其解释
自张骞通西域后,河西始见重于当世。其实,在此以前,已经有了有关河西的记载。出之于战国时人士之手的《尚书·禹贡》篇,所论述九州中的雍州,就明确指出其西界为黑水。黑水所在,历来解经者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既是雍州的西界,当于今甘肃西北部求之。《禹贡》的作者曾说:“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今甘肃西北部皆在黄河以北,作为雍州西界的黑水如何能越过黄河而入于南海?这个千载难破之谜,迄今依然不易得到适当的解释。道黑水所至的三危,《禹贡》中曾两次提及。其中一次也在雍州,即所谓“三危既宅,三苗丕叙”。窜三苗于三危,亦见于《尚书·舜典》。伪《孔传》说:三危,西裔。确地未能实指。郑玄引《地记书》,谓三危之山在鸟鼠之西南,当岷山。则在积石之西南。孔《疏》虽谓《地记》乃妄书,其言未必可信,却还说:“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今敦煌市城之南有三危山,逶迤蜿蜒,其势非小,说者谓即三苗所窜的三危,这是和解经者所说不尽相同的。
不过以三危在敦煌也并不是毫无来历的。《左传》襄十四年,晋范宣子数姜戎氏说:“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开瓜州。”又昭九年,周詹桓伯辞于晋,也曾说:“允姓之奸,居于瓜州。”这都是晋惠公由秦东归,迁戎于伊雒流域近于周王都城雒邑所引起的问题。允姓为阴戎之祖,也就是后来的姜戎氏。杜预解释说:“瓜州在今敦煌。”两汉魏晋时,敦煌为郡,其治所在敦煌县。敦煌县故城在今敦煌市西南。杜预在说到“允姓之奸”时,还特别提了一笔,说是与三苗俱放于三危。杜预这句话并不是随便说的。因为詹桓伯辞晋,在说“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之前,先说了一句:“先王居祷杌于四裔,以御魑魅。”祷杌为舜时四凶之一,四凶中包括三苗。既云四裔,当然也涉及三苗流放之地。经杜预这样的解释,三危山就由河南移到河北,而且具体确定到敦煌来。
以瓜州在敦煌,并非杜预所创始。这是东汉初年杜林的说法。《汉书·地理志》敦煌县的注文说:“杜林以为古瓜州,地生美瓜。”颜师古更作补充说:“即《春秋左氏传》所云‘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者也。其地今犹出大瓜,长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
其实,瓜州之戎并非就在敦煌。这一点顾颉刚先生曾有论及。颉刚先生提出五大理由以驳斥旧说,可以成为定论。颉刚先生说:秦穆公都雍(按在今陕西凤翔县),去敦煌三千余里,如姜戎在敦煌,与秦何干?何劳师远征。这是理由之一。其二,自雍至敦煌,其间戎人至多,秦安得越国长途远征?其三,如果秦国西征,戎必更向西奔,何至反东向入秦,劳晋惠公诱之?其四,如秦地于穆公时已至敦煌,何必张骞专美于后?其五,秦始皇统一大业成就,如秦已取得敦煌,始皇何故不一言及?颉刚先生还特别指出:地出美瓜者多矣,不只敦煌,如杜林能更向西游,则瓜州将必不在敦煌[601]。虽说如此,但在以前由于杜林的说法几成定论,后魏明帝时竟于敦煌设立瓜州,经过一度改名,瓜州还是成为定称。隋初重定疆域制度,曾经罢郡存州,后又罢州置郡,其在存州之时,仍用瓜州名州。唐初于敦煌设立沙州,移瓜州于晋昌县[602],其地在今甘肃瓜州县东南。后来瓜州的名称还是沿袭下去,一直到了元代[603]。不实之辞,竟然影响这样的深远,就是到现在,也还有人以此为故实,而频繁的称道。《禹贡》于黑水、三危之外,还提到弱水、猪野、合黎和流沙。《禹贡》述导水,是先说弱水而后才提到黑水。可见弱水也是一条大川。后来释经者以今张掖河相当于弱水,这大体上是可以说得通的。确定了弱水,合黎山和流沙都可有了着落。今合黎山在张掖西北,张掖河绕合黎山之西而北流,是和《禹贡》所说相符合的。张掖河下入居延海,其周围皆为沙漠,正可以之解释所谓的流沙。历来释经者以猪野为今甘肃民勤县北的白亭海,揆诸事理,也是相当的。可以说《禹贡》的作者对于雍州的西部,也就是后来的河西,虽然不能像对当时其他诸州那样的了若指掌,基本上还是相当明了的。因为这里当时可能还是从事游牧的族类所居,和内地诸侯称雄的局面不同。后来张骞的西使,正是在这样前提条件下前往的。
二、独特的自然环境及其演变
论河西较为明确的历史,应从汉武帝建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时肇始。四郡建置之前,汉的西北边郡为陇西郡。陇西郡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县。由陇西郡西北行,依次可以达到这四郡的治所,但偏向西北的角度却不尽相同。武威郡只在陇西郡稍偏西北处,张掖郡之于武威郡,酒泉郡之于张掖郡,就都更偏于西北。而敦煌郡和酒泉郡又几乎正为东西相对的局势。四郡逶迤相连,大体成为中间稍微向北突出的弧形。《禹贡》称道河西的山,只说到三危山和合黎山。三危山能够为《禹贡》的著者所重视,并非由于其山的雄伟崇高,而是因为它为黑水流经的地方和三苗放逐的所在。它只能算是祁连山的一个小支脉,论河西诸山一般说来是数不到的。河西最大的山应为祁连山。匈奴人呼天为祁连,故亦称此山为祁连山[604]。以祁连名山,可知其确为大山。今其主峰海拔为5924米,为邻近诸山所难于比拟的。《禹贡》所称道的还有合黎山。合黎山在今高台县北,居于张掖和酒泉间,其海拔仅2504米。不仅无祁连山之高,抑且无祁连山之长。论者称河西四郡为河西走廊,以其在祁连山和合黎山之间。祁连山自敦煌蜿蜒至于武威,堪称一方的屏障。这条走廊之北,合黎山东西固然还有龙首山、北山等山,共同起着屏障的作用。然各山之间互不相连,阙口亦复不少。汉唐诸王朝经营河西,每谓借此可以隔断羌胡,也就是说阻挠青藏高原和瀚海南北从事游牧的族类使之不能互相接近和联系。事实上,祁连山南从事游牧的族类诚然不易越山北向,而北方的匈奴、突厥、回鹘等族皆尝南向牧马,往往徜徉于合黎山南各处。这固然显示出当时国力的强弱,亦地势使然也。
自河西四郡先后建置之后,内地人士对于当地的了解,远较《禹贡》作者为深入。即以河西的河流而言,亦不复以弱水为限。由东徂西,则有流经现在古浪县的松陕水,流经今武威县的谷水,流经今张掖县的羌谷水,流经今酒泉市的呼蚕水,流经今玉门市西的籍端水及冥水,还有流经今敦煌市的氐置水。这些都是内陆河流,下游或入泽,或入海。其实所谓海也就是泽。松陕水是入海的。其他皆入于泽。谷水入休屠泽,弱水、羌谷水、呼蚕皆入居延泽,籍端水和冥水入冥泽,氐置水则入于无名的泽中[605]。谷水今为石羊河。弱水和羌谷水今为张掖河,张掖河亦称黑河。呼蚕水今为北大河。籍端水今为疏勒河。氐置水今为党河。至于松陕水和冥水今已绝流。就是松陕水所入的海,氐置水所入的泽,以及籍端水和冥水所入的冥泽,亦皆湮失。休屠泽更是往往干涸。居延泽则已分为二处:苏古诺尔和噶顺诺尔。这两个诺尔中间有了隔离地区,显示出原来的居延泽已经有所缩小了。
这些泽或海的缩小和消失,为时并非很久。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胡林翼请邹世诒等编制的《大清一统舆图》,犹能显示出这些泽或海。松陕水所流入的海,在此图中称为白海,谷水所流入的休屠泽,则称为鱼海。此图中玉门县北有花海子、布鲁湖、青山湖。布鲁湖居中,东为花海子,西为青山湖,三湖贯通,连在一起[606]。大体就是冥泽演变而成的。胡林翼图上已称氐置水为党河,党河流入哈拉池。哈拉池应是氐置水所入的泽。其实也不尽然。哈拉池位于敦煌市西北,更在玉门关遗址以西。氐置水则是由汉时龙勒县流向东北[607],则其所在地应在今敦煌市北或稍偏东北处[608]。至于居延泽,胡林翼图上已经分成东西两海了。同治二年之后又70余年,为1934年,原来松陕水所入的海,即清时的白海,虽有残迹,已经常无水。籍端水所入的冥泽,也久已干涸,惟谷水所入的休屠泽,即清代的白亭海,仍见于当时所绘的图中。居延海虽分为东西,哈拉湖稍有东移,储水仍未竭涸[609]。
是什么原因促成这些泽和海干涸和消失的?问题可能相当复杂,气候过于干燥也许是其中一个因素。可是问题显著的形成却是在由现在上溯的125年之间,说得更严重的是在最近五十余年间。百余年来或五十余年来气候能有如此显著而剧烈的变化,殆属不可能。斯坦因在探索额济纳河(即弱水)下游居延海附近黑城子荒废的原因时,指出是由于灌溉的困难。而灌溉之所以失败,可能是由于额济纳河水量的减少,也可能是由于河流在渠头处改道,而垦地因为某种原因以致不能得到充足的水量。斯坦因对此没有再作结论。灌溉渠道的更动以至于河流的改道都可促使灌区的荒废,这一点到后面当再详述,这里姑且暂置不论。斯坦因虽对这两种可能性未作结论,但他却提到额济纳河中游毛目垦地荒废的原因。毛目在金塔县东北。据斯坦因所述,这里适宜于维持沟渠,但是过去为了要在春初得到适当的水量,也曾感到重大的困难,因以,以前的垦地就此荒废了[610]。斯坦因虽没有肯定额济纳河水量的减少,实际上却是减少了。
这样的问题在敦煌莫高窟前得到证明。莫高窟前有一条干涸的大泉河河床,河床上架有规模不算很小的公路桥。由敦煌前往莫高窟的旅游者必须过桥,才能到莫高窟下。河西各处不乏干涸的河床,故旅游者对此不至于引起注意。莫高窟的第148窟中有一通《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根据碑文可知此窟是唐大历十一年(公元766年)凿建的,碑也是这一年建立的。碑文说到当时莫高窟的风景,说是“碧波映阁”。这是说窟前这一条干涸河床本来是有河水的。不仅有水,而且水量很大,足以使莫高窟的楼阁在碧波中反映出来。现在这条河道中诚然无水,但这并不能说这里就没有任何水源了。其实这条河道并非完全绝流,仅仅剩下的一条细流,被引用成为一条灌溉渠。莫高窟前绿树婆娑,绿树间栽种若干花草,也足以使旅游者为之流连。这样一条细小渠水,如何能够说得上“碧波映阁”?唐大历年间迄今一千二百余年,前后竟如此悬殊,不能不使人惊奇!莫高窟第329窟中有武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据碑文所记,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为沙门乐僔所创始。从那时起,历代都有兴建,规模日趋宏大。大德驻锡,役徒施工,前后不绝,当地如果没有充足水流,曷克臻此。据闻敦煌研究所工作人员饮食用水,尚需运自敦煌市城区,远在千百年前,如何能够有这样的设施?可知能有足以“碧波映阁”的河流,并非始自唐代大历年间,而是前秦始建莫高窟时,就已具有这样的自然环境。
这里的河流水量为什么减少?目前似尚不易得到答案。河流水量来源不外两途:一是地下泉水,又一空中降水。地下泉水若未遇到像剧烈的地震等引起地壳或岩石的变动,就不至于阻断泉水的来源。而近百年来尚未闻及当地曾经有可使地壳或岩石变动的地震,亦未闻及气候有明显的剧变,使降水长期减少,以致影响河流的流量及各自下游所入的泽或海的储水量。按照一般说法,山地森林可以含蓄水分,使所得降水不至骤失,有关的河流的流量亦不至前后过分悬殊。因此不妨略一探索河西各处山地森林的分布。关于森林的分布,一般地理载籍中往往不乏记载。今传世的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成书于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其时下距胡林翼编制《大清一统舆图》仅20年,不妨以之为论证的依据。据其所刊载,河西森林山地有如下各处:
1.雪山,在张掖县南100里,多林木箭竿。
2.临松山,在张掖县南,一名青松山。按:山以临松、青松为名,其上可能多松。
3.祁连山,在张掖县西南。据所征引的《西河旧事》记载,山在张掖、酒泉二郡界上,东西二万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
4.青山,在武威县东250里,山多松柏,冬夏常青。
5.松山,在武威县东310里,上多古松。
6.第五山,在武威县西130里,有清泉茂林,悬崖修竹。
7.燕支山,在永昌县西,产松木。
8.黑松林山,在古浪县东45里,上多松。
9.柏林山,在古浪县东南75里,上多柏。
10.棋子山,按,在今天祝藏族自治县西南200里,相连者为桌子山,道险林密。
11.大松山,按在今天祝藏族自治县东北120里,山多大松。
12.榆木山,在高台县南40里,上产榆树。
13.白城山,在高台县西南80里,有林泉之胜。
这样一些记载,显示出河西的森林山地似乎并不是很多的[611]。值得注意的是祁连山。《大清一统志》引《西河旧事》说,山在张掖、酒泉二郡界上。这是前人的一般说法,《元和郡县图志》也是这样说的[612]。其实并不应以此为限。《大清一统志》又引《行都司志》就指出永昌卫(今永昌县)南的雪山与凉州卫(今武威县)西南的姑臧南山相连,也是称作祁连山的。河西的河流不论其具体发源于何处,总起来说,都是由祁连山上流下来的。祁连山上多森林,就不能不和这些河流的流量大小有关系了。
如前所说,河流的流量来源于地下泉水和空中降水。近一百多年来,这两项在河西不易得到完全了解。只能在与涵蓄水分有关的森林多事推敲。由于人为的原因,历来都有破坏森林的事例。而明代中叶以后,森林的破坏更为严重,黄河中游黄土高原最为突出,这一点我曾经有所论列[613]。应该指出,黄土高原以外的地区,也都难得幸免。上面征引《大清一统志》所记载的山地森林,有些都是根据其前代文献列举的。只不过特别提出《西河旧事》一种而已。它如张掖雪山的林木箭竿,就是出自《元和郡县图志》。这样的征引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河西的森林直至清代中叶还保持当时以前长期未有多少改易的情况。如前所说,这是在同治二年以前20年的记载,说明这些河流流入的泽或海还能保持一定的储水量不是没有理由的。同治二年以后,甚或是在公元1934年以后,这些泽或海有的干涸甚至消失,和山地森林就不能说没有关系,虽然具体破坏的过程和情况都还未能完全明了。河西许多地方近似戈壁中的绿洲,有的地方实际就已经成了绿洲。维持绿洲的生机,利用河水灌溉以前已经取得重大的作用,就在以后可以预见的岁月里,这样的作用还将是不可或缺的。如何能够保持河流常水位时正常的流量,确是一项不可稍微忽视的问题和工作。
河西自然环境的另一特点,是具有相当广大的沙漠和戈壁地区。河西的北方和东北方就是内蒙古的沙漠地区。阿拉善右旗的巴丹吉林沙漠和阿拉善左旗的腾格里沙漠,不仅已侵到合黎山和龙首山之南,而且有的地方也已逐渐接近到明长城,金塔、民勤等县的治沙工作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是不可稍微忽视的。戈壁与沙漠不尽相同,也成为河西发展生产极大困难的地区。由河西走廊东端西行,愈往前行,所能看到的戈壁也就愈益繁多。在戈壁中有的地方还间生着杂草,有的地方竟然寸草不生,真可以说是上无飞禽,下无走兽,因为在这样地方连飞禽走兽也都不容易生存下去,遍地的石块和碎石形成另一种特殊景观。
正是由于有许多沙漠和戈壁的地区,当地人民的居住和生产就不能不受到影响。愈往西去,这样的影响就愈益显著,敦煌及其附近各地更是如此。显而易见的是居民点的分布很不均衡。西汉时,敦煌郡设有六个县,绝大部分是集中在籍端水和氐置水的下游。这固然是近水之地容易引水灌溉,也是近水地方不至于有很多沙漠和戈壁。西汉如此,唐代亦然。唐代的沙州虽是在汉代敦煌郡的基础上设立的,其实只有敦煌郡的一半,其东部另外设了一个瓜州。唐代的沙州除辖有汉代敦煌郡西部一半外,更向西扩展,其西境直达到且末城,也就是现在新疆的且末县。辖地虽然扩大了几倍,实际只设了两个县,就是敦煌和寿昌。敦煌是西汉时的旧县,寿昌则是西汉龙勒县改称的,还是没有能够远离氐置水。
全面积改造沙漠和戈壁是一项极难奏效的工作。但人总是有改造自然环境的意愿的。只要能够有机会、有可能也是不放过的。由柳园到敦煌市城区的大道上有相当广大范围的戈壁,而柳园和敦煌城区则是肥沃的绿洲。戈壁和绿洲都是自然形成的,当然不能都是整整齐齐的像刀截过的一样。可是这里的戈壁和绿洲之间虽不能说像刀截过的一样,却是整整齐齐十分明确。这当然是经过人为的加工的,说明当地的人对于沙漠和戈壁时时在想方设法加以治理。但自然环境也时时在演变之中,不一定就符合人的意志,甚或和人的意志背道而驰,出现了相反的结果。就在敦煌市区之外有过明显的反映。现在的敦煌市区据说是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由于党河决堤,冲毁旧城,才新建起来的。旧城在党河之西,是汉敦煌郡和唐沙州的治所,一般就称为沙州老城。现在敦煌县城党河以西,虽还有些绿洲,但戈壁却已是一望无垠了。汉代的龙勒县亦即唐代的寿昌县,也都成了戈壁。其间固然还有若干小块绿洲,由于范围太小了,起不到若何巨大的作用。像这些地方的戈壁,其形成的时期是不会太久的,可能是当地居民离开以后才有的。
绿洲的形成主要是有赖于水流的灌溉。一条河流在常水位时,可资灌溉的水量是一定的。绿洲人口过多,可资灌溉的水量自然难以满足。原来在下游的人往往会舍弃其田亩,改移到较上游容易引水处另行开垦新地。原来下游已种植的土地就难免荒废[614]。曾经耕锄的土壤逐渐为风吹走,虽然不至于马上成为戈壁,沙化恐怕是难于避免的。
绿洲是肥沃的土地,如何珍惜土地,保持其肥力,不使之沙化,可能是这个地区不应忽视的问题。
三、居住于河西的族类和人口数字的增损
河西夹处于祁连、合黎两山之间,又当东西交通的孔道,故来往居住于其间的族类相当繁多,而且还不时有所变化。这样的变化对于河西各方面都会发生影响,这是关心河西的人士所不应忽视的。
论述这样的问题必须从头谈起。根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最早出现在这里的是月氏和乌孙,接着则为匈奴人。张骞出使西域时,匈奴已驱逐月氏而据有其地。张骞的出使就是为了联络月氏和汉朝共同对付匈奴。据张骞所说,月氏始居敦煌祁连间。张守节解释说,初月氏居敦煌以东,祁连以西。又说凉、甘、肃、瓜、沙等州本月氏国之地。这五州的治所就是现在的武威、张掖、酒泉、安西和敦煌。是河西之地由东迄西本来皆是月氏的居地。张骞初次由西域归来,得知乌孙本为匈奴西边小国,拟招之益东,使居故浑邪之地。此事见于《史记·大宛传》。匈奴浑邪王故地,汉已设为张掖郡。张骞这样设想,只是为了联络乌孙,共断匈奴的右臂。可是在《汉书》中却另有新意。《西域传》说:“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张骞传》则说:“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至于谋求乌孙东迁,则是因为“蛮夷恋故地”,故“招以东居故地”。是乌孙原来所居之地不限敦煌一隅,而达于张掖郡。如果乌孙故地东至张掖郡,则如何能与月氏“共在”,也是一个问题。关于乌孙和月氏的初居地,学者间早已有所论及,日本学者也曾发表过宏论,似宜再作深入研讨,不过已非本文范围,故暂不再赘陈[615]。
乌孙和月氏是否就是河西初民?目前未闻多所议论。《史记·大宛传》说:“大月氏,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汉书·西域传》也说:“乌孙,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显然都是以游牧为生的。游牧族类不娴于农耕,或者根本不谙于农耕,可是1985-1986年,在民乐县城北27公里发掘的东灰山文化遗址,却显示出另一种境界。在这个遗址所发现的有炭化小麦和大麦,还有高粱和粟、稷。据测定距今5000多年[616]。这样多的农产品不是游牧族类所能够种植和收获的。应该说,河西曾经居住过月氏、乌孙和匈奴人,只是根据史籍的记载,但他们并不一定就是河西的初民。
西汉中叶,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这是河西一宗大事。浑邪王降汉后,汉设五属国以处其众。五属国分隶天水、安定诸郡。张骞说汉武帝:“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617],就是指此而言。但这并不等于说,河西从此就没有匈奴人了,实际上匈奴在河西的影响还是相当深远的。浑邪王降附后,汉在河西设了武威等4郡和35县。有些郡县名称分明是采用了外来语。当时不仅设了敦煌郡,还有敦煌县。敦煌郡治所就在敦煌县。敦煌二字作何解释?东汉时应劭曾经说:敦、大也,煌、盛也。以敦作大解,见于《扬子方言》。以盛释煌,可能就始于应劭本人。这样的解释,总不如武威、张掖的确切,更不如酒泉的具体,似未能得其奥义。闻之于谭季龙教授,这敦煌二字可能是当时的外来语。是否为匈奴语?还有待于考核。其他一些县名,匈奴语是不少的。武威郡治所的姑臧县,据王隐《晋书》说,这本是匈奴的盖臧城,语讹为姑臧[618]。武威郡还有一个休屠县,另外还有一个休屠泽。这个县名和泽名用不着多作解释。本来要和浑邪王一同降汉,后来为浑邪王所杀的休屠王,其名称正是和这个县名和泽名相同。而这个休屠县还是休屠王的都城[619]。张掖郡的得县和休屠县也相仿佛。因为这个县本为匈奴得王所居,所以就用其王名为县名[620]。还有几个县名,如武威郡的揟次县、扑县、媪围县,张掖郡的屋兰县、日勒县,敦煌郡的龙勒县,皆不能得其确解,是否为匈奴语,有待论定。谨志于此,容作质疑。其实不仅郡县名称沿用匈奴旧名,就是一些山水名称也未能例外。前面曾提到祁连山,就是沿用匈奴语。匈奴语称天为祁连。山称祁连,极言其高也。祁连山之北,有焉支山,在今山丹县南。匈奴失去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621]。”以焉支山与祁连山并提,则焉支山当也是匈奴的本名。匈奴失去焉支,竟使其妇女无颜色,可见山上所产之物可作为妇女装饰之用。后世以胭脂作为化装用品,胭脂当为焉支同音语。焉支山亦名删丹山。删丹山亦当为匈奴语,删丹县的得名与此山有关。今删丹县改写成山丹县。焉支、胭脂、删丹、山丹皆用到现在。
河西诸地不仅有匈奴孑遗,而且还有葆塞蛮夷。葆塞蛮夷之名始见于《史记·文帝纪》和《匈奴传》,为降附于汉而居住塞下的族类。匈奴曾侵盗这些上郡蛮夷,明其和匈奴不同。葆塞蛮夷既居于塞下,当非上郡一郡所独有,河西诸地亦应不稍少其踪迹。《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有骊靬县。此骊靬当即《史记·大宛传》《汉书·张骞传·西域传》记载的黎靬。黎靬为西域国名,东汉时称为大秦。骊靬为县名,当是因骊靬降人而设置的。以域外降人设县,亦见于上郡的龟兹县。其县也是因龟兹国的降人而设立的。这在汉时已是通例,无足为奇。然由此亦可以证明河西有骊靬人。
匈奴浑邪王降汉后,河西的匈奴人内徙到五属国所在地,如何来填补这样的空隙?必然是由内地徙民实边。浑邪王的降附在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史记·匈奴列传》说:这一年“徙关东贫民处所夺河南新秦中以实之”。《平准书》则列此事于元狩三年。至于徙民的地方则添上关以西。徙民之数也确定为七十万余口。《汉书·武帝纪》于元狩四年却载:“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皆似与河西无关。按:汉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在元朔二年(前127年)。匈奴失河南地后,亦举族远去,朔方、五原郡皆须徙民充实,不应迟至6年之后始行徙民。元狩三年,山东诚被水灾,徙民就食不能稍迟,何能迟至元狩四年冬季,始克就道,当时河西已空无人居,为什么只徙到陇西、北地,而不至于河西?颇疑所说的只是一事,史家未能详记,遂使失真。
由于内地迁来了人户,也由于当地的滋养生息,到西汉末年,河西的户口已达到相当可观的数字。据《汉书·地理志》元始二年(公元2年)所载,河西四郡具体的户口数为:
武威郡所属10县,有户17581,有口76419;
张掖郡所属10县,有户24352,有口88731;
酒泉郡所属9县,有户18137,有口76726;
敦煌郡所属6县,有户11200,有口38335。
四郡合计,共有户71270,有口28021l。在当时各边郡中,都不能算是很多的。
河西四郡在当时都还有一定的富庶因素,比起内地来总是有点不及处。河西四郡又首当汉与匈奴冲突的要地,是容易受到从事游牧族类的骚扰和侵略的。迁徙到边郡的人口如何能够长期居住下去,不能说不是一个问题。汉朝有一条明文规定,居住在边郡的人不能随便向内地迁徙。这条规定,直到东汉后期都还有效。东汉后期,敦煌张奂以功当封,悉辞不受,唯愿徙属弘农华阴。正是因为张奂功大,才破格得到听许[622]。这样的特例只有西汉杨僕以军功请移函谷关一事差相仿佛。杨僕为新安(今河南新安县)人,新安则在函谷关外。杨僕欲作关内人,而又不愿意移家。会建立功绩,因请以家财移函谷关至新安县,并得到汉武帝的许可[623]。杨僕移关只能说是偶然的特殊事件,和张奂破例内迁还是有所区别的。
两汉这条规定虽说是严格,却难得永久持续下去,在王权政衰,国内有了乱事时,就不易奏效。魏晋继起,再不闻有所限制。西晋末年,永嘉乱起,洛京倾覆,中州沦为战场,人士逃逸,四散离析,大部渡江南去,至于河西者亦非少数。其时张轨方为凉州刺史,由于“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因分武威郡别置武兴郡以居之[624]。十六国霸主迭兴,中原乱离未已,西来避难仍时有所闻。前秦苻坚还曾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其间武威、张掖以东之人西奔敦煌、晋昌者亦有数千户。西凉李皓以酒泉为都,皆徙之于酒泉。因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其余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625]。显得当时河西有所增多。也许当时河西人口稠密度超过中原,实际上远未能赶上西汉元始二年。
后来魏收撰《魏书·地形志》,备载黄河下游各州户口,这是永嘉乱离以后始见的较为完全的记载。空谷足音,殊堪称道,惟以武定为断,致使瑕竟掩瑜。武定为东魏孝静帝年号自543年至550年,就以东魏来说,已是季世。其时关西早隶西魏版图,魏收称之为沦陷诸州。其中偶然亦记户数,却据永熙馆籍。永熙为魏孝武年号,自532年至534年。532年至533年,魏室尚未分为东西,不能说到沦陷。惟已在孝明帝孝昌(公元525年—528年)乱离之后,就难得一概而论。据说孝昌乱离之际,“恒代而北,尽为丘墟;崤潼已西,烟火断绝;齐方全赵,死如乱麻,于是生民耗减,且将大半”[626]。故《地形志》所记载的凉州,所统十郡二十县,仅有三千二百七十三户,较之西汉时户数最少的敦煌郡犹有不及。
如果说到河西户口再度较为繁多的时期,应该数唐代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这一年河西诸州的户口数为:
凉州(武威郡),所属五县,有户22462,有口120281;
甘州(张掖郡),所属二县,有户6284,有口22092;
肃州(酒泉郡),所属二县,有户2330,有口8476;
瓜州(晋昌郡),所属二县,有户477,有口4987;
沙州(敦煌郡),所属二县,有户4265,有口16250[627]。
凉、甘、肃、瓜四州共有户31553,有口155827。加上贞观年间的沙州户口,共有户35818,有口132077。就是加上贞观年间的沙州户口,也还没有西汉元始二年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户口之多。
再往后说,能够有河西各地总的户口数,那就要等到清代[628]。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对于河西各处户口有如下的记载:
凉州府,属县五,有户182862,有口284131;
甘州府,属县二,有户79841,有口282496;
肃州,属县一,有户22537,有口319768;
安西州,属县二,有户6094,有口77873;
两府两州共有户291334,有口964268[629]。
这样的数字不仅超过了唐代的天宝元年,而且也超过了西汉的元始元年。这样的差异可能有几个原因:其一,由嘉庆往上溯,河西的承平时期较长,可以上溯到明代初年。明代嘉峪关外诸卫虽偶争执,皆未引起若何事端。惟土鲁番曾寇肃州,明廷视为一方大患,其实河西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骚扰[630]。明清易代之际,河西亦大致平静。当时河西户口当不至于有所减少。其二,到了清代,回部内属,嘉峪关再不起阻隔的作用,自有助于河西的稳定。其三,嘉庆《大清一统志》所载的“今滋生民丁男妇大小”,乃是指雍正时摊丁入地,不再增收口赋,因而各地滋生的民丁男妇大小皆呈报户口,而无所畏避,遂使户口数目大为增长。河西各府州的户口显然多于前代,也是合于情理的。
这些户口数字中是否包括居住在河西的从事游牧生活的人们或其他的族类?这就未可一概而论。两汉时没有明文规定,可能是两种情形都会有的。东汉初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比率众内附,居于西河美稷。“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扦戍,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当时八部共有四五万人[631]。平均计算,每部约在五六千人之间。据《续汉书·郡国志》所记载顺帝时这几郡的人口数为:西河郡,20838;北地郡,18637;朔方郡,7843;五原郡,22957;云中郡,26430;定襄郡,13571;雁门郡,249000;代郡,126188。东汉户口极盛时为质帝永嘉二年,而质帝即上承顺帝,亦可谓近于极盛之时。此时上距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比居于西河美稷已将近百年。百年之间,休养生息,人口应有一定的增长。可是朔方郡仅有7843口。如南匈奴右贤王部众犹在,而未有所增添,若列于当时户口簿中,则朔方郡非以游牧为生的人口的仅有一二千人。当时朔方郡所领六县,每县将只有两三百人,这是和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不过也有例外。前面曾经提到西汉张掖郡所属的骊靬县。这个县是骊靬降人建置的,就不能说是没有骊靬人,而这些骊靬人的户口也应为张掖郡的官吏所执掌。就是一般保塞蛮夷也应该是一样的。唐代前期,承周隋之后,对于各地人口采取授田办法。当时规定:“丁男中男给(田)一顷,笃疾废疾给田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632]。当时居于域内的以从事游牧为生的人们似未能共享这样的待遇。唐初于周边各地置羁縻州,以处内属的游牧部落及其他族类。这些羁縻州的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隶于凉州者就有乾封等州[633]。契苾部落之居于甘、凉之间,就可以为例证。契苾部落本铁勒的别部,贞观初年,契苾何力随其母率众千余家诣沙州奉表内附,太宗置其部落于甘、凉二州。及薛延陀强盛,契苾部落皆愿从之,并执何力至延陀所[634]。这显然是游牧部落的本色,可见其居于甘、凉时并未改从农耕。契苾部落虽未见置有羁縻州的记载,其贡赋版籍当亦不隶于户部。到了清代,这样的差异显然已经泯没。清代规定:除外藩札萨克所属编审丁档掌于理藩院外,其各省诸色人户由其地长官造册送于户部,至若回、番、羌、苗、瑶、黎、夷等户皆隶于所在府厅州县[635],和一般齐民相同。
事实上亦是如此。自东汉末年至于魏晋,由于中原王朝的萎靡不振,未遑兼顾域外,不仅缘边各郡人口逐渐向内迁徙,而西北两方的游牧部落也随之内迁。迄于西晋,“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636]。关中如此,边郡可知。及(晋怀帝)永嘉丧乱,先后起伏的所谓十六国霸主,泰半皆出自游牧部落。当时祁连山北先后建有五凉政权,除前凉张氏及西凉李氏外,后凉吕光为略阳氐人,南凉秃发乌孤为河西鲜卑人,北凉沮渠蒙逊为临松卢水胡人。南凉鍮勿仑说其主秃发利鹿孤的一段话,正足以看出这些霸主的本来面目。鍮勿仑说:“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发左衽,无冠冕之仪,迁徙不常,无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因之,鍮勿仑建议:“宜署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637]。”而秃发傉檀征集戎夏之兵,竟至五万[638]。吕光主簿尉祐叛光,亦曾煽动百姓,故夷夏多从之[639]。而吕光自西域东归,将至武威,胡夷皆来款附[640]。可知当时河西族类,相当繁杂,为数亦殊不少。
这些族类来到河西,是各有其渊源和造因的。当时的统治者似未多加以诱导,鸠摩罗什东至凉州,实因苻坚有意的罗致,以前秦破灭,暂时淹留[641]。李皓虽曾并击玉门以西诸城,而广田积谷实为东伐作准备[642]。直至隋炀帝时,始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当时张掖已发展成为和西域交往的都会,西域诸国来者多在其地交市。裴矩以礼部侍郎主管交市事,遂因诸胡商各自言其国的山川险易,并其本国服饰仪形,丹青模写,撰成《西域图记》三卷。据其所云,共有四十四国,可见来到河西胡商的众多。后复奉炀帝命往张掖引致,西蕃至者十余国。炀帝西巡,行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皆谒于道左[643]。这些国名都不易一一稽考,仅以来朝的国数来说,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了。这些来朝的国君不会久居于河西,可是其影响所及,不会短期泯没的。由于这样的渊源,河西的胡人不仅为数众多,而且在当地的社会上已隐然成为一种力量,甚至可以左右当时的政局。唐初,受命执李轨的安兴贵、安修仁兄弟就是久居于凉州的胡人。安修仁曾经对高祖说过:“臣于凉州,奕代豪望,凡厥士庶,靡不依附[644]。”这当然不是一般流寓的商胡了。当时像安氏兄弟这样的胡人在凉州应非少数。李轨的谋主梁硕曾因凉州诸胡种落繁盛,劝说李轨防范剪除[645]。
就在李轨平灭后的十年,玄奘西行求法,途次来到凉州。这时凉州更为繁荣,玄奘在此也受到社会上的特殊礼遇。据其弟子慧立等所述,可见一斑。慧立说:“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业往来,无有停绝。时开讲日,盛有其人,皆施珍宝,稽颡赞叹,归还各向其君长称叹法师之美,云欲西来求法于婆罗门国,是以西域诸城无不预发欢心,严洒而待。散会之日,珍施丰厚,金钱、银钱、口马无数,法师受一半然灯,余外并施诸寺[646]。”所说的虽仅限于玄奘讲道的场所,凉州商胡人数的众多以及举动的豪华,应是其他各地所难以比拟的。
凉州胡人之多亦见于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一诗。诗中说:“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647]。”由这句诗中判断不出凉州胡人有多少,但他特别提到胡人,至少可以说当地的胡人是很多的。
这里所说的胡人,只是概括的名称。王国维著《西胡考》,谓自汉世,匈奴与西域诸国之人皆有胡称。其后匈奴寝微,西域之人遂专有胡名[648],故裴矩招诱西域诸国,总称之曰诸胡。这当然不包括居于北陲的突厥和回纥。不过突厥和回纥诸部也兼有胡人,即所谓九姓胡是也。河西节度使治凉州,其副使则居甘州,这是为了督察九姓部落[649]。可能是由于驻于甘州的河西节度副使的控制,九姓部落尚未见内徙于河西事例。然回纥、契苾、思结、浑诸部却曾杂居于凉州界中[650]。契苾即前面所提到契苾何力的部落。唐德宗朝曾建立功勋的浑瑊,即出自浑部[651]。这四部不仅居于凉州,甘州界内也有踪迹。其南徙在武后时,由于突厥默啜方强,夺取铁勒故地,故相率迁入唐境。其后回纥以私怨杀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君㚟,梗塞安西诸国入长安道路,寻为唐军所逐,复奔于突厥[652]。
安史乱起,唐朝西部防边之兵皆东归平定内乱,吐蕃乘间侵扰,遂尽取河西陇右诸地。吐蕃侵河西,虽有几条道路,这时出兵却是由东趋西。凉州的陷落在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甘州在永泰二年(公元766年),肃州在大历元年(公元766年),瓜州在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沙州在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653]。吐蕃既据有河西,唐人遂尽沦为奴婢[654]。迄于文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沙州首领张义潮始驱逐吐蕃守军,奉瓜、沙、伊、肃、甘等十一州地图来归[655]。张义潮所献诸州中,有瓜、沙、肃、甘四州而无凉州。直至僖宗咸通二年(公元861年),始由张义潮取得,奉献归国[656]。其后吐蕃衰弱,余部有浑末者,居于甘、肃、瓜、沙诸州间。浑末亦作嗢末,为吐蕃奴部。吐蕃旧法,出师必发豪富。豪富隶军中,皆以奴从。这些奴仆平居则散处耕牧。及吐蕃乱离,奴无所归,相聚合数千人。不仅居于甘、肃、瓜、沙四州,河、渭、岷、廓诸州亦有之[657]。
浑末的居地不包括凉州。凉州也不是没有吐蕃的。《宋史·吐蕃传》载后汉、后周之际,“凉州郭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余皆吐蕃”[658]。后来到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有所谓河西军左厢副使、归德将军折逋游龙钵来朝。河西军就是原来的凉州。折逋游龙钵当是吐蕃族人。据其所言,河西军旧领姑臧、神乌、蕃禾、昌松、嘉麟5县,户25693,口128193,今有汉民300户。所谓旧领县及户口数,皆唐天宝年间凉州未陷没前旧制及数字。这时当然不能恢复到天宝年间的实况,但当地汉民确是很少的。
唐中叶后,徙居于河西者尚有回鹘。回鹘即回纥,唐初固曾一部居于甘凉间,前文已经论及。回鹘曾佐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称雄一时,其后为黠戛斯所攻,内部亦有未能和谐,又为唐边将所攻,部众离散,其一部在庞特勒率领下,入居于甘州,且有碛西诸城。而另一大酋仆固俊则自北庭击吐蕃,尽取西州轮台等城。然居于甘州者已无复昔时之盛[659]。五代北宋时犹时与中原通往来,今维吾尔族及回族盖其孑遗也。
继回鹘之后,党项亦曾入居于河西。西夏为党项族建立的政权。西夏控制了河西,正说明河西已有党项的居处。西夏进攻凉州,早在宋真宗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至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又有谋劫西凉,袭回鹘的消息,大概都未能如愿[660]。其后于宋仁宗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攻拔甘州,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取瓜、沙、肃三州。而这一年元昊的版图,已包括凉州在内的河西全土。并以甘州路为右厢,驻军3万人,以备西蕃、回纥[661]。自西夏取河西土地后,各族遂未再见记载。
西夏为蒙古所灭。迄于元朝灭亡,蒙古族之在河西,亦如在内地一样,居住往来无所阻滞。其时色目人的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色目人包括相当广泛,举凡畏吾儿、钦察、唐兀、阿速、乃蛮、汪古等皆在其中。河西各处不仅多蒙古族,亦多色目人。敦煌石窟壁画中,元时所绘者,就显示出有蒙古族和色目人的图像,可以作为证明。
就是后来到了明代,蒙古族并非和河西就没有关系。明代为了防御鞑靼和瓦剌,在北陲修筑长城。长城的西端起自嘉峪关,嘉峪关在今酒泉市西。其遗迹大部尚留在地上,可供凭吊。长城之北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由于长城限制,其时的蒙古族人不易南下而至于河西居住。可是嘉峪关外就迥然不同。嘉峪关的建立,说明明朝的版图就止于斯处。这里有蒙古族人,也有旧受元朝控制的其他族人。虽在嘉峪关外,明朝仍加以羁縻。明初就在这里设安定、阿端、曲先、罕东、赤斤蒙古、沙州诸卫[662]。安定、曲先两卫皆在今青海省西北,阿端卫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惟罕东、赤斤、沙州三卫在河西。赤金蒙古卫就在嘉峪关外,今玉门市西北有赤金堡,就是当年卫址的所在。沙州卫在今敦煌市。这里本是古沙州,因以为名。罕东卫在赤斤卫之南,嘉峪关西南,敦煌市境内。沙州卫后废,其地建为罕东左卫。
这些族类的居地因时而有变迁。明英宗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沙州卫人全部入塞,居于甘州,凡200余户,1230余人,而沙州遂空。后来罕东卫就据有其空地[663]。这样的变迁在以后的年代里,仍不少见。1949年以来,于各族聚居之地设立自治县。迄今已成定制的有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
四、农牧业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成效
河西由于自然条件的特殊,是一个农牧兼宜的地区。远在大月氏人和乌孙人、匈奴人的时期,这里就是一个天然的牧区。如果回顾到更早的新石器时期,如前所说,由民乐县东灰山文化遗址所发现的碳化小麦、大麦、高粱和粟、稷,就可以显示出这里的农业是有悠久的渊源的。
河西地区是相当广大的,可是戈壁和沙漠的范围却也是很不小的,而且愈接近北边和西陲,就愈益明显,甚至超过了农田和牧场。这种特殊情形确为内地各处所少有。就历史的发展看来,不论其为农为牧,其生产的获得都能满足当地的需要,有些时期还可受到其他地区的称道。这在当地人口相对稀少的时期是不足为奇的。就在人口较为稠密的时期也未见过分依赖其他的接济和扶持。当然在突出发生自然灾害和受到封建统治阶级过分剥削时期也是免不了若干艰苦,但这就不仅河西这个地区如此,就是其他自然条件更为优越的地区同样是未能幸免的。
在月氏、乌孙、匈奴诸族居住的时期,整个河西都属于游牧地区。游牧地区的人口一般都不是很稠密的。人口有限,游牧所得是不会过于匮乏的。月氏、乌孙、匈奴之间互相争执,这是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当地的生产应该没有多大关系。就是后来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也只能说是匈奴单于处理不当,而不能再涉及其他方面。
从事农耕的人们进入到河西,首先的要务就是改变相当广大的一部分牧场为农田。这样并未能降低当地畜牧业的重要性,也许还会因此而使畜牧业有所提高和发展。就在西汉时,“凉州之畜为天下饶”[664],已成为当时社会的定论。西汉凉州有今甘肃一省之地,说到产马的地区,河西应该更为优越。为了保障边塞,各郡太守都是以兵马为务。如果不是马多马好,是不能完成任务的。
这里畜牧业的发展是基于自然的因素,并不因王朝或政权的起伏而有兴替。《魏书·食货志》曾经指出:“世宗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统万为赫连夏国的都城。北魏灭夏在太武帝始光四年(公元427年),灭北凉在太武帝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其间相差仅十余年。《魏书》从平统万说起,是其时已注意这一方的畜牧业。其后更扩展到秦陇以至于河西。这里虽泛指畜产,其实更注意于戎马的繁殖。后来孝文帝就以河阳为牧场,每岁自河西徙牧于河阳。正是因此而“河西之牧弥滋矣”[665]。就是再后到了隋代,河西诸郡还是和安定、北地、上郡等郡的风俗相同,“勤于稼穑,多畜牧”[666]。这是说,农业虽已有发展,畜牧业却并未因之而萧索下去。
西汉时于北边西边分置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养马三十万头[667]。这些马苑分布于安定、北地等郡,河西各郡不在其中[668]。唐初为了养马曾设四十八监,养马区域跨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亦未扩展到河西诸州[669]。明代于陕右宜牧之地设监苑,跨地二千余里。其后惟存长乐、灵武二监[670]。其他各监所在地不可俱知,似亦与河西无涉。河西宜于畜牧,不列于养马之地殆因其地临边,易受边外诸部所侵夺。西汉时匈奴入侵,多虏人民畜产[671],甚至进入养马苑,夺取马匹[672]。这样的情形也见于唐代。唐时突厥引兵内侵,有一次就掠凉州羊马[673]。这就不能不引起有关王朝或政权的注意和防范。但这并不就等于说,河西不能养马。唐代中叶,王忠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就曾由朔方、河东引得战马九千匹[674]10。唐时河西、陇右本为两道,王忠嗣为节度使乃是兼领河西、陇右道。两道皆临边,所得的九千匹马,就不能不有一部分分牧于河西。明代养马地区虽未涉及河西,然其初年始定北边牧地时,就曾规定:“自东胜以西至宁夏、河西、察罕脑儿,以东至大同、宣府、开平,又东南至大宁、辽东,抵鸭绿江又北千里,而南至各卫分守地,又自雁门关西抵黄河外,东历紫荆、居庸、古北抵山海卫,荒间平野,非军民屯种者,听诸王驸马以至近边军民樵采牧放,在边藩府不得自占[675]。”这条规定包括地区相当广阔,就有河西在内。到了清代,蒙古族内附,长城已不复再起作用,于是甘、凉、肃三州和西宁就各设马厂,分五群,群储牝马二百匹,牡马四十匹。这不仅是在养马,而且是以之为种马厂的。稍后甘州厂改属巴里坤,实际上还是保持河西马厂的规模的[676]。清朝崩溃后,山丹县作为种马繁殖场所,依然延续很久。迄至现在,居住在河西的蒙、藏、裕固、哈萨克各族仍然在从事游牧生活。前面曾经提到肃北、天祝、肃南、阿克塞四个自治县,就是为这些蒙、藏、裕固、哈萨克人民建置的。同时也说明了这几个县境的绝大部分土地都是牧区。当然还应该指出,河西的畜牧业并不是以这四个自治县为限的。
河西历来在农业方面的成就,可与畜牧业相埒,甚至超过了畜牧业。如果不是荒歉之年,也没有过分的人为灾难,河西还不至于出现难以克服的粮食问题。如前所说,河西各地最早的户口记载,是在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这一年河西四郡共有户71270,有口280211。四郡属县多寡互有不同,所有户口亦因之而异。每县平均户口自然参差不齐。张掖郡所领10县,平均每县有户2435,有口8813,这是最多的数字。敦煌郡所领6县,平均每县有户1200,有口6389,为诸郡中最低的。就当时全国各郡来说,这是属于人口最为稀疏的地区。前面还曾提到唐代天宝元年(742年)河西诸州的户口。这一年除沙州无户口数外,凉、甘、肃、瓜四州共有户31553,有口155827。凉州所领5县,平均每县有户4492.4,有口24056.2。这是最多的数字。瓜州所领2县,平均每县仅有户238.5,有口2493.5,为诸州中最少的。唐代河西诸州中独无天宝元年沙州户口数。即令以贞观年间的户口代替,五州的户口总数也不如西汉元始二年河西四郡的众多。户口总数不多,而每县平均户口最多的凉州,却超过了西汉最多的张掖郡。这是因为唐代河西各县面积较大,各州领县较少的缘故。西汉元始二年,河西四郡共领35县,武威、张掖两郡最多,各领10县,最少的敦煌郡也领有6县。唐代天宝元年,河西五州共领13县,最多的为凉州,所领5县,其余四州皆只有2县,所以按每县平均计算户口,前后就颇有悬殊。虽然不免悬殊,却都没有发生过严重的粮食不足问题。
远在秦始皇时,蒙恬驱逐匈奴,开设九原郡,为了供应阴山上下防边驻军和新徙来移民的粮秣,曾大举运输粮食。这些漕粮最远取之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677]。黄县在今山东黄县东,腄县在今山东福山县。琅邪为郡名,其治所在今山东胶南市南。总起来说,都是在今山东半岛的东部。由今山东半岛东部运粮至今内蒙古阴山之下河套附近,路途是十分悬远的。这样悬远路途运输粮秣,自然劳民伤财,甚至有人认为这是秦亡的一个原因[678]。汉武帝开拓土宇,远较秦始皇时为广大,朔方、五原两郡和河西四郡都是这时期设置的。土宇较前广大了,各处新地的粮食供应如何解决,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当时为了取河南地,筑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皆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为了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地,担馈饷,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辑之”[679]。这确实都是劳民伤财的大事。稍后“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680]。这当然也是劳民伤财的大事。不过前后不尽相同。取河南地,筑朔方,都是军事行动,通西南夷道,也是巨大的工程,这都不属于迁徙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不能不供应所需的粮食。至于徙民实边,就和前两者异趣。前文论及这次迁徙人口事,谓所迁徙的地区应包括河西四郡在内。所以为这次迁徙人口而耗费的帑金,也应该包括河西四郡在内。诚然,这次所迁徙的人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不宁惟是,对于这些迁徙的人户不仅要“贷与产业”,还要“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其结果就难免“费以亿计,县官大空”。试一设想,当匈奴人在此游牧之时,不事营建,仅居于帐幕之中,而此帐幕又随水草盈竭而时时移徙。匈奴人被逐远去,茫茫原野,势必是毫无栖止之地。新来的迁徙人口将如晁错所说的,“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681]。而新开垦的土地未必就能处处丰收,也是事理所必然的。所谓衣食之费是不能不仰给于县官的。经过几年的经营,迁徙到新地的人口,“男女有婚,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这就不需要县官的扶持,迁徙的人口是会“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的”。
这样的效果是相当明显的。汉武帝愤胡粤之害,屡兴兵戎,于是“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相奉”[682]。其时对于西域的用兵,先后也有几次,情况似略有不同。武帝停止轮台屯田诏书中曾经指出:“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诸国兵便罢,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甚众[683]。”这段诏书所言不外三事:一、汉军在西域的军糈供应,率多仰给于当地诸国;二、行军时军队自带的粮饷;三、河西的支援,最东只远到张掖郡。在这篇诏书中并未提到由内地转运漕粮,实际上也不需要从内地转运。轮台诏书颁布于李广利以军降匈奴之后。李广利之降匈奴在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由征和三年上溯三十二年为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这一年汉始置武威、酒泉郡[684]。由此可知,经过三十二年的经营,河西四郡的农业已有一定的基础,不仅满足当地人口的需要,还可能供给用兵西域所需的粮饷。
这样情形还可见之于十六国时期。十六国时期是一个兵戈扰攘、社会极端混乱时期。由于各国霸主的争夺,各地人口经常有大量的迁徙,难得有较为稳定的户口数字。这里不妨举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的户数,以事论述。其时凉州一州统郡8,县46,户30700。所统的8郡中,金城郡不应列入河西诸郡数内。金城一郡领县5,有户2000。河西诸郡共领县41,有户28700,平均每县有户700。永嘉乱离之后,凉州较为安谧,故内地人口多趋向其地。前文引《晋书·张轨传》,谓其时“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虽未悉其具体数字,由张轨为之特设武兴郡,可知是相当多的。其后苻坚、李暠时皆有徙入,已见前文,不再赘陈。苻坚和李暠所徙不下二万七千余户。以此数加上西晋太康元年的28700户,应有55700户,而张轨时所徙入者尚未计入[685]。虽不能和西汉平帝元始二年相当,亦不能说是过为稀少。在这样分裂的乱世,凉州以东的霸主们是不会运输粮食到西方的。凉州这些人口都应是依靠当地农田的收获为生的。不仅此也,李暠据有敦煌时,为了向东略地,还曾在玉门、阳关等处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686]。李暠所据有的土地于诸凉中最为狭小,稍稍广田积谷,便可维持一方政权,还可练军经武,谋向其东各处扩张。李暠的西凉如此,前凉和后凉,南凉和北凉也都是在这样情况下巩固它们的政权的。
当然这并不排除当地所遇到的自然灾害和人为设施不当因而构成的一些困难。唐代初年,河西陇右的虚耗凋敝,确曾引起若干顾虑[687],经过一番努力和振作还是能够有改观的。拙著《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一文中曾征引陈鸿祖《东城老父传》对此作过说明。东城老父于安史乱后回忆天宝年间富庶的景象,曾经说,“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还曾征引《明皇杂录》所说的:“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所谓陇右当然是包括河西在内。在那篇拙著中曾经辨明这两条记载,并非完全都是实录。天宝末年,河州敦煌道确曾运输过相当数量的粮食,漕下黄河,以备关中凶年。其实这是当时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为了争取唐玄宗的宠信而故弄玄虚。不仅唐玄宗中了圈套,就是东城老父这样与唐玄宗有关的人也都信以为真。《明皇杂录》更扩大其辞,竟说“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这样不实之辞原是不值一驳的。不过还应该再作推索。哥舒翰由河州敦煌道运粮至关中,固然是为了争取唐玄宗的宠信,但河州敦煌道的粮食还是运输出去了。这证明了当时河西的农业还是有相当的成就的,是可以满足当时河西人口和驻军的需要的,但不能说过分富饶。哥舒翰为了争取唐玄宗的宠信运出了粮食,只好另谋补偿的办法,借东土的漕运来供给了。《明皇杂录》所说,过分夸大,益见其为讹妄。正因为河西农业所产的粮食能够自足,是无须假借外地的资助,也未见到有关外地资助的记载。后来元稹在《西凉伎》一首诗中所说的“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688],虽系得自古老的传说,却还是近乎实录的。
在这样悠久的年代中,河西的农业是怎样取得成就的?除当地农民的勤劳耕耘外,至少有两点是应该得到称道的:其一是开发农田水利灌溉,其二是尽可能扩大农田的地区。
我国先民从事农业生产,对于灌溉水利向来是重视的。为了能够灌溉,经常在可能的条件下进行渠道的开凿。这就有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这种事例史不绝书。就在西汉中叶,曾经有过一度高潮,河西各处受益不少。《史记·河渠书》在论述汉武帝堵塞瓠子决河之后,接着就说:“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这只是笼统的说法。《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就较为具体。据《地理志》所说,张掖郡得县,千金渠西至乐涫入泽中。得县在今张掖县西北,当时为张掖郡的治所。乐涫为酒泉郡属县,在今酒泉市东南。羌谷水出南山羌中,经得县西北流,再折向东北至居延入海。这就是现在的黑河,也称张掖河或弱水。千金渠当是利用羌谷水开凿渠道的。以地形度之,这条渠道可能长达200公里,自然是一条大渠。敦煌郡中的籍端水和氐置水也被引用溉田。籍端水今为疏勒河,也是一条古川,灌溉面积不会很小。《地理志》系籍端水于冥安县下。冥安县在今瓜州县东南。冥安县东北有渊泉县,据阚骃所说,地多泉水,故以为名。渊泉县近籍端水,当也受到灌溉的利益。阚骃为晋时敦煌人,曾仕于沮渠蒙逊,以舆地之学名家,著有《十三州志》。以舆地学者言乡邦事当不会偶有舛讹。由阚骃所说,不仅可知西汉时籍端水的灌溉作用,还可知这条河流直到十六国时对农业仍然有所裨益。氐置水的灌溉区由龙勒县开始。龙勒县在今敦煌市西南。氐置水流经敦煌市,敦煌市也应列入氐置水的灌区之中。氐置水由龙勒县东北流入于泽中,如前所说,这个泽应在今敦煌市北或稍东北处。《汉书·地理志》敦煌市所领的6个县中,除这里已经提到的还有效穀和广至两县。颜师古于效穀县下注说:“本鱼泽障地。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为县名。’”而广至县的昆仑障又为宜禾都尉治所。县以效穀为名,都尉又以宜禾相称,皆说明当地农业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效穀县在敦煌市东北,其西就是氐置水下游,当地农业能够有成就,应与氐置水分不开的。广至县又在效穀县之东,也可能与效穀县同为氐置水的灌区。酒泉县治所的福禄县,在呼蚕水流域。呼蚕水今为流经肃州市的北大河。《汉书·地理志》于呼蚕水条下未言及溉民田事,然酒泉郡有灌溉渠道已见于《史记·河渠书》中。酒泉郡于呼蚕水之外别无大川,则《河渠书》中所言灌溉,除呼蚕水更无足以当之者,不能因《地理志》失载而置之不论。河西还有一条谷水,流经武威郡及其所辖的武威县的城外。《地理志》亦未一言其溉民田事。河西四郡中,张掖、酒泉、敦煌三郡治所分别为得、禄福、敦煌三县,这几个县能够作为郡治,应各有其具备的条件,至少也是和它们作为灌区,农业能够获得成就有关。准此而言,濒于谷水的武威县,也是应该得到谷水的灌溉的。河西四郡都有能够灌溉的条件并能充分加以利用,农业能够取得成就,那就不是意外的事情了。
欧阳修撰《新唐书·地理志》,于唐代各州农田水利皆备载无遗,独于河西的凉、甘、肃、瓜、沙五州竟未着笔一字。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于河西诸州中仅详载瓜州晋昌县的冥水,并说:“自吐谷浑界流入大泽,东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丰水草,宜畜牧。”所说的冥水就是汉时的籍端水。汉时籍端水如上所云,是可以灌溉民田的。可是到了唐代,却仅仅是“丰水草,宜畜牧”,前后差别是很大的。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可能是由于天宝以后,河西为吐蕃所据有,职方之臣未能掌握其地的情况,李吉甫已无足够的材料可供撰述,异代之后欧阳修当更不易着笔了。其实唐代前期河西各地并不是就无农田水利的设施,拙著《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中就曾列举了三宗以资证明。在那篇拙著中是这样说的:“武则天时陈子昂就曾说过:‘甘州诸屯皆因水利,浊河灌溉,良沃不待天时。’稍后冉实也曾在凉州利沟洫,积糗粮。开元年间,张守珪为瓜州都督,更取得可观的成就。瓜州地多沙碛,本不宜于稼穑,又每年少雨,只能以雪水灌溉,其时当王君㚟败没之后,州城残破,渠堰尽毁,张守珪修复了州城,整理了渠道,为州人所称颂。”这样一些成就是会博得当时后世的称颂的。
河西的降水量一般是稀少的。当地对于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的兴修自来是十分重视的。如果没有其他意外的变化就可一直沿用下去。实际上若是不能得到水利灌溉,种植农作物就难保不遇到困难,甚至将颗粒无收。所以利用和保护旧渠是刻不容缓的。前面说过,西汉在取得河西之后,兴修农田水利不遗余力,因而能使农业获得显著的发展。魏晋继之,一方赓扬前功[689],更注意修理旧渠[690]。后来到了十六国时期,戎马倥偬,农田水利自难得到修整,史籍亦未见有关记载。可是五凉霸主并未因田亩歉收而多有顾虑,这是在前面已经论述过的。唐宋时期,河西农田水利亦未多见记载,可是灌溉事业并未因此而多所废弛。其遗迹尚多完整,未尽湮塞,当是长期为后世所利用,故能保存至今。今年(公元1988年)秋初,中国唐史学会部分同志组团远赴敦煌、哈密、鄯善、吐鲁番等处考察,海亦偕同前往。途中得识敦煌研究所李正宇君。李君正在撰述《唐宋时期敦煌县河渠泉泽简志》。其中所述唐宋时期敦煌县河渠泉泽及水利设施共103所。文中所附《唐宋时期敦煌县诸乡位置及渠系分布示意图》,就显示出当时敦煌县十二乡及沙州城附近50余所河渠泉泽。当时农田水利设施历历可睹。敦煌于河西地区最居西端,尚且如此,其他各处至少皆当与敦煌相同。可知历来河西各处农业能够有所发展,而且取得相当成就,并非偶然。
河西于汉武帝时始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武威郡治姑臧,其故城在明凉州卫东北二里[691]。明凉州卫即今武威县。张掖郡治得县,其故城在宋张掖县西北四十里[692]。宋张掖县即今张掖县。酒泉郡治福禄县,即今酒泉市城[693]。敦煌郡治敦煌市。敦煌市于唐时为沙州治所。今敦煌市西南有沙州旧城,与今县城隔党河相望,当系汉敦煌郡的遗址。四城城址虽间有改动,最远不超过40里,不能说是很大。这可以说,西汉中叶人士选择城市位置的知识和能力是相当高明的。城市的形成诚然有各种不尽相同的因素,时易世异,有些因素可能已失去作用,城市却不至于有根本的变化,就足以作为证明。河西城市应是受到一些自然条件的制约,由于戈壁和沙漠掺杂于农牧地区之间,而为农为牧又各有其渊源。这四个郡城的设置显然都与当地适于耕耘,而农业都能获得成就有关。自西汉初建四郡,历经隋唐而至于明代,河西在阻隔祁连山南和合黎山北游牧民族的交往,确如有关王朝的期望,起过一定的作用。而丝绸之路的开辟和畅通,这几个城市也能绾毂其间,使往来无所阻碍。
在这四个都具有一方都会的城市中,姑臧犹为重要,又较为繁荣。凉州人户的稠密,于这四个都会中最居首位。历来有关河西人户的记载,皆未言及这四个都会中的具体数目,然由各郡(或各州)的人户数字按所领县数平均分配,其间分布的稠稀是明显可见的。虽是以县数平均计算,然郡治或州治所在之县的人户必然较其他各县为多。这是普通的道理,无待于多事阐述。这样说来,武威郡及后来凉州治所的姑臧县,人户之多应为河西诸县之冠。前文根据汉唐两代的记载,指出西汉元始二年时武威郡所领10县,共有户17581,有口76419。平均每县有户1758,有口7642,姑臧县的人户应多于这个数字。也指出唐代天宝元年,凉州所领五县,共有户22462,有口1202813。平均每县有户4492,有口24056,姑臧县的人户也应多于这个数字。前文还曾征引唐代岑参的诗句:“凉州七里十万家”,这是说当时凉州繁荣的情形。实际上当时凉州的人户仅多于4492,是否就达到5千户,还未敢必,如何能够说是十万家?有唐一代,作为都城的长安、万年两县,皆为京兆府的属县,天宝年间,京兆府领23县,共有户362921。平均每县为15779户。长安、万年共治于都城之内。按平均数计算,两县共有户31558。实际上两县的户数应该超于此数,然距十万家仍尚很远。远在边地的凉州,如何能够说上有十万人家?显然是在诗人笔下过于夸大了。虽然如此,姑臧城在河西还是规模最大和最为繁荣的。姑臧城本为匈奴所筑,匈奴被逐,这座城就为汉人所沿用,似未闻有所增筑。西晋末年,张轨为凉州刺史,始大城姑臧,南北七里,东西三里[694]。其周围当为20里。后来到五代时,其城依然方幅数里[695]。这在河西是少见的。今武威县城为明时所筑,周11里有奇[696]。明时度制与晋制略有不同,相差不应过大,今武威县城显然较小于晋时的姑臧县城。西汉时,武威郡和河西其他三郡居于同等地位,似无若何差异。唐时凉州为中都督府,瓜、沙二州皆为下都督府,甘、肃二州皆为一般的州,且又均为下州[697]。这其间就是有所区别的。唐初,玄奘西行求法,道过凉州。据其所见闻,“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业往来,无有停绝”[698],繁荣的情形跃然纸上。及节度使制度建立,凉州更为河西节度使驻节之所,更有利于当地繁荣的发展。前文征引元稹《西凉伎》诗中所说的“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虽系旧时传闻,谅非虚语。直到北宋时还有人说:“唐之盛时,河西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699]。”
河西次于凉州治所武威县的都会为张掖县。张掖县于隋时为张掖郡的治所,其实就是汉时张掖郡治所得县。得县于晋时改为永平县,隋开皇时改为酒泉县,大业时又改为张掖县[700]。隋时西域诸国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701]。张掖于此时作为与西域诸国交市的地点,当与交市监的设置有关。交市监,隋初于缘边各地设置,掌互市,参军事,出入交易。炀帝时改为互市监[702]。当时对于西域各国相当重视,炀帝特令裴矩主其事。裴矩时为吏部侍郎,名为称职[703]。隋制,吏部侍郎为正四品,诸缘边交市监视从八品[704],贵贱相差甚远。炀帝令裴矩主其事,而且还兼程前往张掖,可知其重视的一斑。裴矩到张掖后,即招诱诸国,先后至者十余国[705]。这就使张掖城趋于繁荣。由于隋帝的招徕,张掖城的繁荣迄于隋季当不至凋零。唐时河西节度使驻节凉州,其副使则驻节甘州,这对于张掖的繁荣是会有所帮助的。张掖城是繁荣了,但武威城却并未因之而衰落下去。前文曾征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证明唐初凉州的繁荣。玄奘至凉州为贞观三年事,上距裴矩监张掖互市,尚不到20年。在此期间,张掖正在繁荣时期,对于凉州似无若影响。
最能引人注意的,则是敦煌。莫高窟的开始兴建,远在前秦之时。其后陆续开凿,并未稍有止息。隋唐时期施工益为繁多。这由诸石窟的雕塑艺术和题名、石刻可以一一覆按,尤其是不少的供养人像显示其为来自西域的远客。这些远客的莅临正显示出敦煌有一定的繁荣。自张骞通西域后,西域和内地的交往,不论其出入阳关或玉门关,都必须经过敦煌。前往西域者,出阳关或玉门关前,都必须在敦煌重整行装,补充给养,以便远涉戈壁不至遭受更多的困难。其来自西域者,沿途历经奔波,甚至艰险,得至敦煌,便当稍事休整,再继续长途跋涉。一些胡商还可就地销售所携来货物,即可专返原地,计划再度来此贸易。有此诸因,敦煌的繁荣是无待疑问的。不过有一点还须稍加解释。十六国时期,李暠建立西凉政权,即以敦煌为都。其后又迁都酒泉。这次迁都并非由于敦煌的萧条,而是李暠图谋向东扩展。李暠在迁都之前,曾大集群僚,慷慨陈词,谓“今惟蒙逊鵄一城,自张掖已东,晋之遗黎,虽为戎虏所制,至于向义思风,过于殷人之望西伯。大业须定,不可安寝,吾将迁都酒泉,渐逼寇穴”[706]。这段言辞至为明显。李暠的迁都纯从政治与军事着眼,敦煌废不为都,只是其所在位置偏于西僻,延缓它的东向扩展,和敦煌的繁荣萧条是不相关的。
其实,以敦煌的富庶是可以支持一方的政权的。唐代中叶,吐蕃乘安史之乱,占据了河西陇右各地。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唐以全国之力防御吐蕃东侵,防秋之兵难得解甲稍息。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沙州人张义潮阴结英豪归唐,竟能战胜吐蕃守军,奉瓜、沙、伊、肃、甘等十一州地图归国[707]。张义潮虽能奉唐正朔,然远在西陲,实不易得到长安的助力。到了五代,曹义金仍能绍继张氏的旧勋,巍然系一方的安危。直至宋时,西夏强盛,沙州方为所并。以敦煌为中心这样的地方力量,能够继续存在,固然是张义潮、曹义金及其后继者毅力壮志的具体表现,如果不是敦煌的繁荣和沙州的富庶作为基础,恐怕也是难于支持这样悠久的年月的。
五、经过河西的交通道路
论西域和内地的交通,自来都认为是始于张骞的凿空。张骞以前虽未见于记载,然亦非绝无此可能。张骞在大夏时,始见邛杖蜀布。此邛杖蜀布能够远至大夏,当是由今云南省西运的。这应是假借商贾之手,故史籍未见记载。唐蒙在南越获食枸酱,因而建议通夜郎道。蜀中枸酱能够输至南越,也是商贾所致力的。张骞西使以前,祁连山下可能已有商贾往来。不过这是推测之辞,是难得证实的。
然而有一问题不容不在此略为涉及。这是有关殷商时期制造器皿所用的玉出自何方的问题。我国先民喜用玉器是有悠久的渊源的。《尚书·汤誓》:“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代三朡,俘厥宝玉。”后来到了殷商,用玉更多,下至两周,用玉之风愈益普遍。制造这些玉器所用之玉究竟来自何方?殊滋疑义。近来有的同志据出土殷商的玉器,作化学测定,谓其中有一部分的素质和现在新疆和田所产的玉相同,因而确定殷商时所用的玉来自新疆。这就不能不引起若干疑问。据说所测定的玉器,仅有一部分和新疆所产的玉素质相同。如果这一部分的玉来自现在的和田,其余得自何方?就不能不成为问题。我国产玉之地也并非绝无仅有,只是有的矿源已竭,未见再行开采。是否这些产地所产的玉都已经过测定?矿源已竭的产地,无玉可采,将用何物来代替测定?若无法测定,如何能说所产的玉不含所测定的因素?就是来自现在的和田,在此悬远的距离中,究竟取什么道路?未见有所考实,仿佛就在近旁,唾手可得。按之张骞凿空前后,西域道上,小国林立,不必追溯远古,秦穆公就曾西伐戎王,益国十二。秦昭襄王时,还曾继续开拓,义渠戎国就为秦国纳入版图[708]。义渠以西,尚渺茫难知。西汉中叶,始从匈奴降者得知有大月氏,复知与大月氏共居的乌孙。阳关以西又有鄯善、若羌、且末、扞弥等七八国,然后才能达到产玉的于阗。这样窎远的路途,于阗之玉如何能够东运?当然也可以说,假借商贾的力量。可是当时用玉之多,商贾之力如何能够供应得上?十六国时期,吕光在姑臧建立凉国,史称后凉。吕光自称三河王,遣使至于阗购买六玺玉。及玉运至敦煌,李暠的西凉政权已经建立起来,这批玉货就为李暠所没收[709]。殷商时的玉如果来自于阗,沿途经这许多政权和族类的辖地,是否了无阻隔,就不能不是个问题。当然这只能算是猜度,实际上当时恐难如所设想,真的能够远至于阗运玉。今传世《穆天子传》叙述穆王西游,曾远至于昆仑。昆仑山在今新疆西部,为黄河发源之地。这个昆仑山乃是汉武帝听到张骞的报告所起的名称,与穆王的游历无关。因为古图书说黄河发源于昆仑山。张骞以今塔里木河为黄河,所以昆仑山也就移到今新疆的西部[710]。《穆天子传》,《四库全书总目》列于《小说家类》,盖以其“夸言寡实”,不能与一般史籍相提并论。据《国语》所载,穆王曾经征过犬戎,仅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犬戎为西戎别名,居于周的西陲。周幽王时,犬戎内侵,西周为之倾覆,其相去并不很远。西周时期尚且如此,殷商之时何能远至西域,采玉购玉于昆仑山下?
张骞自西域归来,汉使多循迹前往。由于河西已入汉的版图,汉使往来,即遵循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一途。这条道路也是所谓丝绸之路的一段,这是论西域史事者共同认可的道路。河西夹处在祁连、合黎两山之间,若不是南越祁连山,而北绕合黎山,这里是别无其他歧途的。
然而河西的东西两端,不仅有歧途,甚至不是一条。论河西史事者不容舍而无所涉及。拙著《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曾经指出,由当时都城长安西行,有南北两道都可抵达河西的东部。其南道经雍县、汧源、上邦、襄武、渭源、狄道、金城诸县,出金城关,循乌逆水而上,再经广武县,而至凉州。用现在地理来说,就是经过陕西凤翔、陇县,甘肃天水、陇西、渭源、临洮,兰州诸县市,溯庄浪河而上,经永登县,就可达到原来凉州的治所姑臧县。其北道经新平、安定、平凉、平高、会宁诸县,出乌兰关,亦可至凉州。用现在地理来说,就是经过陕西彬县、甘肃泾川、平凉、宁夏固原和甘肃靖远诸县,而至凉州。在这南北两条道路之外,还有一条道路,乃是由上述的南道西行,至狄道县,渡洮河和大夏河而至于河州,出凤林关,渡黄河,再经鄯州和鄯城县,过浩亹水,越祁连山,而至于甘州。唐河州治所在今甘肃临夏县。鄯州治所在今青海海东市。鄯城县今为青海西宁市。凤林关在今甘肃永靖县。浩亹水今为青海大通河。这条道路更在南道之南。
这三条道路只能说是唐代丝绸之路东端的几条歧途。道路的设置固然可以承袭前代的旧规,但溯其肇始却也不能一概而论。经过凤林关和越过祁连山的道路,也就是南道之南的道路,是要经过位于今永靖县的炳灵寺的。炳灵寺的建筑始于西秦乞伏炽磐建弘元年(公元420年),可以作为这条道路畅通的标志。再往前溯,东晋法显就是从这条道路西行求法的。法显的西行是在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其时炳灵寺固尚未建立也。
另一求法高僧玄奘所行的却是上面所说的南道。据慧立和彦悰所记:“时有秦州僧孝达在京学《涅槃经》,功毕返乡,(玄奘)遂与俱去。至秦州,停一宿,逢兰州伴,又随去兰州。一宿,遇凉州人送官马归,又随从至彼[711]。”这当然不是说,这条道路至玄奘西行求法时始畅通无阻。
其实,玄奘所行这条南道乃是张骞通西域后,由长安西行的主要道路,也是唯一的道路。《史记·大宛传》论述当时的形势说:“匈奴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隔汉道焉[712]。”汉廷为了保证进入河西道路的安全,在浑邪王降附之后,“始筑令居以西”[713]。令居县故城在今甘肃永登县西北,位于庄浪河流域。庄浪河当时称为乌亭逆水。乌亭逆水上源近乌鞘岭,其地山岳重叠,所谓“筑令居以西”,当由其地开始。这就足以证明溯乌亭逆水,经令居县,当时为前往河西道路的所在。
唐时这条道路由长安西行,是要经过雍县、汧源两县,再至于上邽县。雍县为今凤翔县,汧源为今陇县,上邽县今为天水市。这是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的。西汉时由长安往西,同样要经过这几个县的。只是唐汧源县,汉时称为汧县。这条道路在这里的路线只有这一条,别无选择。因为汧县或汧源县以西,陇山高耸,行到这里必须越过陇山。陇山岩障高崄,不通轨辙,行旅视为畏途。陇头呜咽流水,越山远行者往往为之怅惘。虽历尽艰辛,亦无术改变途程。可知远在汉世,这条道路不仅是前往西域的主要道路,而且还可以说是唯一的道路。
唐代前往西域的北道,是要经过乌兰关的。乌兰关在乌兰县,濒于黄河。乌兰县在会州治所会宁县的西南。周武帝西巡至此置乌兰关[714]。乌兰置关显示这条道路的重要。道路上设置关隘当是这条道路的通行已有相当岁月,但也不是开通已久。西汉时,这里不仅未设关隘,而且也还未形成前往西域的大道。汉武帝曾经西逾陇山,由陇西北出萧关,行猎新秦中而归[715]。萧关在今宁夏固原市东南。由此更西北行,即可达到今会宁县,亦即唐代会州的所在地。然武帝却是由萧关北去,去到新秦中。更始时,班彪避难凉州,作《北征赋》以见志。赋中备列沿途所经过的地方。他一则说:“朝发轫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他又说:“乘陵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乡”;他接着说:“登赤须之长坂,入义渠之旧城”;他还说:“过泥阳而太息兮,悲祖庙之不修;释余马于彭阳兮,且弭节而自思”;然后他再说:“跻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716]。长都指长安而言,这是说他由长安首途。瓠谷为焦获,在今陕西泾阳县。郇为右扶风的属县,在今陕西旬邑县的东北。邠为郇县的乡聚,亦当在今旬邑县境内。赤须坂在北地郡,义渠的旧城当在今甘肃庆阳西南。泥阳为北地郡属县,在今甘肃宁县东。彭阳为安定郡属县,在今甘肃镇原县东南。高平为安定郡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市。高平为班彪此行最后的目的地。他由长安一路行来,经过今陕西泾阳、淳化、旬邑,甘肃的宁县、庆阳、镇原诸县,而至于宁夏的固原市。
稍后于班彪经行这条道路的是东汉光武帝的征隗嚣。光武帝为此也曾经亲自到过高平。在高平会见了窦融及其所率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金城五郡太守[717]。窦融及五郡太守从哪一条道路去到高平,未见记载。既有金城太守偕行,可能是由金城渡过黄河,再折向东行的。汉武帝曾经越过陇山,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718]。空同山在今甘肃平凉市西,亦作鸡头山。祖厉河源于今甘肃会宁县,北流至靖远县入黄河。汉武帝由空同山西行,所临的祖厉河当在今会宁县境。秦始皇巡陇西、北地时,出鸡头山过回中[719]。汉武帝所行的空同山至祖厉河一段道路,应是陇西郡至北地郡的大路。汉武帝当时仅至于祖厉河,并未由此前往陇西。当窦融率五郡太守会光武帝于高平以前,曾派遣其弟窦友赴洛阳诣阙陈情。友至高平,会隗嚣反叛,道路阻绝,中途复还[720]。窦友由河西赴洛阳,也要经过高平,这是因为隗嚣盘踞天水,反对汉室。窦友如果要经过天水去洛阳,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能不绕道高平,再折而东南行。就是这样也为隗嚣所阻,未能继续前去。这就完全可以证明:汉时由长安赴西域是以越过陇山,再经天水为主要道路,是不会经过高平的。由窦友到高平一事,还可以证明当时由长安至六盘山下的道路,仍然是像班彪所走过的那样,要经过郇邠和彭阳,也就是经过现在陕西旬邑和甘肃镇原的道路,那时好像由现在甘肃平凉、泾川等县东南行的道路,还未能成为通行的大道,不然窦友越过六盘山后,不会再折向北行,到达高平,也就是现在的固原的。
唐代的乌兰县于汉时为祖厉县。祖厉县城在祖厉河的下游。汉武帝虽临祖厉河,却未到过祖厉县。史籍中亦未见有人到过祖厉县的记载,可见祖历县并未有通行的大道,远越西域者是不会出于此途的。
前面曾经指出:由长安西行经过河西而至西域的道路中有一条是遵循南道,到今甘肃临洮县,渡洮河和大夏河,经青海海东市和西宁市,越祁连山而至于张掖的。这是河西中部分出的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以西还应有一条道路,也可说是河西大道的另一条分支。这条道路是由敦煌南行,大致是通过现在的当金山口,经由柴达木盆地,更东南行,以达吐谷浑东境龙涸(今四川松潘)而入益州[721]。西凉李暠曾经几次派遣使臣间行奉表至建康[722],所行的就是这条道路。其时沮渠蒙逊方盘踞张掖,建立北凉,由敦煌经过酒泉东行是不可能的。由敦煌南行经过柴达木盆地的道路并非主要的大道,当时称之为间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其后北凉姑臧为北魏所攻破,凉王沮渠牧犍降魏。牧犍弟无讳继续与魏军相抗,辗转至高昌,仍自称凉国。这个凉国为了取得东晋的支持,不断派遣使臣东南至建康。当魏军还未占领敦煌时,赴东晋的使臣仍和西凉一样,由敦煌南行。后来这条道路阻塞,只好改道由焉耆到鄯善(今新疆若羌县),再越过阿尔金山口,进入吐谷浑境内[723]。虽未能取道阳关或玉门关,经过敦煌,也还是可以作为丝绸之路的一条支路的。
由河西西行前往西域,西汉时有南北两道。即《汉书·西域传》所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东,为南道”,“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这是出玉门、阳关西行的。《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又增添了一道。《魏略》说:“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若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西汉时的北道是经过车师前王庭的。车师前王庭治交河城,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魏略》所说的北道却与车师前王庭无关。《魏略》所说的新道,要经过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的高昌,高昌在今吐鲁番的东南,和交河城相距并非过远。这样的改变使原来北道的路程有所缩短。《魏略》所说的新道,是出五船北到高昌。五船未知确地所在,但既有意避开三陇沙及龙堆,当是出玉门关后即转向北行。其北为伊吾,即今新疆哈密市。《魏略》所说的新道未明白指出经过伊吾,恐是行文简略,未能一一涉及。伊吾本匈奴伊吾卢地。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取得此地,并于其地置宜禾都尉,从事屯田。伊吾土地膏腴,为匈奴所必争,故常驻军以资防卫[724]。这样重要的地方,新道若不经过其地,那将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新道的形成也不至迟到曹魏之时,只是到《魏略》的撰著才见于记载。
魏收撰《魏书·西域传》,于玉门关外的道路,别有论述。它说:“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出:自玉门渡流沙西行两千里,至鄯善,为一道;自玉门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魏书》所说的虽为四道,实际上却只有两道。莎车今为新疆莎车县,正是西汉时南道经过的地方。南道逾葱岭,至大月氏、安息等地。《魏书》西行的两道,皆须逾葱岭。西域诸国因时而有兴废,故所至之国与西汉时不同,可以说,《魏书》莎车西行的两道,只是汉时南道的伸延,或者就是汉时的南道。《魏书》所说的自玉门渡流沙至车师的一道,既可说是《汉书·西域传》的北道,也可说《魏略》所说的新道,因为这两条道路都和车师有关。《魏书》的记载只是董琬、高明两人由西域归来后的陈说,董琬、高明曾至乌孙、破洛那等九国,故所述有限。
隋炀帝时裴矩曾数至张掖、敦煌,由于究心边事,撰成《西域图记》三卷。据其所述,由敦煌至于西海,凡有三道。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唱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725]。这三条道路其发韧处和最初的路段,略同于《魏略》。其中南道自来少有改变。北道和中道与《魏略》的北道和新道所差异的,只是高昌的问题。其实这几条道路都是可以达到高昌的。山川形势如此,只是跋涉者取其方便而已。
敦煌于唐时为沙州的治所。《元和郡县图志》记沙州的“八到”:“西至石城镇一千五百里,北至伊州七百里。”沙州与伊州相距700里,虽亦须经过莫贺延碛,路程究非过远,可以暂置不论。石城镇即鄯善。贾耽所记入四夷道路,于沙州西行的道路曾有具体的记载,据其所说:“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脩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726]。”虽所记道路里数与《元和郡县图志》不尽相合,而沿途经过却较为详备,可以征信。《元和郡县图志》于沙州八到中未涉及至西州的道路,而西州的八到中却有“东南至金沙州一千四百里,南至楼兰国一千二百里,并沙碛,难行”的记载。唐时无金沙州。此金沙州当系因下文的金婆岭而误衍金字。有这一条记载,即可与沙州的八到相互订正。《汉书》所说的车师前王庭,《魏略》所说的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的高昌,皆在唐西州境。西州治所的前庭县,本名高昌,即取旧高昌国为名[727]。这条沙州和西州间的大道,当即《敦煌石室佚书》本《西州图经》所说的大海道,亦即《太平寰宇记》征引裴矩《西域记》所说的柳中路。大海道是因柳中县东的大沙海而得名,柳中道自是因经过柳中县而得名。柳中县即今鄯善县的鲁克沁,大沙海即今噶顺戈壁。由于有《西州图经》和《西域记》的记载,这条道路就更为明确[728]。《汉书·西域传》记南北两道,虽是出玉门、阳关,而北道却是从车师前王庭起始。由隋唐时期的记载,可补玉门至车师前王庭间的一段。《魏书·西域传》所记较《汉书》为明确,惟道路里程与《西州图经》《西域记》皆不同。戈壁中的里程恐也难得都能一致。《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皆未著录裴矩《西域图记》,亦未著录《西域记》,恐二者本是一书,传写误为两书。《隋书·裴矩传》所录者为其书序文,《太平寰宇记》所征引者当为其具体条目,故详略有所不同。得《太平寰宇记》的引用,更可以征信。
不论这些道路如何分歧,都是发韧于敦煌的,也就是离不开玉门和阳关。这里应该特别提出,由河西前往西域除过由敦煌起程外,还有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由瓜州治所晋昌县东北起,可以通到伊州。伊州治所伊吾县,汉魏以来都是有名的所在。唐贞观初年,玄奘西行求法,就是由这条道路前往的。据慧立和彦悰所记:“(玄奘)遂至瓜州,……因访西路。或有报云: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河,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伊吾国境[729]。”玄奘即遵此路前往。《元和郡县图志》瓜州晋昌县东二十步有玉门关。未载置关年月。《元和郡县图志》又于沙州寿昌县条下列有玉门故关,亦未载废省年月。西汉酒泉郡有玉门县,在今甘肃玉门市西北。据说,汉罢玉门关屯,徙其人于此[730]。论其方位又与唐玉门关不同。玄奘既由此玉门关西行,西行之年为贞观三年,则这里的玉门关唐初已经有了。玄奘离晋昌县时,由于逻者甚严,入夜始得启行,三更许即望见玉门关,计程约二十余里,《元和郡县图志》谓玉门关在晋昌县东二十步,显然是记载的讹误。玄奘离晋昌县前,闻人说玉门关在瓠河上。迨其将至玉门关时,发现这条河水的两岸可阔丈余,河上架木为桥。瓠河未见地志记载,晋昌县有冥水,瓠河当即冥水。谭季龙(其骧)教授撰《中国历史地图集》,于唐代《陇右道东部图》中不从今本《元和郡县图志》之说,而置玉门关于冥水之西,极是。惟距冥水稍远,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未尽相合。
这条通过唐代玉门关的道路的开通,实际上是绕过了敦煌。但这条道路只是河西通往西域的一条支路,其他几条道路仍然继续畅通,还是依旧经过敦煌的。敦煌的重要地位并未因此而有显著降低和削弱。玄奘西行是在唐的初年,他所走过的道路以后照常通行,玉门关没有废止就是具体的证明,就在这时,敦煌仍然繁荣,莫高窟在唐代不断有新窟开凿成功,说明了其他几条道路继续显示出重要的作用。
此外,还有一条有关河西至西域的道路的记载,见于《隋书·高昌传》。《传》中说:“从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碛千余里,四面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寻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之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魑魅魍魉也,故商客往来多取伊吾路。”这段叙述中特别指出这是一条“捷路”,显示它并非一般通行的道路。再则说,它是一条不经过伊吾的道路,因为由于这条道路难于通行,所以商客往来才多取伊吾路。伊吾在高昌之东,武威更远在伊吾东南,由东南或东方去到高昌,是一定要经过伊吾的。后来北宋王延德使高昌,就是绕道今内蒙古前往的,途中经过伊州(即伊吾)才到高昌的。由武威前往不论采取哪一条道路,也是不能不经过伊吾的。况且武威距离高昌绝远,并非只有千余里。当时通行大道是由凉州至甘州,再至肃州、瓜州。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凉州至甘州500里,甘州至肃州400里,肃州至瓜州480里。仅凉州至瓜州之间已有1380里。而瓜州至高昌的里程更远过此数。所谓“捷径”应较此为近,但近至千余里是讲不通的。可能《隋书》于此有误文,这条捷路不一定始于武威。如由瓜州西行,里程差相近似。因为伊州东南取莫贺碛路至瓜州900里,西州(即高昌国故城所在地)东北至伊州730里,合计亦是千余里。这条道路是要经过伊州的,应该就是伊吾道。而《隋书》记载这条捷径明白不是伊吾道。这就不能说是这条道路的舛讹。或谓《隋书》所说的武威为敦煌之误[731]。敦煌在伊州正南微东,由敦煌去高昌可以不必绕道伊州,而高昌所在的西州距敦煌也只有1400里,是和千余里之说相符合的。可是由敦煌去高昌的道路,自西汉以来即已通行,说不上是一条捷径。到底如何解释,只好暂置不论,留待高明。
上面所述的这几条道路,都是通过河西的西北、东南走向的大道的分支。也可以说是丝绸之路在这个地区的分支。虽说是丝绸之路的分支,也可以作其他的用项。历来有些军事活动就曾经是在这些道路上进行的。当然,通过河西的大道的分支还不仅只是这几条,只是和丝绸的运输没有多大的关系。汉时的弱水,亦即唐时的张掖河,是由甘、肃两州之间流入居延海的。这条河谷也是一条南北向的道路。而由武威城外北流的石羊河,亦即汉时的谷水和唐时的马城河,其河谷也是一条南北向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上的军事行动就显得较多。西汉时李陵北征匈奴,即由居延北行,出遮虏障,而至于浚稽山上[732]。居延县和遮虏障皆在今额济纳旗,正是张掖河行将入居延海处。到了唐代前期,这两条道路都是突厥不时南下必经之地,军事行动尤为繁多。
唐代后期,河西多故。吐蕃借安史之乱,据有陇右、河西。其后吐蕃衰乱,沙州张义潮以瓜、沙、甘、肃来归。寻而回鹘余部亦散居甘州等处。于是丝绸之路就逐渐失其作用。胡商使人即使有所往来,也不一定仍然遵循旧日通行的大道。五代时,党项族散居于邠宁、鄜延、灵武、河西间,而居于灵、庆诸地者尤为剽悍。这些地方约当于现在陕北、陇东和宁夏,当时的灵州治所就在今宁夏灵武县,庆州治所则在今甘肃庆阳市。这时甘州回鹘朝贡中原王朝,经过灵、庆之间,往往为当地部落所邀劫,甚而执其使者,卖之他族,以易牛马。为什么甘州回鹘舍正路而不由,而出此不安谧的道途?据说是“唐亡,天下乱,凉州以东为突厥、党项所隔”[733]。唐末五代党项逐渐强大,稍后的夏国曾数以公主下嫁回鹘,其时回鹘方强大,牙帐在漠北,何得远至张掖河畔?王延德自拽利王子部西行,历阿墩族而至马鬃山。此山迄今仍以马鬃为名,其主峰在甘肃玉门镇北。其东距张掖河亦非过远,故王延德于渡过合罗川后即可直至马鬃山。王延德由马鬃山西行,又历格啰美源。据说这是“西方百川所会,极望无际,鸥鹭凫雁之类甚众”。这样的大湖泊惟冥水下游所入之海足以当之。冥水即今疏勒河。然其地远在马鬃山之南,王延德若至其地,似更近于西夏。由马鬃山再西,历小石州而至于伊州,也即现在新疆哈密市,已在河西的西北。由伊州至高昌,当时大道仍可通行无阻。王延德此行约略与十六国时期仍袭用北凉国号的沮渠安周之通使东晋相似。沮渠安周为沮渠无讳之弟。沮渠无讳其时据有高昌,借敦煌一途与东晋互通往来。沮渠安周时,敦煌以东皆已为北魏所据有,沮渠安周所派遣的使人只好由现在新疆若羌越过阿尔金山口,进入吐谷浑属地,再继续向东南进行[734]。沮渠安周的使人和王延德所行皆已远离河西,只是在河西大道难于通行时,使丝绸之路不至完全中断而已。
西夏占据河西,确实使丝绸之路的交通受到一定的困难,却也不是就此阻阂不通。下迄北宋,西域使者还是往来不绝。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于阗使人说:“昔时道路尝有剽掠,今自瓜、沙抵于阗,道路静谧,行旅如流。”[735]哲宗绍圣(公元1094-1097年)中,知秦州游师雄言:“于阗、大食、拂菻等国贡奉,般次踵至,有司惮于供赉,抑留边方,限二岁一进,外夷慕义,万里而至,此非所以来远人也。”北宋政府接受这样的意见,自后朝享不绝,讫于宣和(公元1119-1125年)之时[736]。但对于回鹘,却是多方限制,据《宋史》记载:“回鹘使不常来,宣和中,间因入贡散而之陕西诸州,公为贸易,至留久不归。朝廷虑其习知边事,且往来皆经夏国,于播传非便,乃立法禁之[737]。”这些记载都显示出丝绸之路有些阻阂,当时的中原王朝也应有一定的责任。
这条大道在蒙古统治时期还有一段畅通时期,也为敦煌莫高窟中增加了若干色彩。可是这条道路后终于萧索下去,河西当然也受到影响,至少在经济方面显得多些。不过河西还有其他有利的因素,仍然能不断发展下去。
注 释
[601]《史林杂识·初编·瓜州》。
[602]《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沙州·瓜州》。
[603]《元史》卷六〇《地理志》:“瓜州,宋初陷于西夏。夏亡,州废。元至正十四年复立。二十八年,徙居民于肃州,但名存而已。”
[604]《汉书》卷五五《霍去病传》。
[605]《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籍端水本作南籍端水,“南”字误衍,今删去。
[606]《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本)第10章《古代边境线的发现》:“库鲁克塔格斜坡南界三百尺以上的高沙丘之间,有一大片盆地,盆地中间有一连串显明的干湖床。……这些湖床证明是古代疏勒河的终点盆地,如今河流的终点是在更南十五里的大泽中了。以前相信疏勒河注入喀喇淖尔,现已证明还在更东边相差经度有一度以上。”疏勒河即汉时的籍端水,喀喇淖尔应即胡林翼图上的布鲁湖和花海子、青山湖。冥泽的故地应如斯坦因所说在其北的干湖床,喀喇淖尔当是泽地向南移动所构成的新泽。
[607]《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沙州》:“寿昌县,本汉龙勒县。”唐寿昌县在今敦煌市西南。
[608]出版于1934年的《中华民国新地图》标绘哈拉池(图上作喀拉湖)于敦煌市西北玉门关之东,则又向东移徙了。
[609]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编《中华民国新地图》。
[610]《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6章《从额济纳河到天山》。
[611]《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传》:“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张骏之世,取于秦陇而植之,终于皆死,而酒泉宫之西有槐树生焉。”嘉庆《大清一统志》所载有森林诸山,其西亦仅止于高台县。高台县在酒泉之东,似酒泉之西本来就没有林木,现在酒泉之西各绿洲上,树木葱茏,敦煌附近尤多。莫高窟前大泉河的上源也有不少树木。这些可能是出于人工栽培,已和《晋书》所说不同,论现在河西的森林者,对此似当多加留意。
[612]《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甘州》。
[613]拙著《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
[614]这是在敦煌时承敦煌研究所李正宇同志见告的。李正宇同志现正在研究唐宋时期敦煌的河渠泉泽,这应是实际调查的结果。
[615]对于月氏和乌孙的问题,日本国白乌库吉、藤田丰八、加藤繁等皆曾有论著发表。近年松山寿男著《古代天山历史地理研究》,于乌孙的原居地定为博格达山北麓。他是根据下面这些材料得到这样的结论的。一、《太平御览》卷一六五《州郡部》引《梁氏十道志》所说的:“庭州,雍州之外,流沙之西北,前汉乌孙旧地,东与匈奴接,历代为胡虏所居。”二、《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典》所说的:“庭州(原注,今理金满县),在流沙之西北,前汉乌孙之旧壤,后汉车师王之地,历代为胡虏所居。”三、《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也说:“金满,流沙州北(西北之误),前汉乌孙部旧地,方五千里。后汉车师后王庭,胡故庭有五城,俗号‘五城之地’。”书此以备一说。
[616]《新华社新闻稿》第6497期。
[617]《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
[618]《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二《凉州》引。
[619]《水经·<禹贡>山水泽地篇注》。
[620]《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甘州》。
[621]《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引《西河故事》。
[622]《后汉书》卷六五《张奂传》。
[623]《汉书》卷六《武帝纪·注》引应劭说。
[624]《晋书》卷八六《张轨传》。
[625]《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传》。
[626]《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
[627]《旧唐书·地理志》。按:两唐书《地理志》皆未载天宝年间沙州户口数。《旧唐书·地理志》有旧户口数,《新唐书·地理志》以之为贞观年间户口数,天宝时,凉、甘、肃、瓜四州户口数较之贞观年间皆有增长。沙州虽无天宝年间户口数,然总不会低于贞观时,故一并录出贞观户口,以备参考。
[628]《元史》卷六〇《地理志》,河西共有甘州、永昌、肃州、沙州四路,四路中仅甘州、肃州两路有户口数。甘州有户1550,有口23987。肃州路有户1262,有口8697。皆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数字。
[629]《大清一统志》于各府州户口一栏共列有:1.原额民丁,2.今滋生民丁男妇大小,3.屯丁男妇大小,4.户数等四项,安西州无原额民丁,亦无屯丁男妇大小。故知今滋生民丁男妇大小一项为当时实有口数。其余两项与实有口数无关,故不取。在这些数字中,户口比例颇有极大悬殊,如肃州只有22537户,却有319768口,平均每户超过14人,似与实际未能完全吻合。
[630]《明史》卷三二九《西域传一·土鲁番传》。
[631]《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632]《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
[633]《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
[634]《旧唐书》卷一〇九《契苾何力传》。
[635]《清史稿》卷一二六《食货志一·户口》。
[636]《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637]《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利鹿孤载记》。
[638]《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
[639]《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
[640]《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
[641]《晋书》卷九五《艺术·鸠摩罗什传》。
[642]《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传》。
[643]《隋书》卷六七《裴矩传》。
[644]《旧唐书》卷五五《李轨传》。
[645]《旧唐书》卷五五《李轨传》。
[646]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647]《全唐诗》卷一九九。
[648]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三《西胡考上、下》《西胡续考》。
[649]《吕思勉读史札记》戊帙《胡考》。所谓九姓胡为:药罗葛、胡咄葛、啒罗勿、貊歌息讫、阿勿嘀、葛萨、斛嗢素、药勿葛、奚邪勿。
[650]《旧唐书》卷一〇三《王君㚟传》。
[651]《旧唐书》卷一三四《浑瑊传》。
[652]《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按《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王君㚟死后,玄宗命郭知运讨逐回纥,王君㚟为河西陇右节度使,是由于郭知运死后,取代其位。王君㚟被害后,何能再有郭知运讨逐回纥事,《旧唐书》此处当有误文。
[653]《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陇右道下》,《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
[654]沈亚之《沈下贤文集》卷一〇《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尝与戎降人言,自瀚海以东,神乌、敦煌、张掖、酒泉,东至于金城、会宁,东南至于上邽、清水,凡五十郡六镇十五军。皆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田牧种作,或聚居城落之间,或散处野泽之中。”
[655]《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又卷四〇《地理志》。
[656]《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
[657]《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
[658]《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659]《旧唐书》卷一九二《回纥传》,《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传下》。
[660]《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661]《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
[662]《明史》卷三三〇《西域传》。
[663]《明史》卷三三〇《西域传》。
[664]《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665]《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
[666]《隋书》卷二九《地理志》。
[667]《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
[668]《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669]《张说之文集》卷一二《大唐开元十三年监牧颂德碑》。
[670]《明史》卷九二《兵志》。
[671]《史记》卷一一〇《匈奴传》。
[672]《汉书》卷五《景帝纪》。
[673]《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七》。
[674]10《旧唐书》卷一〇三《王忠嗣传》。
[675]《明史》卷九二《兵志》。
[676]《清史稿》卷一四七《兵志》。
[677]《汉书》卷六四上《主父偃传》。
[678]《汉书》卷六四上《主父偃传》。
[679]《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
[680]《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
[681]《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682]《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
[683]《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
[684]《汉书》卷六《武帝纪》。按:《地理志》,武威郡置于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酒泉郡置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皆与《武帝纪》不同。《西域传》:“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征和中,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武威、酒泉郡始置于元狩二年,与《西域传》所言相符。故两郡建置之年,应以《武帝纪》为正。
[685]其时凉州人口亦有被徙他处的。《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坚曾徙姑臧豪右七千余户于关中,即其一例。
[686]《唐书》卷八七《凉武昭王传》。
[687]《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唐纪一二》,又卷二一三《唐纪二九》。
[688]《全唐诗》卷四一九,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西凉伎》。
[689]《三国志》卷二七《魏志·徐邈传》:“明帝以凉州绝远,南接蜀寇,以邈为凉州刺史,……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广开水田,募贫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
[690]《后汉书》卷七六《循吏·任延传》:“(建武中),拜武威太守。……河西旧少雨泽,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皆蒙其利。”
[691]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二六七《凉州府》引《明统志》。
[692]《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二《甘州》。
[693]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二七八《肃州》:“肃州城,明洪武二十八年因旧改筑。”又引《河西旧事》,“禄福城,隋谢艾所筑”。明时所谓旧城,当即谢艾所筑,亦即在汉禄福城址筑成的。
[694]《晋书》卷八六《张轨传》。
[695]《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696]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二六七《凉州府》。
[697]《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
[698]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699]《五代史记》卷七四《附录三·吐蕃传》。
[700]《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下《陇右道下》。
[701]《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702]《隋书》卷二八《百官志》。
[703]《隋书》卷六七《裴矩传》。
[704]《隋书》卷二八《百官志》。
[705]《隋书》卷六七《裴矩传》。
[706]《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传》。
[707]《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吐蕃传下》。
[708]《史记》卷五《秦本纪》。
[709]《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传》。
[710]《汉书》卷六一《张骞传》。
[711]《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712]汉陇西郡西北界直抵黄河。匈奴与陇西郡接壤,其辖地也已至黄河岸边。这里特别提到陇西长城。乃是指秦始皇使蒙恬所修筑的长城。秦始皇的长城与其祖秦昭襄王的长城一样,起于临洮(今甘肃岷县),至狄道(今甘肃临洮县)后直向北行,再循黄河而下。《大宛传》所说的“至陇右长城”就足以作为证明。
[713]《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
[714]《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会州》。
[715]《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716]《文选》卷九。
[717]《后汉书》卷一下《光武纪》。李贤注:五郡谓陇西、金城、天水、酒泉、张掖。按:窦融时为河西五郡大将军,所率领的五郡中有武威、敦煌,而无陇西、天水,李注盖误。
[718]《汉书》卷六《武帝纪》。
[719]《史记》卷六《秦始皇帝本纪》。
[720]《后汉书》卷一三《窦融传》。
[721]唐长孺《北凉承平七年(公元449年)写经题记与西域通往江南的道路》(刊《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
[722]《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传》。
[723]唐长孺《北凉承平七年(公元449年)写经题记与西域通往江南的道路》。
[724]《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725]《隋书》卷六七《裴矩传》。
[726]《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
[727]《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西州》。
[728]王去非《关于大海道》(刊《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
[729]《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730]《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注》引阚骃说。
[731]王去非《关于大海道》。
[732]《汉书》卷五四《李陵传》。
[733]《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
[734]唐长孺《北凉承平七年(449)写经题记与西域通往江南的道路》。
[735]《宋史》卷四九〇《于阗国传》。
[736]《宋史》卷四九〇《于阗国传》。
[737]《宋史》卷四九〇《回鹘国传》。
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期、1989年第1期。
葛剑雄:对中国人口史若干规律的新认识
内容提要:本文在研究中国人口史的过程中通过深入反思,从而对中国人口发展的周期和周期性、人口过剩和人口爆炸、中国人口发展变迁的决定性因素等若干带规律性的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人口数量的变化是否存在周期性特点,目前还无法确定;中国人口史上不存在人口爆炸,增长从来没有出现过“大起”,而只有“大落”;中国并不存在单纯出于人口压力而产生的社会动乱。0002纪念张政烺诞辰110周年丨张政烺:我在史语所的十年
一九三六年我进历史语言研究所,被分配做图书管理工作,至一九四六年离开史语所到母校北京大学任教,在史语所服务近十年之久,先后历任图书管理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这期间正是国难当头,人民颠沛流离的时期。史语所在傅斯年所长果断和艰辛的筹划和指挥下,一九三七年秋全所人员携带大量珍贵资料迁往长沙,接着又辗转大西南,一九四○年才在四川南溪县李庄安顿下来。我要新鲜事2023-05-29 06:16:410000黑龙江龙:亚洲大型食草恐龙(体长10米/6500万年前)
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目前中国已掘出了174种恐龙化石,并为其命名。而这在其中,以省命名的恐龙不少,比如山西龙、黑龙江龙等,今天小编就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黑龙江龙。黑龙江龙基本资料体型:黑龙江龙是一种亚洲的小型食肉恐龙,它体长9-10米,与威拉弗龙、旧鲨齿龙差不多大,体型在已知774种恐龙中排第161位,生活在距今7000万年-6500万年前的晚白垩世。黑龙江化石我要新鲜事2023-05-08 02:32:500000民国时期三个上海滩大姐大,曾经黑白通吃,最后却都不得善终!
民国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由于受到清末儒学文化的深刻影响再加上后面西方洋文化的传入,民国这个时期为我们创造出了很多很优雅霸气的代表性女性。就我们熟知的来说就已经有著名的宋家三姐妹,还有张家姐妹花四个以及才女林徽因、陆小曼以及张爱玲等等。可以说因为那个时代,中国的历史上多了很多的名媛和才女。我要新鲜事2023-05-25 16:42:28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