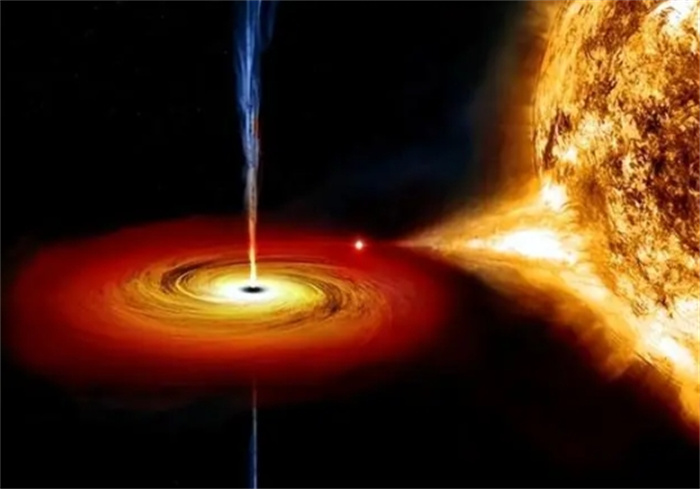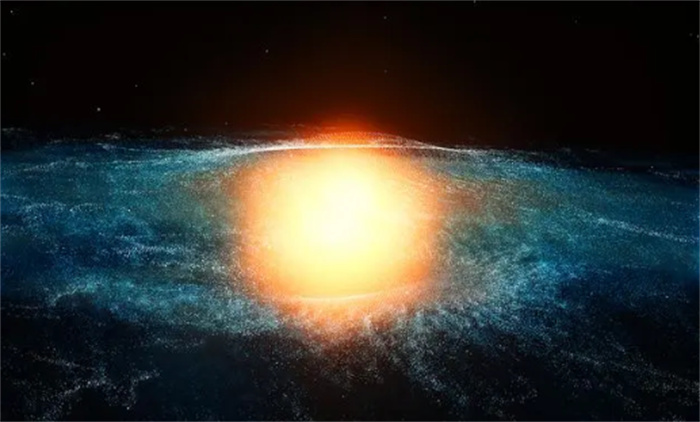严耕望:社会科学理论只是历史研究的辅助工具,不是主导方法
问现在新的风气,要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来研究历史,你对于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答这一点我在《治史经验谈》的第一篇中已谈过,大意是赞同运用各种社会科学方法与理论作为治史工作的辅助。但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在史学上的运用也各有局限,不能恃为万应灵丹。而且社会科学种类繁多,对于史学的研究可说都可能有相当辅助作用,但这样繁多的学科,一个人事实上不可能都能通解。现在我再想更进一层谈几句。
史学研究是要有辩证发展的基本观念,运用归纳法求得新结论;演绎法只可用作辅助方法,不能滥用为基本方法。大陆上一些左派史学家抱着社会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治史的万应灵丹;实际上只是依据未经深入研究而主观拟定的结论与概念,来加以演绎推展,应用到历史事件上去。每一论题大体都先有了一个结论或者意念,这个结论或意念是由他们奉为神圣的主义思想所推演出来的,然后拿这个结论或意念作为标准,在史书中搜录与此标准相合的史料,来证成其说。中国史书极多,史料丰富,拿一个任何主观的标准去搜查材料,几乎都可以找到若干选样的史料来证成其主观意念,何况有时还将史料加以割裂与曲解!
唯物论强调物质生活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因素,政治与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我本来是非常同意这种看法的,所以特别注意经济史,我计划中的《唐代人文地理》也以经济地理所占分量最重。但要像他们那样研究历史,实际上等于没有做工作。因为研究工作就是要找出新的结论,新的概念,既然结论概念都已有了,何须再要研究?这种工作要说有意义,那只是用来巩固什么主义思想的权威性。所以这些所谓史学工作者,只是响应当政者“学术为政治服务”这一个相当坦率的口号,而趋附权贵,不是真正的史学家。所幸近几年来,大陆上的史学工作者,“念经”的文章已渐见减少,转而再走踏实之路,有可看的文章了,这是个好现象!
从另一方面来说,若是大力宣扬运用社会科学方法与理论来治历史,也有偏差。我的意见,运用社会科学方法与理论研究历史本是条很好的途径,可以采取;但过分强调,毛病也很大。我看到好些论文,什么理论、什么模式,不一而足。模式理论有时诚然可以用来帮助理解问题,分析问题;但过分强调,盲目的遵行,研究问题也不免先有了一个概念,甚至有了一个想像中的结论,然后再选样式的找材料,加以证明;也就是找一些合乎模式的材料,再把模式套上去。
这种风气之所以流行,我想除了运用这类理论模式研究历史,有时诚然可以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之外,可能还有两个原因。其一,这是西方史学研究的新动向。青年人留学海外,惊为新奇,不免趋新向往,回国以后,更恃为法宝,以此自矜。其二,抓住一种理论模式来研究问题,工作上要简单容易得多。因为先有一个架子,再找一些材料往上敷砌,就不难。而传统治史方法是要空荡荡的毫无一点预先构想,完全凭些散沙般毫无定向的零碎材料,自己搭起一个架子,自成一个体系。更明白的说,要从史料搜罗、史事研究中,建立自己的一套看法,也可说一番理论;而不遵行某一种已定的理论为指导原则,来推演史事研究。换言之,要求理论出于史事研究,不能让史事研究为某一种既定的理论所奴役。这种研究方式自然要吃力得多。避难趋易是人类的天性,所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一经引进,就成为史学界的新动向!
但1979年我在耶鲁大学,以此项问题请教余英时兄。据他说,这一学派在西方史学界仍只是一个小支流,人数并不很多,而正统的史学家仍居主流。他们的工作仍是着重在史料,根据史料实事求是的研究事实真相,并不标立理论,遵用模式。大约西方正统史学,学起来比较困难,而讲理论模式的方法,比较容易吸取,应用到中国史研究上也比较容易写成论文,所以大家乐于吸取这一类方法,成为一时新风尚。最近几天,我偶翻过去生活日录,看到1974年7月在一次严肃的会议席上发言,也谈到此一问题,认为运用社会科学理论解释历史,是一项好的进展,但我希望这是历史研究方法的一项“发展”,而不是“交替”(替换)。所谓“发展”是在传统方法上再加上社会科学理论的解释,“交替”是放弃传统方法,而过分重视从社会科学理论去作解释。我现在仍坚持此项意见,应不可易。若是鄙弃传统方法,而以理论解释来替代,我担心可能愈来愈走上空疏虚浮一途,重蹈明末王学末流的覆辙,束书高阁,游谈无根!所以总结起来说,我对于社会科学方法,不但绝不排斥,无宁说非常赞成;只是绝不赞成奉为法宝,在史学研究上到处滥用!
来源:《治史三书》
李零:说龙,兼及饕餮纹
中国人,逢年过节,经常舞龙舞狮。舞龙是中国艺术,舞狮是外来艺术。龙是模仿什么动物?它的早期形象是什么?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一、龙是想象的动物我要新鲜事2023-05-29 04:38:220000陈志华:文物建筑保护科学的诞生
0000王巍:聚落形态研究与中华文明探源
0000喙嘴龙:最早的翼龙(体长60厘米/生活在侏罗纪中晚期)
对于翼龙,大家肯定不陌生,它是一种能飞的恐龙,在当时恐龙界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在翼龙中,喙嘴龙是不可忽视的,它是最早的翼龙,接下来就随小编一起去了解看看。喙嘴龙:最早的翼龙体型:喙嘴龙生活在一亿三千万年前的侏罗纪中晚期,它身长1-2米,体重10公斤。喙嘴龙是最早的翼龙,它尾巴很长,末端有一个舵状的皮膜,所以被称为长尾翼龙,后来逐渐被短尾的翼手龙所取代。我要新鲜事2023-05-08 01:12:170000NBA全明星赛编年史:1957绿军传奇
1956年,比尔-拉塞尔加盟NBA,并立即在波士顿建立不世伟业,然而拉塞尔并未入选1957年全明星赛,尽管这届全明星赛重回波士顿,第三次在这里举行,原因很简单,他受伤了,菜鸟赛季总共才打了48场比赛(拉塞尔也未拿到最佳新秀,给了同年进入NBA的队友汤姆-海因索恩)。我要新鲜事2023-05-31 22:28:37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