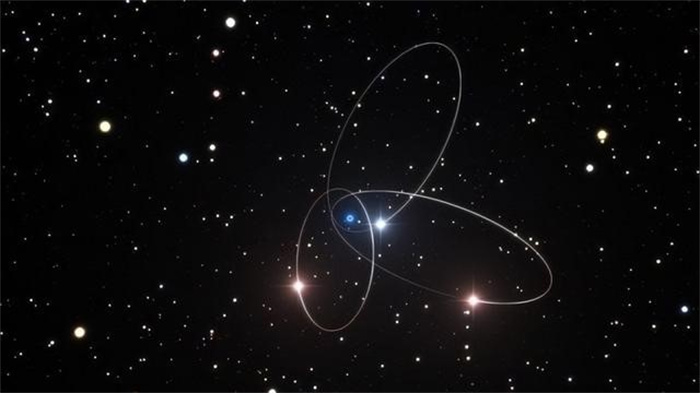陈星灿:中国古代考古学最精彩的一本书
张光直先生在大陆出版的著作主要有三联书店的“张光直作品系列”和辽宁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张光直学术作品系列”,前者包括:《中国青铜时代论集》、《中国考古学论文集》、《考古人类学随笔》、《蕃薯人的故事》;后者包括:《古代中国考古学》、《商文明》、《美术、神话与祭祀》、《考古学:关于其若干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再思考》。另外还有《考古学六讲》和《青铜挥尘》等。
如果说有哪一部关于中国考古学的书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持续而深远影响的话,也许知情的学者都会举这部《中国古代考古学》。这部著作原是张光直先生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1963年正式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后在1968年、1977年分别修订出版了第二和第三版。后者很快由日本考古学家量博满先生译为日文出版(东京:雄山阁,1980年)。1987年,该书的第四版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推出,但正像作者在该书卷首所说,这是一本全新的中国古代考古学著作,虽沿用旧名,但内容和解释都和前三版迥异,是真正的所谓“旧瓶装新酒”。
该书自1963年出版以来,不仅好评如潮,而且几乎成了所有非中文世界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考古学、上古史的教科书和参考书。它的引用率之高,恐怕罕有其匹。但是由于语言的和中国大陆与外部世界的隔离等原因,它在大陆的影响——尤其是该书的前三版——反而非常之小。该书第四版面世后,很快在大陆有所反应。1988年我读到此书,并很快写了书评;长期从事商周考古的杨锡璋先生也著文予以介绍(两文均见《考古》1990年11期)在此之前,张光直先生曾经自己翻译其中的第五章,名为《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在大陆发表(见《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周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但九十年代之前,大陆一般读者只能从这些零星介绍和单独抽出的篇章中,体会原著的内容,难以窥见全豹。
1994年,该书译者印群先生选择该书第三版的商周部分翻译出版,经张先生同意,名为《中国古代文明之起源与发展——当代美国著名学者谈中华文明史》。全书仅15万字,由山东大学教授刘敦愿先生作序,在辽宁大学出版社印行。稍后,印群又选取该书第四版,翻译了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部分,仍以同名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增订本,1997年)。增订版为了吸引读者,改换了章节的名字和次序,把该书最精彩的第五章放在前面,又把新石器时代早期发展的部分,作为附录放在全书的最后。南开大学教授王玉哲先生为该书作序。该书原著第四版除对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背景特别是它同历史学的关系有一个独到的概述外,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自然地理背景以及农业发生之前的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文化。这是中国文化产生的舞台和背景,也是新版中张光直先生着力最多的部分之一。但是由于中文版书名的限制,这些部分全部省略了。因此,1997年出版的增订本,虽然篇幅扩大至30万字,但仍是一个不完全的节本。另外,两种中文版的印数很少,即使在考古界也没有多少影响。这次请印群先生重新翻译原著第四版,据我所知,这是中文的第一个全译本,也是迄今为止了解中国古代考古学最为精彩的一本书。
该书自1963年出版以来,几乎每隔6年就要修订再版一次,这一方面说明它拥有广大的读者,另一方面也显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日新月异。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张光直先生就收集资料准备该书第五版的修订工作。他把每一项重要的发现和与此相关的重要论文,都复印出来,分别门类,以备修订之用但是,由于健康方面的原因,第五版迄今没有完成。这在病中的先生说来,肯定是一件不小的遗憾。但是就我所知,自该书第四版发行以来,虽然时间过去了14年,中国考古学在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又有许多新的重大发现,但是该书的框架结构和它对中国古代文化所做的解释,依然没有过时。作者在卷首所作该书在未来十年内其框架不会失效的预言,不仅体现了作者的自信和学术洞察力,大概也是先生没有急于动笔的一个原因。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古代考古学(夏商及其以前),其重大发现主要体现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长城地带及其以北地区,这些重要的发现改变了传统上对中国历史一元的看法,尤其值得关注。关于这些新的发现,读者可以参看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考古五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此不赘述。关于先生对这些发现以及这些发现所带来的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的反思,同时也是对先生本人一生学术研究的反思,体现在近年来他的系列文章和采访录中。这些文章不少已经收在他的文集《中国考古学论文集》、《考古人类学随笔》(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中。文集没来得及收集的两篇重要文章,一是《历史时代前夜的中国》(China on the eve of the historical period),收在新出的《剑桥中国上古史》(1999年)里,是全书的第一章。它基本上可看作是《中国古代考古学》第四版的缩影,但补上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重要考古发现。另外一篇,名为《二十世纪后半的中国考古学》(《古今论衡》创刊号,1998年),通过对《中国古代考古学》(张先生自谓此书为《中国古代考古》)一书前后几版的分析,解剖考古学新发现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冲击和中国古代文明多元认识的形成。
最近十多年来,张光直先生一直在同病魔做斗争。在此期间,除承担繁重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外,又撰写了大量的论著。其用力之勤,用心之专,意志之坚强,都使我们后学感动。1994年9月至1995年10月在台北工作期间,有案可查的讲演记录就有六次(《田野考古》第六卷,1999年),内容涉及中国考古学的许多方面。1994-1997年他又数度坐轮椅来到北京,并曾奔赴他念念不忘的商丘考占工地。据说他在台北做脑细胞移植手术期间,还完成了早年生活学习的自传《蕃薯人的故事》。要知道所有这一切的取得都是在常人所不能想象的痛苦和折磨中完成的。先生的身躯虽小,然骨头是最硬的。在他的身上,我真正体会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伟大。
原始祖鸟:最古老的窃蛋龙类(不足火鸡大小/酷似鸟类)
原始祖鸟是一种兽脚亚目下的有羽恐龙,诞生于1.28亿年前-1.1亿年前的白垩纪早期,体型仅仅和现代的一只火鸡差不多大小,体长普遍只有1米左右,属于小型恐龙的一种,是比中华龙鸟更加接近鸟类的恐龙,因为比始祖鸟还要更加古老而得名。原始祖鸟的体型我要新鲜事2023-05-10 10:31:390000法国印象派画家和雕塑家Edgar Degas 2
我要新鲜事2023-06-03 10:25:140000段勇:博物馆是人类伟大且成功的创造
2011年,在上海举办的第一期“全国博物馆新入职员工培训班”上,笔者有感而发:博物馆与学校、医院、寺观教堂一样,是人类创立的最伟大且成功的社会机构之一。之所以说它伟大,是因为博物馆能帮助人类更好地了解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是怎么从过去走到现在的,未来又可能向哪里去。我要新鲜事2023-05-26 12:46:340001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丨四川金川刘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文物考古工作高度重视,我国文物考古工作取得巨大进步和辉煌成就。这十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推介活动,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田野考古发掘项目。我要新鲜事2023-05-07 00:56:330001资讯 | 敦煌、云冈、龙门、大足四大石窟发展联盟成立
遗产编辑中心5月30日,石窟寺考古与考古报告编写座谈会暨四大石窟世界遗产地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洛阳举行。我要新鲜事2023-05-07 17:11:47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