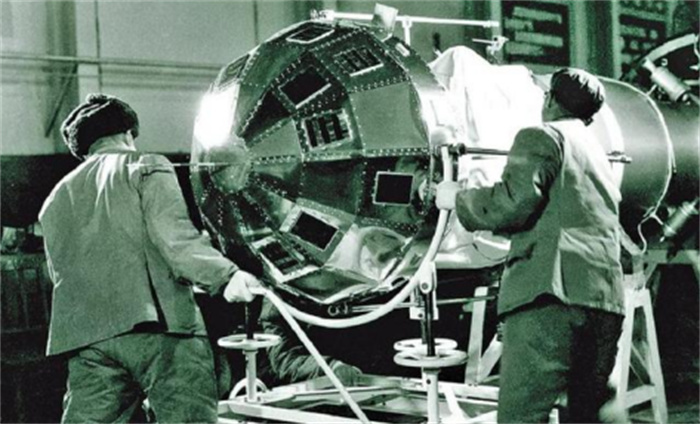郭大顺:关于良渚文化的几点思考——良渚遗址申遗有感
2015年6月有幸参加在京举办的关于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文本的讨论会,受严文明等先生发言启发,又看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权力与信仰——良渚文化展”,有些思考当时做了记录,题名《良渚三题》。主要是讨论城墙与水坝的关系,以莫角山为中心的布局和与古史传说的结合。四年后的2019年7月,得知良渚遗址申遗成功,又有些感受,结合2015年《良渚三题》,写成本文。
良渚遗址多年持续的考古工作并年年有新收获,据我的有限了解,除各级政府重视和有一支勤劳智慧的考古团队以外,是与制定遗址五年考古规划分不开的,规划使课题更明确,也有助取得各方面合作与帮助,对大遗址考古是重要经验。牛河梁遗址下一步考古工作尤其应该学习。
下面对良渚古城谈几点补充认识,关于遗址本身,有三点想法:
一是内城城墙功能问题
01
城墙的宽大于高,是以防卫莫角山免受水患而建的,功能同于水坝。这里要提到上古时期城墙与水坝的关系。曾有怀疑良渚遗址城墙的功能问题,一个理由是40多米的宽度与仅10米左右的高度不成比例。申遗文本讨论会上也有提出为什么既是城墙还要在墙顶上建住房的疑问,说明这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有水利专家等提出古城墙的防洪功能,是不容忽视的观点。为此需要明确的是,上古时期在平原或湿地所筑城墙大多以防洪为主要功能,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诸多龙山文化时期古城的出现应与此有关,南方同时期建在湿地平原的古城尤是。良渚遗址的城墙与塘山水坝在结构上有相似处也在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尤其是底部铺石块的做法,是否可能与防止坝基漏水有关,值得进一步分析,即良渚古城墙功能主要是防洪水的。良渚古城墙宽度大而高度不显以及在城墙上建房也由此得以理解。同时,良渚古城墙又有八个水门以通内外河网,这又说明良渚遗址的古城墙除防水外,还具导水功能,是防与导相结合的水利工程。为此,不必因城墙以防水功能为主而怀疑具城墙性质,也不必为强调城墙的传统军事防御性而淡化防水功能。而且,良渚遗址城墙工程量之巨大、下铺石上草裹泥夯堆的多道工序和复杂结构,正暗示当时洪水之盛和防洪引发的社会变革,甚至有学者提出洪水导致良渚人从南向北迁徙的历史大趋势的观点,看来也是可信的。
二是应有祭祀中心
02
玉器高度发达,尤其是M12大玉钺有与玉琮完全相同的“神人兽面纹”和鸟首纹组合,是表达神权更为典型的实例,表明良渚文化与红山文化一样,也具有神权至上的观念和信仰系统。为此,可以考虑应有祭祀中心遗迹,可能就是莫角山土台。台上建筑有多组,可能与各群体或不同的祭祀对象有关。莫角山土台的位置在内城的中心偏北,内城围绕其而建;良渚古城甚宽且工序复杂的城墙、外郭和塘山水坝,都是以莫角山为中心的布局和以保护莫角山为特定对象陆续建成的,最终形成对莫角山的三重保护,是当时对莫角山建筑址特殊重视的表现,也突显出莫角山在良渚遗址群和整个良渚文化中的神圣地位。尤其要提到的是,莫角山和古城墙基本都是南北正方向的,这不同于陶寺和石峁古城址,良渚先人为此而将这一超大建筑选择在两山之间开阔的低洼地,也为此而不惜动员庞大的人力、组织浩大的水利工程,这是需要以强烈的信仰作为支撑的,护卫“神居之所”是筑坝和城墙的最高目标。由此可以考虑在该文化最高层次中心应有与宫殿相比拟甚至规格高于宫殿的更为重要的遗迹,如类似于牛河梁女神庙那样的宗庙级的祭祀主体建筑遗迹,地位在作为随葬品的玉琮等玉器普遍装饰的“神人兽面纹”之上的祭祀对象。
这里引牟永抗先生1991年在中国文明起源座谈会上的发言:“在城墙和宗庙之间,我认为后者更为重要。”“随着自然崇拜经由图腾崇拜发展成直接而具体的祖先崇拜时,在崇拜形态上亦经历了由互不从属的多神信仰转变为以一神为主体的信仰模式。赋予直接而具体的祖先以原先属于自然或图腾的神力,正是现实生活中人与人关系产生质变的真实写照。由祭坛演化成为宗庙,正是这种质变的表现。很有可能,在庙堂建筑中,宗庙出现在宫殿之前。”
三是现各遗迹的年代有先后
03
大约反山墓地与塘山水坝年代较早,然后是莫角山,再后是城墙,可知作为一个整体有较长时间的形成过程。有提出良渚古城的建设应有规划,是合理的推论,或先有一个总体规划,然后分期实施,或在古城形成过程中逐步将规划加以完善,如在莫角山土台形成前先筑水坝,则显示规划意识更强。由此可以对良渚古城的中心地位和形成过程有进一步理解。
关于社会发展阶段。良渚文化以“钺壁琮”为主要组合的玉器和土台、墓葬、祭坛等遗迹,无论形制和追求正南北的方向,都是高度规范化的表现,良渚遗址以外的环太湖地区还有诸多规格较高有的也规范的遗址如福泉山、张陵山、赵陵山、寺墩等,是大中心下的多中心关系。规范化和大中心下的多中心,这是方国的两个主要特征,所以苏秉琦先生曾说过,良渚文化已进入方国时代,环太湖地区的古国时代应在先良渚文化寻找。已有线索如崧泽文化的张家港东山村和安徽含山凌家滩,需继续追索。
与古史传说的结合问题。陈剩勇先生曾力主良渚文化为先夏文化。近刘斌同志由良渚古城内外防导水系统引良渚遗址所在地的现余杭名称由“禹航”演化而来的考证,也在暗示良渚文化和良渚古城与夏与先夏有关,多有指出,良渚遗址附近的浙江地区盛夏禹传说,如会稽山与大禹墓,应都不是偶然的。新的考古发现为此提供了更有力证据,这就是城门的防洪功能,特别是以水门为主,是既防水又导水,与史载五帝时代后期即尧舜禹时代由治水不成功到成功的从堵到疏的主要事迹惊人吻合;中原和西北地区如陶寺及芦山峁等中心遗址不断出土的玉琮、俎刀可以作为夏人逐鹿中原的证据。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结合虽不必过于具体,但良渚遗址与文献的多例契合是不能忽视的。前辈学者以最终实现文献与考古结合、复原中国上古历史为学科终极目标正在实现,这也是良渚遗址极为珍贵的学术价值和进一步提高保护意识、完善宣传普及口径的决策依据,有必要继续加以论证而不必回避。
还需要探究的是,大遗址考古以布局为要,就城址来说,城内城外重要建筑及其布局的重要性要大于城墙,对此,夏鼐先生在70年代夏商大遗址会上曾一再强调过。良渚古城重要遗迹在布局上已显示规律,如城内墓地都位于莫角山西侧,其中最大墓地的反山位于莫角山西北角,其他墓地都位于城外。据俞伟超、巫鸿等先生研究,中国古代从周代起都有宫殿和宗庙筑于城内而帝王陵墓都有位于城外旷野的分布规律,只有燕下都的王陵位于燕下都东城城内,且在武阳宫的西北角,这是保持了殷墟王陵在宫殿宗庙区西北(西北岗)的古老传统(俞伟超:《战国秦汉考古》(上)22页,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3年;巫鸿:《从“庙”至“墓”》,《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98-110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庙与墓的这种布局规律及其演变,早在史前时期就已显露,从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看,牛河梁遗址无城墙发现是具“不设防”特征,却有庙宇建筑,且为庙与庙北山台(台上已发现大房址线索)与周围墓(积石冢)坛成组合配套。古建专家于倬云先生考察牛河梁遗址后著文提出,最早的庙字有“草”字头就是如牛河梁这样庙在旷野与墓在一起的写照。以此看在良渚古城内所置唯一一处规模与古城墙相称的反山墓地(在反山墓地以南新发现的墓都规模较小),在已发现的良渚文化墓地中规格最高,且在莫角山宫殿或祭祀址的西北方向,应是上古时期古老传统的更早实例,是反山墓地或具王陵规格的又一证据。
良渚遗址的布局不仅在城内已有规律可循,还应考虑城外。城东北的瑶山有方坛式建筑址。瑶山遗址在古城北部偏东的方位同于古成都的金沙或十二桥东北方向的羊子山方坛,历代祭地的地坛位置在都城以北,瑶山墓葬多琮而不见大型玉璧,都可相互印证;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良渚古城唯一的陆门在内城接近正南方向,陆门的东西总宽度超过150米,有三墩分四门道,最西门道即第一门道甚窄(8米),第二、三、四门道较宽且宽度相近,其中第二、四门道等距(宽都为18米),第三门道稍宽(20米),这三个门道应为一组,居中且稍宽于两侧门道的第三门道即南中门应为主门道,是为突出中门道的三门道,这同后世都城城门突出城内外中轴线布局的“三门道”制度可相互比较(参见徐应龙《中国古代都城门道研究》,《考古学报》2015年4期)。近发掘者著文,以为古城南陆门所在处为湿地,所以门的象征性大于实用性,更是良渚先人中轴线意识强烈的表达。开三门道的陆门同时是一个重要的指示器,因为历代祭天在城的南郊,如陆门以南有高丘等遗迹,可勘探是否在南门外布置有祭天的遗迹,如圜丘之类。现知陆门以南与莫角山—陆门北南一线的卞家山遗址发现有土台,土台以北有墓葬、灰沟,以南有码头,是由北而南依次分布的,墓葬的头向有过半非良渚文化大多数墓葬头向朝南的葬俗而是头向朝北(且头朝北向的多为随葬纺轮的女性墓),土台和灰沟附近出大量高等级漆木器、带刻划纹和精细花纹黑陶器,都是重要线索。由于良渚古城的核心莫角山建筑址破坏较甚,如古城内外的建筑布局在已有线索基础上有进一步突破,对良渚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对中华传统礼制的影响和传承,都会有更多具说服力的证据。
(2019年7月写于英国白金汉郡AMERSHAM图书馆,修改于海南省东方市汇艺蓝海湾)
本号刊载的作品(含标题及编辑所加的版式设计、文字图形等),未经中国文物报社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改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及作者。
来源 | “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
编辑 | 张小筑 实习编辑 | 刘婧涵
复审 | 郭晓蓉
监制 | 李 让
亚马逊雨林有多狠?为啥有人说亚马逊雨林是人类禁区?有何危险?
亚马逊雨林是地球上最大的热带雨林,占地约600万平方公里,位于南美洲中北部,跨越九个国家,包括巴西、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圭亚那、玻利维亚、法属圭亚那和苏利南。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为全球生态系统和调节气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什么有人说亚马逊雨林是人类的禁区?到底有多危险?我要新鲜事2023-05-28 19:51:370000宝鸡一座简陋的古墓 却出土高价值宝物(古墓宝物)
宝鸡一个简陋的古墓里发现了200多件珍贵文物。在我国的陕西地区出土了很多的墓葬,而这些墓葬当中往往都有着令人惊叹的古代文物,除了西安地区之外,陕西的宝鸡地区是古墓的重点挖掘地区。不过大多数人都认为只有一些规格比较高的古墓才会有着有价值的宝物,但实际上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宝鸡古墓我要新鲜事2023-09-20 20:16:180000诺贝尔奖首次授予古基因组学领域对古DNA和考古学研究启示
我要新鲜事2023-05-27 12:30:580000唐太宗李世民杀掉亲兄弟后,又做了几件不堪之事,暴露其秉性恶劣
在我们上历史课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有学习过玄武门之变吧,而这里面的主角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唐太宗,在历史书上,李世民被形容成比较宽容仁慈的一代贤明君王,不过如果真正的还原历史,可能会令人心寒了,因为在兵变之后,他的表现已经表现出了他黑暗的一面,那么,他之后又做了哪几件不为人知的事呢?我们接着看。我要新鲜事2023-05-25 17:20:44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