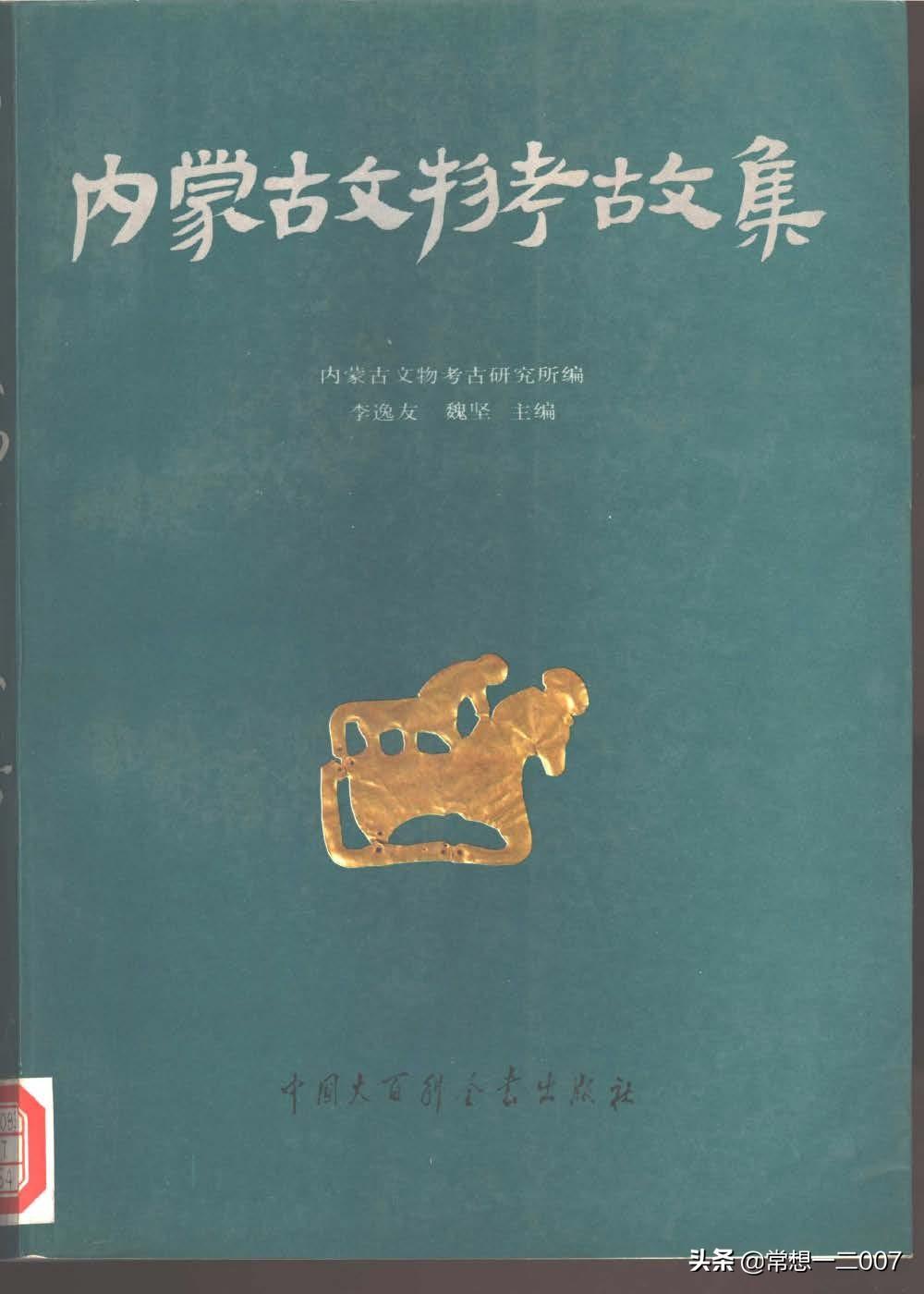赵世瑜:多元的时间和空间视域下的19世纪中国社会
多元的时间和空间视域下的19世纪中国社会[1]
——几个区域社会史的例子
一、问题之由来
近年来,社会史研究在取得迅猛发展之后,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某些社会史研究在揭示以往不曾为人所知的方面的同时,却无力关注以往史学提出、至今也还存在意义的一些重要问题[2],于是,社会史与以政治史为代表的传统研究模式之间,就形成了互不干涉、各说各话的局面,以致造成相互之间的某些误解[3]。实际上,任何新的研究尝试都不可能包打天下,包治百病,而只能对有意义的问题提出新的解答思路;这些新的思路会对旧的思路提出挑战,但这不应该是一种彻底否定,而是一种认识途径上的丰富。
社会史研究会不会或者应该不应该回避历史上的重要变革?尽管目前国内大部分冠以“社会史”头衔的研究成果的确对此较少关注,但我个人的答案还是否定的。我相信我的真正的社会史同行都不会同意说,革命前后的东亚社会或者中国社会“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在这里,“东亚社会”或者“中国社会”是否可以被当作一个同质的有机体,可以不加分别地说它有变化或者没有变化?对此,罗志田已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一文的第一部分“近代中国的变与不变”中提出,在这一时期,变与不变是“并行而共存”的,其具体的表现是沿海和内地竟成两个不同的“世界”,当然这种“多歧性”又不仅体现在空间上,也体现在不同的社会群体及思想界中等等[4]。这种看法及其中体现出的多元视角显然是我所赞同的,他力图避免的是长期以来研究主题和基本观点的单一向度。但是,如果我们再深入一些,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看,或者从多元的时空视域观察,变抑或不变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相对性。
以此立场为出发点,我们就必须去思考一个个区域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但是,这种所谓“在地化”的立场是否能够解释整体的政治变革及社会变化[5]?我个人的答案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立场一样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它可以从与以往不同的角度帮助解释这个整体的变化,也许可以揭示这个整体变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当此之际,下面的问题变得重要起来:区分变与不变是否造成了“有历史”和“无历史”的社会这样一个带有西方殖民话语倾向的两分?即使我们承认这样一个区分,那么我们能否在“不变”中把握“变”,同时又在“变”中理解“不变”?社会史学者如何面对19世纪诸多显示出巨变的事件,是视而不见还是束手无策?他们如何为揭示19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提供新的解说视角?
二、“此鸭头非彼丫头”:19世纪中叶的宁波
宁波是鸦片战争后最早开埠的东部沿海城市之一,即所谓“条约港口”(Treaty Port),这里应该属于近代以后“变”的那个世界。但它之所以被列入首批开埠城市,不仅是因为它在东部沿海的重要位置,还因为它已有很长的“开埠”历史。地理位置上,宁波“北接青、徐,东洞交、广”[6],处于南北洋的分界处,成为南北洋干线和长江干线的水运交叉点之一。这里早在唐代就有通商日本的记录,而自宋元以来浙江沿海市舶机构反复撤建的过程中,宁波市舶机构却基本上一直独立建置,成为辽东半岛至浙江海域合法进行海外贸易的唯一港口。从明中叶到清中叶开埠之前,已有欧洲人来到宁波,进行贸易[7]。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不能仅把它放在1842年以后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即使是从海上贸易——无论是从国内市场的角度还是从国际市场的角度——出发,也是同样[8]。我们在一般的叙述中提及首批五个开埠口岸的时候,往往将其作为自然而然的、相对同质的事,相对忽略了它们之间在区域历史脉络和传统上的区别,而正是这些区别导致了它们在开埠这个重大的政治—经济变动中的不同反应。
故事发生在咸丰初年。这时距开埠已经过去了10年左右的时光,太平天国运动已轰然爆发。咸丰四年,这里发生了所谓“渔镖之争”的事件,将海商、官府、由海盗转化而来的水师、洋人全部牵连其中。事件的起因在于沿海的货物运输长期以来极为繁荣,清初以来,宁波商旅遍于天下,“甚至东洋日本、南洋吕宋、新嘉坡,西洋苏门答腊、锡兰诸国,亦措资结队而往,开设廛肆,有娶妇长子孙者”。而大量的外地人口也纷纷涌入宁波,“嘉道以来,云集辐凑,闽人最多,粤人、吴人次之”[9]。由于海禁政策的缘故,海上走私活动也十分猖獗,伴随而生的则是劫掠海商和渔民的海盗。特别是到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传统运道受阻,浙江漕粮只好通过海运入京,经营北洋贸易的宁波“北号”商帮觉得有利可图,运漕商船大增,江西、两湖的货物也转道宁波集散。这样,水道的安全也就变得更为重要。
这时,纵横宁波洋面的来自广东潮州的“广盗”被地方官府招安,编为“广勇”,力图使他们为商船护航。但海商根本不相信这些亦兵亦盗的人,双方也频频发生摩擦。这批广勇又转而向渔民勒索保护费,使渔民也深受其害。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个别渔民因遭受海盗危害而获得了英国领事的帮助[10],后者介绍他们去寻求葡萄牙人的帮助,由葡萄牙人出力护镖[11]。但后来葡人及其华人代理也经常遇事生风,指商船为盗船,然后将船上货物尽行干没,官府稍作惩处,葡人即出面抗议[12],渔民不得已恢复受广勇的保护,或另与英法水手签订护镖协议。而广勇又与一家法国商行合作,后者则雇有欧洲不同国籍的水手,这样,就此事形成了复杂微妙的局面。但之所以酿成以广勇和法国水手等为一方、葡萄牙人为另一方的武力纠纷,其实又不仅在于每年数万串钱的护镖酬劳,而是在护镖过程中“合法”地大肆进行走私活动获得利益的机会。同时,“西夷本不在互市之列,因历年渔户及南北商船资其护洋,遂得停泊鄞港”[13],表明为商船护航也是一个利薮[14]。这显然说明,五口通商初期,洋人通过“规范”的贸易活动所得利润大大少于他们的预期,需要靠其他途径加以补充。
于是,咸丰四年五月,以广勇、当地“游手”及法国水手等一二千人为一方,以葡萄牙人及其西班牙帮手为另一方,发生了武力冲突,后者阵亡二十余人。葡萄牙人派舰队前来报复,却在外洋被广勇水师击败,被击沉战船三艘,俘获六艘,击毙三人。事后,葡萄牙驻上海领事要求赔偿,官司一直打到浙江巡抚那里,后者建议采用“羁縻”的手段解决,地方官便“移诸领事书,往复排解。以二国本非互市,出资作赆,劝令西归”[15]。葡萄牙、西班牙人由此退出这场利益的争夺,此后也很少来此贸易,这也或可被视为老牌殖民势力衰颓的一个缩影。
从事件的规模及其后果来看,此事并不比我们所熟知的一些晚清中外纠纷之起始事件更微不足道,但却显然完全没有引发更严重的、影响更大的交涉,甚至地方志只是在其《外国传》中记载此事,仿佛与本地毫无干系。究竟是因为受侮辱与受损害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国际事务中过时的角色,还是因为太平天国事件使列强的注意力转移?或者是因为鸦片战争中清军与英军在宁波曾经交战,地方官府希望避免烽火再起,而葡、西两国也无力与广勇背后的英法列强争斗?无论如何,这次事件悄无声息地解决,固然是与当事的洋人一方无意追究有关,但也是由于此事的起因本属于不同的洋人利益集团介入中国内部事务,与其说是中外纠纷,不如说是外人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否则,主要角色之一的广勇不会这样轻易地脱离了干系。
我们可以在这个事件中看到新的变化:这些洋人卷入此事当然是因为有了开埠这个背景,但又不仅是因为这个背景,因为故事的主角之一葡萄牙人早在明代就在宁波活动,他们,以及英国人和宁波地方的关系并非从这个时候才开始。所以在这个事件中,第一,不仅是洋人把中国或者宁波牵连到了“他们的”历史、“现代化”的历史,或者所谓资本主义的扩张史中,同时也表现为洋人被卷入了宁波本地的海上贸易的历史脉络中,被牵连进了一个已经形成多年的复杂的地方权力关系网络中;第二,虽然这些“外夷”已经换成了西洋人,但对于宁波人来说,在上千年的对外贸易史中,无论是西洋人还是东洋人,他们对于来自异域的洋人及其生活方式已经并不陌生,也已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处理方式,当地的一些士绅早已成为熟悉夷务的买办,曾凭借自己的力量劝退前来报复的葡萄牙军队。这样,“变”便被消解在了“不变”之中,或者说,今变乃是昔变之延续。相反,几年后各自有地方大族著姓为后盾的本地渔民与钱庄之间的武装冲突,倒被称为“萧墙之祸”而更受重视。因此对于宁波来讲,同样是“条约港口”、开埠城市,但由于其悠久的“开埠”传统,它又与另一些“条约港口”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这里,这个“千古未有之大变局”虽产生了相当震撼,但它却成为——至少是在这个阶段——这个具有悠久的对外贸易传统和讲求经世的文人传统之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三、从南下牧马到北上移垦:19世纪前后的土默特
让我们把视线拉到远离东南沿海那个“是非之地”的内蒙古草原。
这里同样不是一个“不变”的世界,更不是一个由于没有发生前者那样一些政治事件而“无历史”的世界。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这里的“变”不仅不同于前者那里的“变”,而且对当地人来说,也是一种“巨变”,也是“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在它们的深层之间,也许还可以找到某种若隐若现的联系[16]。
土默特地区在长城以北,阴山以南,西临黄河,东接察哈尔,地近归化(今呼和浩特)西郊,土壤、气候条件均属上乘。清初,蒙古为封禁之地,1902年正式开禁放垦。但在实际上,到这时土默特地区已有大量从内地来的汉人移民,光绪末年的移垦高潮只是18—19世纪移垦潮流的延续。因此这里的巨变是移民拓垦所带来的,是生态、生计方式、社会组织、人际关系、权力网络、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内容与工业化和“国际规则”给东南沿海带来的那些并不相同,但涉及的方面却同样广泛,对这个区域社会而言,它们给原有的社会带来的震撼并不比后者小。
导致1902年正式开禁的虽是19世纪社会的一系列变动,但这里的移民屯垦却已经历了数百年的过程,因此这里的“近代史”显然不是沿海的那部“近代史”,这里唱响的历史主旋律也并非那里的主旋律,要想不折不扣地将这里的这段历史纳入以后者为标准构建起来的国家史版本,只好削足适履。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里发生的一切完全孤立于19世纪的世界变化,只是我们还没有准确地把握它们之间的脉搏。
在土默特或丰州滩,元代便已有零星农业拓垦,但直到明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这里基本上都是牧地。明嘉靖以后,长城以内的叛卒、民间宗教会众、逃难者,以及被掳掠、被招募的汉人纷纷进入此地,建立了定居的聚落,称为“板升”,开垦土地达万顷之多。但后金天聪年间皇太极率军征服漠南蒙古,这些聚落在战火中大多被摧毁[17]。原居汉人或死于战火,或逃回内地,或融入蒙古。清初禁垦,但自康熙时又有内地汉人前来,采取春来秋归的“雁行”方式,其户口仍在原籍,从理论上说亦应在原籍纳税。于是政府也对此采取半放任的态度,规定“种地之民人……俟秋收之后,约令入口,每年种地之时再行出口耕种”。对政府分给蒙古人的份地——户口地,蒙古人也像关内旗人一样,将其租给外来汉民耕种,所谓“蒙利汉租,汉利蒙地,当时虽有私垦之禁,而春种秋归之习依然”[18]。
乾、嘉以降,内地汉人出口耕种已成为不可禁止之势,此时一味禁止已证明行不通,而完全宣布开放封禁,会违背祖宗“既定国策”,形成进退两难的态势,只好做一点局部调整。比如乾隆十三年政府就要求“蒙古部内所有民人,民人屯中所有蒙古,各将彼此附近地亩照数换给”,等于承认汉人移垦的合法性。到光绪十年,清廷正式批准民人在土默特地区落籍,这个合法性就从事实上的变成了法律上的。在这一过程中,直至清末民国时期,由于内地民人移垦引起的蒙汉纠纷大量增加,土默特档案中的大量诉讼案件就说明了这个变化。在这些案件中,土地纠纷案是相当常见的,因为耕种土地需要浇水灌溉,因挖渠争水出现的诉讼也很多,因在草场建造房屋引起蒙人不满的案件也不少。特别是从嘉庆到光绪这段时间,康乾时期移入土默特地区的内地民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渐富裕起来,从最初的租种蒙民土地变为将蒙民土地购为己有。这就使得许多失去土地的蒙民不满,这种不满情绪通过各种渠道表现出来,引起当地社会的震荡[19]。于是,旧的游牧社会秩序被已经商业化了的农业移民的进入打破,适应新变化的新秩序急需建立。19世纪便是这个地方新秩序营建的时代。
在蒙古实行的盟旗制度下,参领、佐领下的基层管理人员为领催,虽然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继续发挥制度赋予的作用,但对管理汉民村落已经力有不逮。于是雍正年间,在所谓汉人“寄民”中实行保甲制度,一村设一甲头,个别村庄会设有蒙、汉两个甲头。光绪时情况变化,甲头成为村众共同推选出来应付官府之职,其性质也从最初的一个管理内地民人的职位变为了内地民人“支应官差”之职。这说明政府已从对临时移民的管理过渡到对永久居民的管理,重点考虑其交税问题,甲头也同时肩负在赋税问题上与政府打交道的责任。
除此之外,山西移民也把原居地的会社组织形式带到这里,成为民人村落自治组织的一种形式,与甲头制度相表里。这些会社也是围绕寺庙而形成,也通过组织祭祀活动整合乡里,但也同时起到协调关系、调解纠纷、稳定秩序的作用,比如水神社在解决争水纠纷过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这显然是把山西原居地解决此类问题的传统有效方式,带到新的环境中[20]。由于这类会、社组织的亲和力,使我们在大量诉讼案件中见到所谓“甲会”并称出现,即甲头与会首共同扮演维持地方秩序的角色。在光绪年间的一起纠纷中,“领催格海呈控甲头张六九、会首赵德明等,声称托府主出谕,由各村捐办义务,令其入社,随同伊等摊办襟差。格海与甲会理较,而甲会以禀明托厅,拘锁到衙门责打管押,那时看你入社不入。说完扬常(原文如此——引者)而去”。汉人甲头、会首对原有盟旗制下的蒙古领催的固有权威地位也提出了挑战,似有在基层实际管理上取而代之的趋势。虽然地方官府还要维护原有制度的权威性,归化城厅长官批示“晓谕该村甲会等,嗣后再不准牵连蒙古摊派民社差使”[21],但这样的组织形式显然也较大地影响到了蒙古社会,而这影响的另一方面体现就是我们同时见到大量关于“蒙社”的记录[22]。
由此,我们知道,来自长城以南的移民大量涌入,给土默特地区造成巨大冲击,原有的制度——无论是国家的还是民间的——都被迫去适应这个新的变化,在适应的过程中发生冲突,在冲突的过程中日益调适。经过各种纠纷和不断磨合,到光绪年间,土默特基层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个由旗制(参佐领催)、甲头、会、社以及喇嘛等共同构建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远非完善和谐,但却是对因移垦引起的日益剧烈的社会变化的有效反应。要了解这些挑战与响应,我们仅靠西方挑战与中国响应的模式及相关的方法是无法得出答案的,仅靠了解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变化也是无法得出答案的。
四、简短的结语
我们还可以举出若干例子,这些例子的取得基于我们的区域研究实践,其结果恰好是为了使我们避免某种单线的、以某种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大历史母版来概括历史的认识逻辑,而希望从具体的历史情境去理解政治事件和制度,又反过来通过这些事件和制度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的操作去把握社会变迁。
比如,在因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和诸多学者、国民政府的关注而闻名天下的定县,我们在当年平民教育试点的那个村的邻村,看到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庙宇韩祖祠,其中供奉的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民间宗教领袖飘高老祖,现存多块碑刻说明了当地的信仰系统历经数百年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现代平民教育实验和这个信仰体系共处于同一个空间,它们之间究竟存在怎样一种张力?定县士绅长期以来不断塑造的韩(琦)苏(轼)形象,与现代平民教育运动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仅从清末改制、新学推广、思想启蒙等因素,是否能全面解释定县平民教育运动的前因后果?我们自以为(或者通过文献,包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材料)已经被明清两代统治者镇压下去的、以无生老母信仰为核心的民间宗教,在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普遍存在(这里不能详细叙述我们所见的田野资料),脱离了这些了解,我们也许对义和团事件的认识就不会全面;脱离了这些了解,我们对定县平民教育运动之类的研究始终被框定在一个现代化话语中,而脱离了具体的时空脉络。
再如,我曾随研究华南的学者前往曾经爆发太平天国运动的广西桂平,虽然没有深入调查研究,但此地的材料所显示的问题也足以对我产生巨大的冲击。在随后的田野随笔中我曾写道,此行对我以往的相关历史认识至少有两点深化。第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并没有把这里与王阳明成就其事功的平定大藤峡瑶民起事联系起来,并不觉得这两件通史叙事中的大事件发生在同一个县里。恰恰就是在那前后,外来人日益进入此地,在明代有从附近地区调来镇压瑶民的狼兵,在明末清初则有随永历政权避入西南的大批官员、军队和百姓,在清代更有日益增多的经商的福建和广东商人,于是此地渐成化内之区。不过成为化内之区的代价是外来人与“土著”之间会因资源等问题产生越来越多的纠纷,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也经常出现。太平天国运动发起时的主要成员是外来人,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土著”的生活秩序,只好靠破坏原有秩序来解决问题。也正因此,明朝瑶乱平定为大量外来移民创造的契机,就与太平天国起事有了联系。第二,我们以往总会把洪秀全及其拜上帝会捣毁偶像的行为与其信仰基督教联系起来,这样,这种行为就与近代西方列强进入中国这个大形势有了直接的关系。但当我们进入这个地区就会知道,他们之所以和那些寺庙和神灵过不去,并不是因为他们要以一神的基督教来对付中国本土的神灵崇拜,而是因为当地是以神庙为中心构成不同的社群及其行为空间,这个社群及其行为空间又通过日常的祭祀仪式被不断强固,外来人则被排除于这个社群和空间之外,也就是被排除在地方公共生活之外。没有以“在地”身份参加过游神的人,不会理解自己没“份”的那种困境。由此我们也看到了这里的“变”。这个变化是跨越明朝中叶直到19世纪的中叶,而不仅与1840年以后的事件有关。从这里燃起的火焰之所以迅速在南方燎原,也许主要并不在于清廷的压榨加重,也主要不在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而是人口流动等等原因导致的资源再分配和社会秩序再调整的欲求[23]。
这样的例子随着研究的深入还会继续浮现出来。它们显然没有回避政治史,也没有回避变化,甚至“变”与“不变”的问题在这里并不是核心。它们所回避的只是某种特定意义上的变化,即可以说是向两个“半”的转变,也可以说是“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甚至可以说它们回避的并不是这些具体的走向或过程,而是回避这种话语及其语境。我想,之所以讨论“变”与“不变”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一切现实问题似乎都和欧洲完成了工业革命、中国被动挨打的那个19世纪具有直接联系。我们将“近(现)代”的划时代或转折点意义作为“应然”接受下来,但是,为什么近(现)代这个转折或断裂比任何其他转折或断裂意义都更重大?是不是真的是因为它创造了超过以往的巨大的生产力?无论如何,因为有了对“现代性”的追求,才有了“启蒙时代”,有了“萌芽”,有了“早期现代”“前现代”,甚至“后现代”等等,它们都是以“现代”为旨归的。这些对历史时段的表达都是掌握了话语霸权的近代人群体所发明的,后者并不考虑在他们之前的那些人如何思考他们自己的时代,因为那些人“俱往矣”。
前面两个例子都在讲19世纪的变化,在社会史学者的眼里,社会绝不是静止不变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采取的仍然是历时性的眼光,而不是社会学家的共时性角度。只不过两个例子提示我们,时间的标志是人为设定的,历史时间(historical time)具有很多的层次,宁波、土默特,甚至定县、桂平不仅经历了世界历史的时间,也经历了中国历史的时间,同时还经历了它们各自区域历史的时间,在不同的时间表达中我们发现了不尽相同的历史面向。显然,如果我们不循着多元的时间线索,特别是以本地为中心的时间线索去追寻的话,我们对这些地区的历史解释是可以预先想见的。空间具有同样的特点,这两个例子已经说明了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假以时日,当我们试图将这些天各一方的区域发展整合在一起,并试图给予解释的时候,会发现19世纪的中国并不完全是现在我们所知的中国。
宁波的例子告诉我们,当中国人开始与西洋人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完全没有本钱。事情的发生本围绕中国人的利益而起,但结局却仿佛是新老殖民者的鹬蚌相争,本地人并没有承担什么责任,这个“渔镖之争”的故事便成为一个演出了多年的肥皂剧的新的一集。土默特的例子告诉我们,到18—19世纪欧亚大陆重新连成一个整体——这里主要指陆路——的时候,以往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牧马的两千年历史被翻转过来,北方汉人的移垦使长城以外的北部和西部地区真正成为帝国疆域的一部分。就整个世界历史的格局来看,这二者难道就不存在某种内在关联吗?
在区域社会史的眼光下,历史的音调是多重的,但它们无疑交织成为一个具有共同主题的混响。
[1] 本文曾提交2005年北京论坛的历史学分论坛,参与2007年于台湾举行的“基调与变奏:7—20世纪的中国”国际讨论会,并以此为题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过演讲,承蒙在场学者和同学的评论,受惠匪浅,特此说明并致谢。
[2] 参见拙文《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或《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52—70页。
[3] 例如,在2005年北京论坛历史学分论坛的“近代东亚社会的转型与重构”主题说明中,设计者有这样一段阐释:“一些人认为东亚某些国家经过百年政治革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另一些人则认为历经革命洗礼的社会与革命前的社会没有太大的差别。在这个问题上,政治史学者与社会史学者的看法有明显的差别。……这一组的学者们将围绕着对世界进程有重要影响的典型事例,借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更多地利用新发现的历史数据、特别是档案史料,从政治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关系等等新视角,来看待‘历史中的变迁’,分析其表征与实质,实现政治史与社会史之间的对话,并向原有的对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解释提出挑战。”(重点为引者所加)这个问题的提出非常有意义,即不仅是讨论“变与不变”的问题被延续到了上述台湾会议上,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政治史与社会史之间对话的机会,使二者有可能发现各自的局限性。但从这段话中仍然可以发现研究视角间的某些误解。
[4] 罗志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5] 杨念群在其《“在地化”研究的得失与中国社会史发展的前景》一文中(《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就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他在文中表达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也非无的放矢,其实我们自己也在不断地反躬自问,一些成果是否有可能成为新的学术理念训练出来的人用新的学术概念表述的新版“地方志”?显然,对于历史的重新诠释仅靠所谓“在地化经验”是不够的,我们也不认同把所谓“在地化”的实践视为学术创新的一种快捷方式。问题在于,在目前这个所谓“历史人类学”的群体中,无论是否以“在地化经验”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他们的学术训练、早期研究实践及关注的问题与其他同行没有太多区别,甚至多由政治史或制度史出身,因此他们的“在地化身份”恐怕不是唯一的身份,甚至不是主要的身份,他们的研究基础也不仅是“在地化经验”。在我看来,区域史(我不用“在地化”这个概念是因为我在研究中多不具备这个身份)不过是“感觉”历史或诠释历史的方式之一,任何方式被“过度依赖”都会有其危险性,这绝对是正确的告诫。
[6] 光绪《鄞县志》卷七四《土风》,清光绪三年刻本,叶1a。
[7] 关于19世纪中期前朝鲜、日本、安南、南洋诸国,以及葡萄牙、荷兰、英国等通过宁波开拓海洋贸易线路的记载,参见光绪《鄞县志》卷七○《外国·附市舶》。
[8] 这个例子参考了李伏媛的研究,她的硕士论文《宁波渔民:权力关系的多样性与社会变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5)所提供的事例引起了我的思考,在此特致谢忱。相关细节可参考她的论文。
[9] 光绪《鄞县志》卷二《风俗》,叶6b—7a。
[10] 据说,一个宁波渔民在舟山附近被海盗抓住,他的寡母在得不到官府的帮助之下,向其邻居英领事馆求助并如愿以偿。参见J.K.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p.335。
[11] 关于葡萄牙人很早就在东南沿海一带从事“护航事业”的叙述,参见《五口通商时代疯狂残害中国人民的英美“领事”和“商人”》,载《严中平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又,Francisco João Marques: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Ningpo Massacre,printed at Noronha's Office,H.K,1857。这是记录这一事件的主要资料,当然也因此具有片面性。
[12] (清)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4—65页。
[13] 咸丰《鄞县志》卷二九《杂识》,清咸丰六年刻本,叶24。
[14] 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1857年至1858年一年间,宁波渔船交出了“护渔费”5万元,南号的运木船只交纳了20万元,其他的船只所缴也不下于50万元。(上海:上海书店,2000年,第458—459页)
[15] 光绪《鄞县志》卷七○《外国传·西班牙葡萄牙》,叶33b。
[16] 以往学术界对于明代蒙古板升以及清代内蒙古的移垦都有不少研究,但我们在看了土默特左旗档案馆所藏数万件清代档案之后,认为对这里的了解还需要大量具体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的乔鹏、中山大学的田宓都以此为题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这里涉及的问题,使用了乔鹏在该档案馆抄录的档案资料,特此说明并致谢。此外,我在该处买得《土默特旗志》两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其中也保留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17] 明宣大总督王崇古说:“自东山西到黄河约三百余里,自沙领儿北至青山约三百余里,内有板升聚落三十余处,俺答、李自馨……等,或有庐舍,或修堡,或筑墙,或筑墩台。”((明)王崇古:《散逆党说》,《登坛必究》卷三七《奏疏一》,叶87。)据《把什村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1等页)记载,把什村,即原把什板升中的蒙古家族坟墓有10—20代之多,也就是说最老的村落定居家族可上溯到400多年前,即17世纪时。这个蒙古家族究竟最早是否蒙古人,还未可知。
[18] 绥远通志馆编纂:《绥远通志稿》卷四○上《水利》,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88—589页。
[19] 道光八年(1828)的一份案卷记载:“刘永魁籍隶山西,来土默特河尔土默特营子佃种蒙古地亩,盘剥获利有年,巴牙尔台曾借刘永魁东钱一百九十吊,屡经逼讨,巴牙尔台将园地六亩,熟地十五亩当给刘永魁,尚欠东钱七十吊,无奈以应收租项当给折欠,因尔怀恨,后向刘永魁之弟刘永元借钱,复被刘永魁拦阻,不为借给,巴牙尔益为忿恨,适刘永魁父母先后亡故,因蒙古地方向来不准民人葬坟,刘永魁暂租蒙古隙地,于上年三月十二日埋葬之后,巴牙尔台意以刘永魁本屡佃种伊等地亩起家,竟敢任意葬坟,随邀素与刘永魁不睦之蒙古莫霍尔南沁喇嘛拉什、民人保成子、张不头等共六人,于四月二十七日夜间分持锹错去刨刘永魁父母坟冢”,并最终将刘永魁父母“尸身刨扬”。但最终的判决是,“查向来蒙古地方不准民人葬坟,应札饬所属府州各县,出示晓谕,佃户、商人各以刘永魁为戒,嗣后其有亡故者,仍前浮厝,或代量力送回原籍埋葬,违者治以应得之罪,并行文住居民人之各扎萨克,一体知照”(原件藏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对傅斯年图书馆允我打印该项数据,特表谢意)。这种权宜之计显然并不能让按传统做事的汉民满意。又如,“具呈人纳参领兼佐领下蒙古恩受,年二十九岁,住城东苏计村,距城九十里。为屡欠租银,抗不偿给,祈恩饬宁远厅查卷,地归蒙古,以免失落无着事。缘小的等先人七户蒙古户口地二十二顷余,租给民人花户承种,每年宁远经征租银三十二两,交给小的等七户分散。迨至光绪十年,花户报退八顷有余不堪耕种,每年应得租银无几,以致众蒙古赤贫如洗。又至二十八年,花户弃地逃走,遗留地五顷六亩,现在小的等承种。荒芜者多,耕种者少,宁远至今应征九顷有余,地租银花户分交,不能短欠,小的等更不能见租。现在荒抚(同‘芜’),不堪耕种,逃亡绝户,短欠旧租,该厅原差勒逼,向甲、会讨要。此租与甲、会无涉,将二个甲、会勒拿管押在班。祈恳宪天饬宁厅将九顷有余地原归蒙古,将甲、会开放还家。眼看年节临迩,情迫无奈,为此星夜匍匐来辕,叩乞都宪老大人恩准作主。迅速饬厅查卷,地归蒙古。以免将来失落无着。施行。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此案说的是汉人租种蒙古土地后弃耕而逃,赋税负担落在原蒙古土地所有者身上,但如民人属于租佃,就不应是纳税的花户,也不存在要官府把土地判回蒙古的问题,可能其中还有曲折。原件藏土左旗档案馆,全宗号80,目录号5,卷宗号2313。
[20] 察素齐村有水神社,道光年间,“今小的等九家不知油楞一家所卖与伊系何处水分,但小的等水神社自乾隆年间就有龙王、河神庙宇。到嘉庆十三年,众地户等拆旧建新,嗣因众地户浇地强弱不分,动起口角。是以道光二十四年,全化寺喇嘛并蒙古、民人三赦公同商明,按以水口流水之势,照社帐有地亩人名分开水分。从每年立夏前七日,按焚香分寸轮流使水浇地,不许紊乱成规。如此小的等村始得相安”。原件存土左旗档案馆,全宗号80,目录号5,卷宗号2203。
[21] 原件存土左旗档案馆,全宗号80,目录号5,卷号2213。
[22] 如,“时小的等与上下达赖两村蒙民甲会会同议定,依照旧年旧规,将乔秉义所退之地按亩应社,摊费之事自光绪四年归入上达赖村蒙古神社应社。至今毫无异说。迨至上年间,袁□海等所退之地亦照旧规,仍应蒙社,业已六七年矣。不意空出下达赖村甲会王楞达、李喇嘛等,欲将前已退交,归与上达赖村蒙古神社应社摊费户口地亩,硬霸与下达赖村民人神社摊费。因不遂意,控在萨厅案下”。原件存土左旗档案馆,全宗号80,目录号5,卷宗号2089。前引领催格海那段材料也说,“蒙民各别,各有各社,各当各差”。
[23] 与上述认识相关的研究如黄志繁:《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刘平:《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但最直接最全面的研究是唐晓涛的博士论文:《礼仪与社会秩序:从大藤峡“猺乱”到太平天国》,广州:中山大学,2007年;〔日〕菊池秀明:《广西移民社会与太平天国》,东京:风响社,1998年。
来源:《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
讲座:李零:商周酒器略说——以“觚”“觯”“爵”“角”为例
本文为北大“文研六周年”系列学术活动,“年度荣誉讲座”第四场的讲座纪要。讲座伊始,李零教授即指出,青铜器的分类有功能分类和类型分类两种取向。我要新鲜事2023-05-27 13:35:530000樊锦诗: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之一)
敦煌石窟泛指敦煌地区及其附近的石窟,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是中国中古时期的重要佛教文化遗存。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出土了5万余件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不论从数量还是从文化内涵来看,都可以说是20世纪我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现,从此,以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为发端,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学科——敦煌学。也正是由于藏经洞的发现引导人们重新认识和发现了敦煌石窟。0000#历史冷知识#大秦统一岭南,最南到了什么地方?徐闻考古为证
国庆说历史冷知识,要与中国有关。看标题您就是知道,这一定与广东某地有关,没错!祖国广袤大陆国土最南南方,有个半岛,徐闻半岛,隔琼州海峡与海南省相望,那里是现在徐闻县所在地;也是秦始皇发起的统一中国的战争中,秦人在现今祖国最南半岛留下遗存的地方(在邻国的发现就不说了)。花开两朵,先放下秦人的遗存;说说徐闻县名称的来历:我要新鲜事2023-05-25 16:11:390000文博系列丛书 | 将人类文明高光时刻摆上书架——“里程碑文库”背后的故事
我要新鲜事2023-05-06 17:40:44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