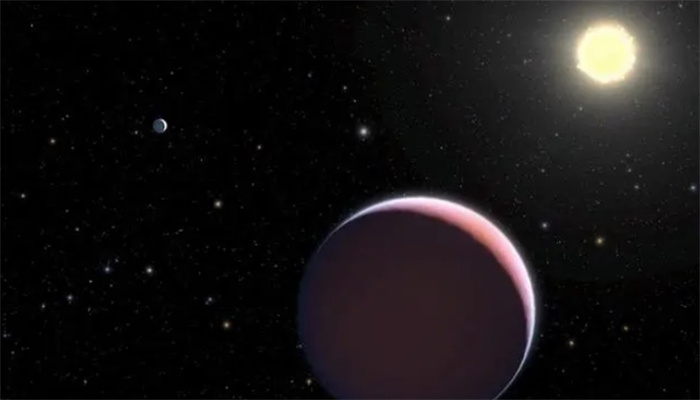周书灿:论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按:原文标题为《周书灿:论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重读<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因格式所限,以上标题略作调整。
内容提要:《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是傅斯年先生的史学代表作。傅氏书中高度重视史料发掘、鉴别与应用,语言学的辅助作用及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理论的借鉴运用,关注“直接研究材料”和问题之“新陈代谢”,逐渐建立起了颇为崭新、独到的学术思想体系,呈现出颇为鲜明的学术特色。傅氏对上古民族与历史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鲜明的独到之处,更具有重要的学术前瞻性与开拓性。傅氏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研究,又不时与其部分学术主张屡相矛盾,加上固有的时代局限,傅氏《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屡屡暴露出设定、假定先入为主,推论多于考证,缺乏科学的历史观念,概念含混,学理逻辑矛盾,史料鉴别、审查存在缺失,材料运用偶失恰当等缺陷与不足。在新的学术背景下,科学理性地审视傅氏古史研究,有助于中国史学的繁荣与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傅斯年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前瞻性 开拓性 缺陷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①是傅斯年先生生前未能完成的一部有关上古民族与历史的著作。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之一,《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于2002年8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首次出版。该书《出版说明》所言,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的出版,是一项“学术文化积累的基础工程”,“是向世界展示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个学术长廊”。《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出版前后,何兹全先生高度赞许《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所收录的五篇已发表的文章,“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创见,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创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②另有学者称傅氏以上大作“时时透露出乾嘉汉学的流风余韵”③,是“富有真知灼见的学术名篇”,“是享誉中外的奇文妙论,为学界推崇备至”。④总之,其学术经典的地位已逐步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肯定。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以往对《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的评论多停留在“新”、“奇”等宏观层面,然随着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的蓬勃发展与先秦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傅氏对中国上古民族与历史的某些论断所暴露出的若干局限与不足,亦日益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因此,在新的学术背景下,客观准确评判这部重要的学术经典,深入剔抉其精义要眇,科学理性地审视其暴露的若干局限与不足,对于中国先秦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繁荣,显得颇为必要。
一、《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的学术思想与特色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是傅斯年先生未能完成的一部著作,却是傅斯年先生的“史学代表作”。⑤2002年8月,是书由河北教育出版社首次出版。书中收录傅先生20世纪30年代陆续发表的《夷夏东西说》、《姜原》、《周东封与殷遗民》、《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论所谓五等爵》五篇有关上古民族与历史的学术大作。该书《附录》另收入傅先生《与顾颉刚论古史书》、《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战国子家叙论》、《性命古训辩证》、《史学方法导论》、《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旨趣》等不同时期的书信、书跋、专著、讲义等迄今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著。由于《附录》所录论著,与是书的主要内容,多不相涉,因此,本节仅以正文所录五篇大作为重点,辅以《附录》相关文字,对傅氏学术思想与特色,做一番系统的考察。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是一部独具鲜明特色的学术著作。通读傅氏大作,不难发现,是书主要具有以下颇为鲜明的特色:
第一,重视史料发掘、鉴别与应用。曾提出“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史学便是史料学”⑥的傅斯年先生,历来高度重视史料的发掘、整理与应用。傅氏将史料分作“直接的史料”和“间接的史料”两类:“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⑦傅氏强调,“直接的材料是比较最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这个都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⑧显然,在上古民族与历史研究中,傅氏对于间接材料也予以充分的关注和重视。《夷夏东西说》一文,傅氏为证明“商代发迹于东北渤海与古兖州是其建业之地”的“假定”⑨,高度重视“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相互参会”。⑩傅氏以《商颂》为论定以上“假定”之“最早最可信之史料”(11),持“后代神话与此说属于一源而分化者(12),“以证商代来自东北,固为不足……以证商代之来源与东北有密切关系,至少亦是文化的深接触与混合,乃是颇充足,很显然的。”(13)傅氏非常重视间接材料的旁证作用。他曾强调:“若旁涉中的证据不止一件,或者多了,也有很确切的事实发见。”(14)例如为证明“皋陶之皞,当即大皞之皞,曰皋陶者,皋为氏,陶为名,犹丹朱、商君,上字是邑号,下字是人名”(15)之论断,他征引《易林》、《路史·后纪》两条晚出的材料,以为“此说或有所本,亦可为此说之一旁证”。(16)又如,他“以《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及传记所载齐人宗教之迹为证”(17),得出结论:“齐之民族必是一个特异的民族”。(18)从某种意义上讲,傅氏高度重视间接材料的旁证作用,无疑使其所作结论建立在更为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从而不断增强学术研究的科学性。
傅氏同样高度重视相似材料的比证作用。诸如他为进一步解释“四岳之后,有文物之大国齐,又有戎者”(19)之现象,以女真为例,加以说明:“建州女真征服中夏之后,所谓满洲八旗者尽染华风,而在混同江上之女真部落,至今日仍保其渔猎生活,不与文化之数。但藉此可知姜本西戎,与周密迩,又为姻戚,惟并不是中国。”(20)他另举“南匈奴在魏晋时已大致如汉人,北匈奴却跑得不知去向。契丹窃据燕云,同于汉化,至今俄夷以契丹为华夏之名,其本土部落至元犹繁。女真灭辽毒宋,后来渡河南而自称中州,其东海的部落却一直保存到现在;虽后来建州又荼毒中夏,也还没有全带进来。蒙古在伊兰汗者同化于波斯,在钦察汗者同化于俄罗斯,在忽必烈汗国者同化于中国,在漠南北者依旧保持他的游牧生活”(21)等典型例证以说明:“姜之一部分在殷周之际为中国侯伯,而其又一部分到后汉一直是戎狄”(22)这一并不奇怪的情形。傅氏解释《诗经》大东、小东“大小之别,每分后先”(23),举证“罗马人名希腊本土曰哥里西,而名其西向之殖民地一大区域曰大哥里西(Magna Grecia)。名今法兰西西境曰不列颠,而名其渡海之大岛曰大不列颠(Magna Britannia)。”(24)通过相似材料的比证,不少繁难的历史问题,迎刃而解。
傅氏在高度关注史料的发掘与整理的同时,亦充分注意对纷繁复杂的古史材料的鉴别与辨析,在对其充分掌握的材料进行科学审查的基础上,对古史材料的价值有区别地看待。诸如傅氏考察夏迹,对于后起发生流传于匈奴、于越、汶山一带的禹的传说,并非不加分析地盲目信从,诸如他综合他认为更可靠的材料推论“禹为古之明神。”(25)同样,他以为,传说中的鲧“与夏后有如何之血统关系,颇不易断。”(26)因此,傅氏认为,“排比夏迹,对于关涉禹者应律除去,以后启以下为限,以免误以宗教之范围,作为国族之分布。”(27)尽管傅氏以上论断并非目前学术界的最后结论,但较之以往信古派学者,泥古不化,亦步亦趋,其对于启以前古史材料的鉴别、辨析,确为卓识。又如,傅氏将少皞诸姓国之地望,列为一表,亦曾言及:“但以见于《左传》、《史记》、《世本》佚文、左氏《杜注》者为限,《潜夫论》所举亦略采及,至于《姓纂》、《唐宰相世系表略》等书所列,材料既太后,又少有头绪,均不列入。”(28)显然,傅氏并非对以上材料,随便拿来就用,而是在进行严格的区别和审查之后,有选择地使用的。又如《吕刑》一书的著作时代和背景,学术界历来争议很大。傅氏指出,“《吕刑》一篇王曰辞中,无一语涉及周室之典,而神话故事,皆在南方,与《国语》所记颇合。是知《吕刑》之王,固吕王,王曰之语,固南方之遗训也。引《吕刑》者,墨子为先,儒家用之不见于《戴记》之先,《论语》、《孟子》绝不及之。此非中国之文献儒家之旧典无疑也。”(29)傅氏以上见解,目前已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由此可见,傅氏对于古史材料性质有着卓越的鉴别与辨析能力。
傅氏对于新旧史料之互相为用,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必于旧史料有工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然而但持新材料,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亦每每是枉然。从此可知抱残守缺,深固闭居,不知扩充史料者,固是不可救药之妄人;而一味平地造起,不知积薪之势,相因然后可以居上者,亦难免于狂狷者之徒劳也。”(30)显然,傅氏更加注意新、旧史料的有机结合,其和王国维先生“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31)的学术旨趣相比,更显出其独到的学术思想。诸如齐侯鎛钟虽为春秋中期之器,傅氏以为器铭所记传说“必古而有据”(32),他结合传世文献和钟铭记载,以证“成汤实际灭夏桀而居其土”。(33)傅氏善于通过新、旧材料比较,寻找出文献记载的破绽。如《论所谓五等爵》一文,傅氏举余永梁《金文地名表》,“以见杜说与金文相差”(34),以证文献所记“五等称谓之分配颇现淆乱”。(35)显然,傅氏正是通过对新、旧材料之互相为用,“扩充史料”,“促成史学之进步”。(36)
第二,重视语言学的辅助作用及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理论的借鉴运用。语言学在古代又被称为小学,曾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有的学者指出:“清、近代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研究不仅超过前人,而且已达到科学的高度。这是本时期古文献学达到空前水平的基本保证。”(37)“以声音文字为本”(38)是清代学者治小学的最主要方法。傅氏在高度重视史料的收集、鉴别与应用的同时,亦高度重视语言学在古史研究过程中的辅助作用。诸如他考察殷之地望,在高诱《吕氏春秋·慎大》注的基础上进一步讲道:“殷即郼,郼、韦、卫三字当一字之异体。今能寻卫、韦之所在,则殷土之原来地望可知。”(39)又云:“殷、兖(古作沇)二字,或者也不免是一词之变化,音韵上非不可能。此说如不错,则殷、衣、韦、郼、卫、沇、兖,尽由一源,只缘古今异时,成殊名耳。”(40)在此基础上,傅氏推知“成汤以前先公发祥自北而南之迹”。(41)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与商史研究的益趋深入,傅氏的以上推论由于逐渐得到考古学资料的印证而逐步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可。目前,不少考古学家赞同将先商文化探索的目标集中于豫北、冀南地区的下七垣文化并由之上溯。自上世纪80年代偃师商城发现以来,多数学者主张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始建和使用时期的商文化即早商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文化逐渐融合,最终以下七垣文化因素为主导,形成内涵丰富且统一、和谐,步入成熟形态的早商文化。”(42)由此可见,傅氏结合语言学材料推论“成汤以前先公发祥自北而南之迹”,方法颇为科学。又如,傅氏从语言学角度立论:“宋为商之转声,卫之名卫由于豕韦”(43),推论周初宋、卫“此两处人民之为殷遗”。(44)傅氏怀疑文献所记五等爵的真实性,对所谓“爵”名进行分析。其从音韵学角度举证:“公,兄,君,尹,昆,翁,官,哥,皆似一名之分化者”(45),其从金文、甲骨文“子”字字形、字义推断:“今作子者借字也。”(46)由于获得语言学材料的侧证,从而大大增强了以上推论的说服力。
傅氏对语言学材料的运用,一反以往学者滥用声训之弊,诸如他推测“济河流域中以薄或博命名者,尚有数处,其来源虽有不可知者,然以声类考之,皆可为亳之音转。”(47)他详细论及:“‘亳’、‘薄’二字,同在唐韵入声十九铎,傍各切。‘博’亦在十九铎,补各切。补为帮母之切字,傍为并母之切字,是‘毫’、‘薄’二字对‘博’之异仅在清浊。蒲姑之‘蒲’在平声,然其声类与‘毫’、‘薄’同,而蒲姑在《诗·毛传》、《左·杜注》中作薄姑,则‘蒲’当与‘薄’通。又十八铎之字在古有收喉之入声(—k),其韵质当为ak,而唇声字又皆有变成合口呼之可能,是则‘蒲姑’两字正当‘亳’之音转。亳字见于殷虚文字,当是本字,(殷墟卜辞类编)五卷十五叶)博、薄、薄姑等,为其音转,以声类韵部求之,乃极接近。”(48)尽管傅氏从声韵学角度对以上文字作了颇为准确的推断,但他仍实事求是地讲道,以上推论仍是“非未能证明之假设”(49),显然,傅氏仅仅将语言学材料作为古史研究的辅助手段,而并非直接证据。又如,傅氏由“燕字今经典皆作燕翼之燕,而金文则皆作郾”(50)推论周初燕国“则与今河南之郾城,有无关系,此可注意者。”(51)显然,傅氏在材料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并没有将以上推论作为“定论”。又如傅氏注意到《诗·?{风·鹑之奔奔》诗句中“君兄相易”现象,进一步讲道:“其义固已迫近,而考其音声,接近尤多。”接着他从音韵学角度进行细致推论:“广韵,君,上平二十文,举云切;兄,下平十二庚,许荣切。再以况贶诸字从兄声例之。况贶均在去声四十?一漾,许访切,似声韵皆与兄界然。然今北方多处读音,况贶诸字每读为溪纽或见纽,而哥字之音则见纽也。(唐韵,哥,古俄切。)诗以强兄为韵,则兄在古邶音中,必与强同其韵部。”(52)尽管以上论析,颇为严密,但傅氏仍以为“此在今日虽不过是一种假设”。(53)傅氏对语言学材料的运用,恰到好处,然而以其论证古史,则仍保持存疑态度。傅氏始终将语言学材料作为古史研究的辅助材料,其对语言学材料的运用,显然比同时期有的学者“穿穴证会”,“每每凭了孤证,便作结论。如根据了厉之与烈,界之与厉,皆以声转相通的原则,即断定介休的界山为烈山氏原住的地方”(54)的做法,显然要科学理性得多。
傅氏亦高度重视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理论的借鉴运用。傅氏曾强调:“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55)傅氏讲道:“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56),主张“将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57)在以上学术思想的指导下,傅氏在古史研究中,高度重视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理论的借鉴作用。诸如傅氏在《夷夏东西说》一文总结部分,用了大量篇幅论述黄河下流及淮济流域一带,和太行山及豫西群山以西的地域之间“根本的地形的差别”(58),并详细比较了东部平原区与西高地系自然环境的差异,进而论及“因地形的差别,形成不同的经济生活,不同的政治组织”(59),以证“古代中国之有东西二元,是很自然的现象。(60)又如傅氏认为,“以祝融为宗神宗祖之诸姓,虽在夏商起来之前占据中原,但毕竟是和南方有牵连的民族,曾在中原过其林隰生活(Jungle Life)。或者黄河流域林木之斩伐,天气之渐趋干燥,正是使他们折而南退的大原因,不仅是夏商的压迫而已。”(61)傅氏以上推测,为中国上古时期族群流徙探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参考价值。关于中国青铜器的早期制作,傅氏曾注意到:“青铜器制造之最早发端固无理由加之中土,然制作程度与数量能如殷墟所表见者,必在中国境内有长期之演进,然后大量铜锡矿石来源之线路得以开发,资料得以积聚,技术及本地色彩得以演进,此又非短期所能至也。”(62)以此和殷商文字为证,以证殷墟文化“乃集合若干文化系以成者”,“其前必有甚广甚久之背景”。(63)为进一步解释殷商以前,黄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带中,“不止一系之高级文化,必有若干世纪之历史,纵逾千年”(64)之论点于考古资料方面的疑难,傅氏以为:“或以为夏代器物今日无一事可指实者。然夏代都邑,今日固未遇见,亦未为有系统之搜求。即如殷商之前身蒙亳,本所亦曾求之于曹县、商丘间,所见皆茫茫冲积地,至今未得丝毫线索。然其必有,必为殷商直接承受者,则无可疑也。殷墟之发见,亦因其地势较高,未遭冲埋,既非大平原中之低地,亦非山原中之低谷,故易出现。”(65)傅氏从地形、地势角度,推论诸如蒙亳“尚未得丝毫线索”,是有道理的,其从反证角度为殷墟文化“乃集合若干文化系以成者”。殷商以前,黄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带中,“不止一系之高级文化,必有若干世纪之历史,纵逾千年”等论点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总之,傅氏对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理论的借鉴运用,大大开阔了古史研究的视野,拓展了研究领域,对于传统史学方法论的现代转型与跨文化视野下传统历史考据学向文化阐释学的变革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三,重视“直接研究材料”和问题之“新陈代谢”。傅氏指出:“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倒退。”(66)傅氏将以上研究分别区分为“科学的研究”与“书院学究式的研究”。(67)傅氏举例说明:“以《说文》为本体,为究竟,去作研究的文字学,是书院学究的作为。仅以《说文》为材料之一种,能充量的辨别着去用一切材料,如金文、甲骨文等,因而成就的文字学,乃是科学的研究。”(68)傅氏《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以上学术思想颇为明显。诸如《姜原》一文,傅氏结合《吕刑》及彝铭资料,以证“姜之原始不是诸夏”(69),进一步申论“姜本西戎,与周密迩,又为姻戚,惟并不是中国”(70)之论点。又如,傅氏举证“鬼方之鬼,在殷墟文字中或从人,或从女。……殷墟文字中出现羌字之从人,与未出现从女之姜字,在当时或未必有很大的分别”(71),批驳以往的学者往往将周代女子称姓的习俗解释为“姓由母系的缘故”,“实在是拿着小篆解字源之错误”(72),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论“女子称姓之习惯,在商代或者未必这样谨严”,以证“姜羌为一字”。(73)又如,傅氏在一一举证《春秋》、《孟子》、《周官》三书所记五等爵旧说,与《尚书》、《诗》“不合”(74),“以常情推之亦不可通”(75)的同时,更进一步结合青铜器铭文资料,以证以上文献中出现的所谓“爵”名,与旧的“五等爵说绝不合”。(76)不惟如此,傅氏还结合新旧材料,另从语言学角度对旧说所谓五等爵的公、侯、伯、子、男进行重新解释,以证“五等爵之本由后人拼凑而成,古无此整齐之制”。(77)综上可知,傅氏结合新材料对以上问题所作“科学的研究”,和以往“书院学究式的研究”的研究相比,无疑具有明显的创始性与突破性。
傅氏强调:“科学研究中的题目是事实之汇集,因事实之研究而更产生别个题目。所以有些从前世传来的题目经过若干时期,不是被解决了,乃使被解散了,因为新的事实证明了旧来问题不成问题,这样的问题不管他困了多少年的学者,一经为后来发见的事实所不许之后,自然失了他成为问题的地位。破坏了遗传的问题,解决了事实逼出来的问题,这学问自然进步。……一种学问中的题目能够新陈代谢,则所得结论可以层层堆积上去,即使年代久远,堆积众多,究竟不觉得累赘,还可以到处出来新路……如果永远盘桓于流传的问题,旧题不下世,新题不出生,则结果直是旋风舞而已……换言之,无后世的题目,或者是自缚的题目,遂至于这些学问不见奔驰的发展,只表黄昏的残缺。”(78)实际上,傅氏以上表达的主题思想,就是强调学术研究的创新与突破,反对抱残守缺,浅尝辄止和低水平重复。以上学术思想贯穿于《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全书,并构成该书颇具鲜明的又一特色。诸如其所论三代时期的民族构成关系,姜、羌关系及羌族流徙,周初封建及东方地区殷遗民的统治,大东、小东地望及周初鲁、齐、燕封地,文献中的所谓五等爵诸问题,皆为在新的学术背景下提出的崭新学术命题,并长期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如张光直先生评说:“《夷夏东西说》不是很长的一篇文章,但是有了这篇文章以后,历史学家看中国历史便有了一个与前不同的角度”(79),“他的东西系统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80)又如傅氏《姜原》一文发表之前,王国维先生仅仅简略言及:“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此周之通制也。上古无姓者,有之惟一姜嫄者,周之妣,而其名出于周人之口者也……虽不敢谓殷以前无女姓之制,然女子不以姓称,固事实也。”(81)以后,徐中舒先生亦曾从语言学角度论及羌与姜相关问题:“羌与姜字皆从羊,他们原是农业与牧业相结合的部族。羌从羊从儿,这是氏族制在文字中的反映,故《说文》以为羊种。姜从羊从女,这是家族制在文字中的反映。姓是中国家族制的产物,它首先是在羌族中完成的”。(82)在某种意义上而论,徐氏以上推论,尽管与傅氏的某些解释并不完全一致,但受到傅氏的影响,则是完全有可能的。傅氏《大东小东说》发表后,亦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诸如徐中舒先生考察殷、周之际史迹时讲道:“《史记·周本纪》及《鲁周公世家》谓武王克殷,即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其说至不足据。盖武庚未灭以前,殷人犹居朝歌,周人决不能越其地而有鲁。傅孟真《大东小东说》以为二南当在成周之南,今河南鲁山县及其近地,即鲁初封之邑。今河南郾城、召陵诸地,即燕召公初封之邑。以二南所咏之地证之,其说甚是。”(83)傅氏《论所谓五等爵》一文发表后不久,董作宾先生则直言其《五等爵在殷商》一文的著述缘起:“近傅孟真先生函询公、侯、伯、子、男五字在甲骨文中出现之次数,余乃嘱胡厚宣君一一辑录之,稍加理董,以成此文”。(84)董氏结合甲骨文资料,对卜辞中公、侯、伯、子、男五字逐一进行解析:“卜辞中所有之公字,尚无作‘五等爵’中公侯之‘公’解者”(85),“伯与侯,均为殷代封建之制……非如春秋时代侯伯名义,可相混淆”(86),“子在卜辞中最多见……一曰干支字,二曰地名字,三曰妇子字,四曰贞人字,五曰王子字,六曰封爵字”(87),“男字在卜辞凡三见……三辞之男字皆可作‘男’爵解”。(88)郭沫若先生则结合金文资料论及:“五等爵禄实周末儒者托古改制之所为,盖因旧有之名称而赋之以等级也”。(89)显然,董、郭二氏的研究是对傅氏提出问题的进一步深化。综上可知,傅氏以上研究,重视问题之“新陈代谢”,其善于提出全新的命题并进行科学的研究,从而使其古史研究建立在崭新的起点和崇高的水准之上,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与繁荣起到了积极的先导作用。
二、《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的若干质疑与批判
综前所论,在《民族与古代史》的撰述过程中,傅斯年逐渐建立起了颇为崭新、独到的学术思想体系,因而使该书呈现出颇为鲜明的学术特色。然而,通读《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则不难发现,傅氏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研究,又不时与其部分学术主张,屡相矛盾,加上固有的时代局限,傅氏《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屡屡暴露出某些缺陷与不足,部分学术观点日渐引起学术界的质疑与批判。兹略举数例,加以说明。
(一)设定、假定先入为主,推论多于考证。
傅氏历来主张:“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为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90)傅氏这一主张和近代以来部分历史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梁启超先生曾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91)又说,“时代愈远,则遗失史料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92)徐中舒先生亦有类似的表述:“史之良窳率以史料为准,史家不能无史料而为史,犹巧妇不能无米而为炊。”(93)总体而论,以上观点是有道理的。然《民族与古代史》一书,傅氏在史料不足征的情况下,屡屡先入为主地进行设定、假定,由于推论多于考证,部分学术论点,疑问重重。
《大东小东说》一文,傅氏结合周初形势,推论“乃成王初立,鲁、燕、齐诸国即可越殷商故域而建都于海表之营丘,近淮之曲阜,越在北狄之蓟丘,此理之不可能也。”(94)征诸相关西周初年的青铜器铭文可知,傅氏以上推论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在史料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傅氏推断:“此三国者,皆初封于成周东南,鲁之至曲阜,燕之至蓟丘,齐之至营丘,皆后来事也”(95),则在很大程度上与西周初年对南土经营的背景(96),并不相合,因而留下不少疑问。不惟如此,在我们今天看来,傅氏据以立论的“比较可信之事实”(97),仍显得十分薄弱。诸如傅氏讲道:“燕字今经典皆作燕翼之燕,而金文则皆作郾。……燕既本作郾,则与今河南之郾城,有无关系,此可注意者。……曰郾曰召,不为孤证,其为召公初封之燕无疑也。”(98)以上仅从地名偶类,就断言郾城为“召公初封之燕”,明显缺乏有足够说服力的文献和考古学证据。同样,傅氏仅据“成周东南既有以鲁为称之邑”(99)一条极其薄弱的孤证,即断言:“鲁之本在此地无疑也”(100),同样难以服人。国家博物馆2005年铭记载虢仲对柞伯所讲周初史事:“才(在)乃圣且(祖)周公又(有)共于周邦,用昏无及,广伐南或(国)。”柞伯鼎铭经过李学勤(101)、朱凤瀚(102)二位先生考释,已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此铭所记周公“广伐南国”之事,印证了周公南征传说的真实性。显然,柞伯鼎铭有关周公南征的记载,同样为傅说提出了更为直接的质疑。傅氏试图以晚出文献记载的周公奔楚传说作为“鲁在鲁山之一证”(103),则存在的问题,显然更多。甚至连赞同傅氏《大东小东说》以上论点的徐中舒先生,也仅仅言及“周公之奔楚,由地理方面言之,自为可能之事”(104),此说“无若何依据”。(105)徐氏为傅氏以鲁山为鲁之初封之地的论点补充了文献所记鲁山一带周公庙的传说,但实事求是地指出,“此诸说多以秦、汉以后之思想或政绩解释前代之史事,天子巡守及汤沐朝宿之邑,未必即西周所有”(106),由此可知,徐氏对傅氏的以上推测,并没有不加分析地一味采信。又如傅氏据“传记称齐太公为吕望”(107),推测“太公封邑本在吕也”(108),同样推断多于考证,臆测成分很大。综上所论,傅氏《大东小东说》一文,从先入为主的设定、假定立论,证据薄弱,推断多于考证,存在着难以自圆的种种疑问。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傅氏学术思想方面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二)缺乏科学的历史观念,概念含混,学理逻辑矛盾。
相对于旧史学家们,在新的学术氛围影响下,傅氏逐步建立起若干新的历史观念。诸如他借鉴西方人类学中的“混合”理论考察上古时期民族构成与民族关系,将中国上古民族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如他以为,“诸夏之部落本甚多,而有一族为诸夏之盟长,此族遂号夏后氏”(109),这一结论和目前考古学家所界定的“夏代在其王朝统辖地域内以夏族为主体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110)的夏文化概念,颇为吻合。又如其解释所谓“夷”之号,“实包含若干族类,其中是否为一族之各宗,或是不同之族,今已不可详考”(111),似乎也颇为科学谨慎。然其接着讲道:“各夷姓有一相同之处,即在东方,淮济下流一带”(112),则与先秦乃至秦汉时期的历史实际,并不相合。征诸相关先秦秦汉时期的文献,不难发现,先秦秦汉相当长的时期的人们并未形成颇为严格的以夷为“东方之人”的概念,文献和甲骨文、金文中不仅有东夷、“东尸”等称谓,还屡有“西夷”(113)、“南夷”(114)、“北夷”(115)等各种称谓。相反,东方各族,古代文献和青铜器铭文中也并非一概称之为“夷”。如《尚书·费誓》中即屡屡言及:“徂兹淮夷、徐戎并兴”,“我惟征徐戎”。征诸周代文献和青铜器铭文可知,徐戎是淮夷中的重要一支,《国语·齐语》说:“东南多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显然,东方淮夷的一支徐既可以称“夷”,亦可以称“戎”,并非绝对严格固定。傅氏以夷“即在东方,淮济下流一带”的观念,显然受到战国秦汉时期文献《礼记·王制》、《风俗通义》佚文《四夷》“东方曰夷”及东汉学者许慎《说文》“夷者,东方之人也”等观念影响,并不能准确反映史前及三代时期的民族构成与地理分布的形势。
随着考古学的蓬勃发展与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傅氏以东西地理角度区分三代民族构成的理论,日臻暴露出不少突出的问题。如20世纪80年代,杨向奎先生即曾对傅说提出怀疑:“本来东方西方是一个相对概念,不建立一个座标点的话,是没法分东分西的,傅的方法先建立商代起于中国东北部以至河南东部的座标,而夏在其西,于是有夷夏东西说”。杨先生在文中还列举大量证据,对傅先生的论点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我们不能说夏初的夷夏交争,是界划分明的斗争,他们是内部混战,夷夏杂处,已由对峙而趋于融合”。(116)李学勤先生进一步提出了“夏朝不是一个夷夏东西的问题,而是夷本身就在夏朝的范围之内”(117)的新说。近年来,有的学者指出,“夷夏东西说”是在特定的背景下从古史的角度提出的,对驳斥流行一时的文化西来说及促进考古发掘活动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它也导致了学者们对考古资料年代判断上的错误认识,以致在利用考古资料复原史前史以及三代文明史的过程中走了一些弯路。(118)总之,傅氏对史前及三代民族构成与民族关系的探讨过程中,尚未能建立起全新的科学历史观,部分概念含混,造成学理逻辑的混乱。
(三)史料鉴别、审查存在缺失,材料运用偶失恰当。
学术界历来强调,研究历史首先要对史料进行严格审查,为史学研究奠定坚实可靠的史料学基础。郭沫若先生强调:“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119),顾颉刚先生亦反复讲道:“对于史料毫不加以审查而即应用,则其所著虽下笔万言,而一究内容,全属凭虚御空,那就失掉了存在的资格”(120),“研究古史,自然应该先把古书的著作年代弄清楚,使这些古书得到史料上适当的价值。”(121)傅氏研究上古历史,颇为重视史料的鉴别与审查,在此基础上注意对古史材料的价值进行区分,然而通读《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亦发现傅氏对某些古代史料的鉴别与审查,亦存在若干缺失。
如傅氏反复强调《商颂》是研究商代历史之“最早最可信之材料”(122),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一论点,明显存在不少问题。目前,更多的学者认为,《商颂》并非殷商时期的作品,魏源曾列十三条证据,断定《商颂》是鲁襄公时正考父祭商先祖而称颂君德的(123),梁启超先生以为,魏氏之说,“足以成为定论”。(124)王国维先生则“疑亦宗周时宋人所作也”。(125)尽管《商颂》成书年代尚存在争议,但可以肯定的,其绝非殷商时期的作品,更非研究商代历史之“最早最可信之材料”。兹略举两例,加以说明。如《商颂·玄鸟》追述殷高宗时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而《汉书·地理志》则云:“初雒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显然,用《商颂》解释殷商时期的国土结构,疑点多多。此外,《商颂》中屡屡言及“天命玄鸟”,“天命多辟”,而“天”是周人最重要的宗教崇拜对象,显然,《商颂》不少文字带有周人观念的深刻烙记。又如傅氏“《周官》集于西汉末”(126)的观点也基本不为学术界所认可。在中国儒家经典中,《周官》历来是学术界争议最大的一部古书。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周官》是战国后期学者采择西周及春秋时期的官制与其他相关原始资料,参考战国时期的政治理想,综合融会,编纂成书。《周官》绝不可能是西汉末出现的著作,兹可举两条有力的证据。《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河间)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史记·封禅书》也记载:“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河间献王所处时代与汉景帝相当,《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大体与汉武帝相当,以上两则材料表明,汉始得《周官》的时代,至迟应在西汉景帝、武帝年间,其为流传已久的先秦古书无疑。(127)综上可知,傅氏对于古史材料的鉴别、审查,尚存在一些缺失,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相关结论的科学性和可信性。
三、傅斯年古史的评价问题
综前所论,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研究所取得卓越成就及其在古史研究中所暴露出的若干明显不足,直接牵涉到对傅氏史学的评价。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傅氏史学的评判,并不一致,乃至颇为悬殊。胡适先生在为《傅孟真先生集》所作的序中,屡屡赞誉:“孟真这部遗集里……有许多继往开来的大文章”(128),盛赞傅氏是“一位能继往开来的伟大学人。”(129)何兹全先生也高度评价:“就这一本未完成的书之已完成的几篇文章,已足以使傅斯年坐上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大师的宝座,享有大师荣誉。”(130)然值得注意的,胡氏为《傅孟真先生集》作序时对傅氏学术作出高度评价,一方面在于二者之间原有的师生关系,带有不少个人情感成分,再就是胡氏难免受序言体文风的影响,难免有更多的拔高溢美色彩。而何兹全先生则是傅氏高足,何氏为《民族与古代史》一书所作《前言》,同样也难免融入更多个人情感因素。
事实上,早在何氏去世之前,即有学者指出,傅斯年和顾颉刚“对于近代史学倡导之功甚伟;惟精力瘁于领导,本人述作不免相应较弱。”(131)另有学者以为,“史语所的突出成就……多多少少放大了傅斯年学术理念的作用”(132),“在追求‘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方面,傅斯年的实际做法与公开宣言之间也存在明显反差。”(133)以上评判,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亦并非毫无根据的一面之词。
笔者以为,以上学者对傅斯年史学的评价,均未免失之偏颇。结合前文对《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的分析,笔者以为,对傅斯年古史研究的评价,大体可以获得以下基本认识:傅斯年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重要代表之一,作为学术界公认的史料派大师,其古史研究具有更为鲜明的学术特色。诸如其高度重视重视史料发掘、鉴别与应用,重视语言学的辅助作用及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理论的借鉴运用,重视“直接研究材料”和问题之“新陈代谢”,其对上古民族与历史问题的研究,无论就方法和论点,不仅具有鲜明的独到之处,更具有重要的学术前瞻性与开拓性。诸如《姜原》、《论所谓五等爵》等文,提出了超越前人的卓越学术见解,为科学的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建立起崇高的学术水准和崭新的起点。傅氏的古史研究,也明显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和若干明显的不足,诸如存在设定、假定先入为主,推论多于考证,缺乏科学的历史观念,概念含混,学理逻辑矛盾,史料鉴别、审查存在缺失,材料运用偶失恰当等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古史研究的科学性与所作结论的可信性。诸如随着田野考古资料的日臻丰富、文化人类学的蓬勃发展与上古史研究的日臻深入,傅氏的“夷夏东西说”、“大东小东说”等论点,不断引起中外学术界的质疑乃至批判。在新的学术背景下,科学理性地审视傅氏古史研究,有助于中国史学的繁荣与进一步深化。
注释:
①傅先生在《夷夏东西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3年)一文的《前言》中说,“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以后,在《周东封与殷遗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1934年)一文《前言》中又说:“此我所著《古代中国与民族》一书中之一章也。”《东北史纲》第一卷(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中,傅先生言及:“商之起源当在今河北东北,暨于济水入海处,此说见吾所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二月后出版。”何兹全先生结合以上三条材料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和《古代中国和民族》是一书的异名,绝不会是两部书。书在未杀青定稿之前,对书名作些考虑是正常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使用在后。傅斯年对这可能是有考虑的,可能认为用《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好。”参见何兹全:《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②⑤(130)何兹全:《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③陈峰:《傅斯年、史语所与现代中国史学潮流的离合》,《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④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9页。
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2)(33)(34)(35)(36)(39)(40)(41)(43)(44)(45)(46)(47)(48)(49)(50)(51)(52)(53)(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90)(94)(95)(97)(98)(99)(100)(103)(107)(108)(109)(111)(112)(122)(126)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20~421、421、422、4、18、14、4、13、456、48、48、63、63、66、66~67、69、69、89、89、24、24、24、51、51、449~450、20、20、102、105、448、13、14、14、76、76、105、110、20、21、21、80、80、105、105、420、472、477、53~54、56、56、166、338、338、338、338~339、469、469、469、67、66~67、68、68、68、91~93、93、93、93、469~470、475、80、80、80、80、81、81~82、82、85、82、24、40、40、14、91页。
(31)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遗书》(五)《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
(37)孙钦善:《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836页。
(38)郝懿行:《晒书堂集》卷二《又与王伯申学使书》,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481册《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50页。
(42)(1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第24页。
(54)李峻之先生批判钱穆考证历史地名,证据薄弱,不少结论难免主观武断。转引自钱穆:《重答李竣之君对余周初地理考之驳难》,《古史地理论丛》,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88页。
(79)(80)韩复智主编,台北市中国上古秦汉学会,1995年发行,《傅斯年董作宾百岁纪念专刊》序。
(81)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册卷十《史林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73~474页。
(82)徐中舒:《巴蜀文化续论》,《四川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
(83)(93)(104)(105)(106)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二分,1936年。
(84)(85)(86)(87)(88)《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五等爵在殷商》,艺文印书馆1977年版,第885、886、892、892、901页。
(89)郭沫若:《金文丛考·金文所无考》,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3页。
(91)(9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1页。
(96)笔者曾结合文献和相关考古学资料考证,“文王、武王之世,周人的政治、军事势力仅局限于西土及中原一部分狭小区域。文王、武王之世,周人并未对南土地区进行政治、军事经营。文献所载文王、武王之世在南土进行政治、军事经营之事,多系讹传,而与西周初年的历史实际并不相符。”“武王之世今河南南阳、鲁山、郾城所处的南土地区,并非西周王朝政治地理的一部分,同样,武王也不可能将齐、鲁、燕三国封于成周东南的南土之境的外族土地上。”“齐、鲁、燕三国于武王之世并未得到封建。司马迁误记以上三国受封年代,傅先生又用徙封之说去加以调和,结果使三国封建的年代和地望问题,同周初的历史实际相去更远。”1996年6月,笔者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师从朱凤瀚教授读博士,曾以《由员卣铭文论及西周王朝对南土经营的年代》为题,投寄《考古与文物》编辑部,虽然很快接到用稿通知,但一直到1999年5月笔者博士毕业一年之久方刊于是刊第3期。当时是刊据手写稿打印出的拙作校样,笔者并没有看到。文章发表后,方发现在排版和印刷过程中,一篇并不算太长的文章,文字错误百出,诸如“郭沫若”打成“郭沫苦”,令人哭笑不得,一篇早年自认为用功最深的短文,竟然成了十足的废文。时隔13个春秋,向学术界告知,以示对学术研究负责。幸好拙作收入笔者的博士论文《西周王朝经营四土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206页)。学界参阅拙作,恳请以该书为准。
(101)李学勤:《从柞伯鼎铭谈世俘文例》,《江海学刊》2007年5期。
(102)朱凤瀚:《柞伯鼎与周公南征》,《文物》2006年第5期。
(113)《水经·清水注》引《纪年》:“周武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孟子·滕文公下》:“东面而征西夷怨。”
(114)《公羊传》僖公四年:“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若线。”
(115)《史记·天官书》:“故北夷之气如群畜穹闾。”
(116)杨向奎:《评傅孟真的夷夏东西说》,《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52页。
(117)李学勤:《夏商周与山东》,《烟台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118)王建华:《新夷夏东西说商榷》,《东方论坛》2004年第1期。
(119)《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120)(121)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24页。
(123)魏源:《诗古微》上编之六·通论三颂《商颂鲁韩发微》,《魏源全集》第一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325~330页。
(124)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10页。
(125)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127)在傅氏《论所谓五等爵》一文发表后不久,钱穆先生于《燕京学报》1932年第11期发表《周官著作时代考》一文。钱氏从祀典、刑法、田制以及《周官》里的封建、军制、外族、丧葬、音乐几方面进行了精细的考证,得出《周官》成于战国晚期,且当在汉代以前的结论。其结论由于建立在严密的逻辑与确凿的材料的基础上,因而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
(128)(129)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附录四,胡适:《傅孟真先生集序》,第480页。
(131)严耕望:《钱宾四先生与我》,台北“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序言第2页。
(132)(133)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280页。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4期
古墓出土青龙偃月刀 居然只有12斤(关羽武器)
我要新鲜事2023-05-14 16:16:390000林沄:对我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一些设想
2011年初,在考古学提升为一级学科的前夕,为了制订考古学的十年科研战略规划,全国十一所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考古专家云集吉林大学,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热烈讨论。后来又经多次会议的征求意见和多方咨询,形成了一个规划草案。这次《社会科学战线》要我参加笔谈,我想在这个集思广益的规划草案的基础上谈些看法。0000王子今:汉代“天马”追求与草原战争的交通动力
对“马”的空前重视,是汉代社会历史的重要现象。“苑马”经营与民间养马活动的兴起,都是值得重视的文化表现。“马政”因执政集团所主持,主要服务于战争,同时又涉及政治史、经济史、交通史和民族关系史。当然,马的繁育和利用,也是体现人与自然生态之关系的重要社会现象。我要新鲜事2023-05-29 03:55:460000重庆有一个秘密,在中国四大直辖市中最特别
重庆的风水秘密本文作者倪方六这篇文章“梧桐树下戏凤凰”头条号,来聊聊城市选址话题,从重庆的鹅岭公园说起。去重庆旅游,不到鹅岭会留下遗憾,它是重庆最早的私家园林。鹅岭前身为清末重庆商会首届会长富商李耀庭的别墅所在。这里树木参天,曲径通幽,山风徐来,环境宜人,故又称“宜园”。辛亥革命后改称“礼园”。我要新鲜事2023-05-27 01:04:180000中国哪里羊肉最好吃?古人说在陕西,甘肃宁夏可能不同意
隋唐人吃羊肉本文作者倪方六吃羊肉、喝羊肉汤,是人们冬日最佳选择。如果说狗肉是秦汉人喜欢的肉品,那羊肉就是隋唐人的菜。进入南北朝时期,中国人的食肉之风有所减弱,这一方面与连年战争,畜牧业生产受到破坏,肉食品供应紧张有关,更与这一时期佛教“戒杀生”、素食风尚兴起有关。到了隋唐时期,中国人吃肉之风再起。我要新鲜事2023-05-26 22:50:52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