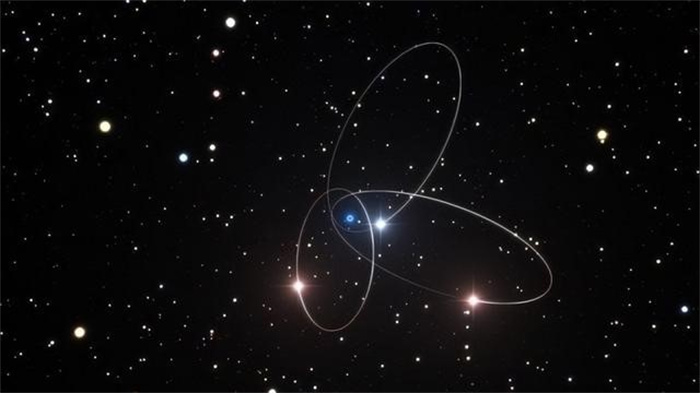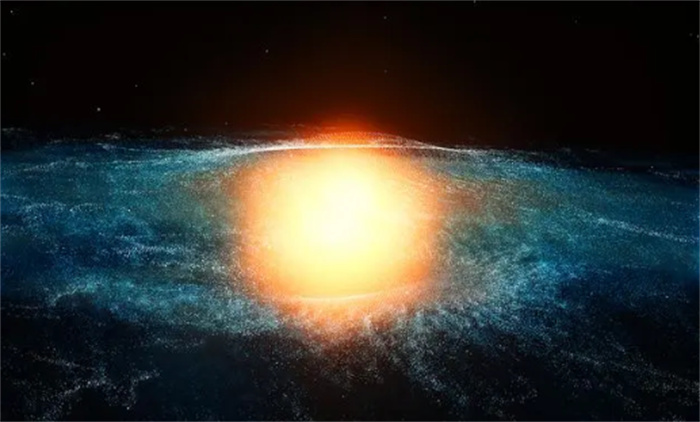张凯:平议汉学——蒙文通重构近代“今文学”系谱的尝试
【内容提要】清末民初,巴蜀“好今文家言者”主张以今文之“理论”统一古文之“事实”,并对以康有为公羊学为中心的今文学系谱提出质疑。蒙文通即认定晚清公羊学近乎伪今文学,而以礼制为本,按家法条例治《榖梁》才是成熟今文学。蒙文通重构近代今文学系谱,不仅丰富了对道咸学术流变的认识,更呈现传统学术近代转型的多元路径。近代今文学的疑古思潮为整理国故与古史辨运动变经学为古史学,以史代经提供思想资源;然蒙文通弘扬廖平《春秋》学,由廖平以今古讲两汉,进而以《春秋》论先秦,志在复古求解放,为其以史证经,以经御史埋下伏笔。
【关 键 词】蒙文通/今文学/榖梁
诚如有论者言,就清学而言,经今古文问题仅是汉宋分争的一个子题,或者说只是少数人的问题。有清一代,真正可以称作今文家者,寥寥无几,如果没有康有为言公羊改制,经今文学应当不会进入晚清思想界的主线。①戊戌维新以后,今文学复兴及其引发一系列学术文化思潮,牵涉到晚清民国政治、社会、思想、学术等诸多层面,经今文学因此一直是学界的焦点问题。相关研究亦多以康有为公羊改制为中心,侧重发掘其经世内涵,近代今文学的谱系也以康有为为核心展开。②
实际上,清季民初,兴“蜀学”成为川省学人的群体诉求,廖平著《今古学考》,拟纂《十八经注疏》,“以成蜀学”,与江浙学术立异,即意在扬弃乾嘉以降汉学传统,在复古求解放的道路上更进一步。此后,巴蜀“好今文家言者”主张晚近学术当以“东西”代“南北”,以今文之“理论”统一古文之“事实”,对以康有为公羊学为中心的近代今文学系谱提出质疑。1923年,蒙文通求学吴越,与江浙整理国故者深入论辩,返川后,即“议蜀学”,重建近代今文学系谱。考辨蒙文通此次江南之行的来龙去脉,梳理民初“蜀学”与江浙学术的分合,由此当可揭示民初中国学术渊源流变的多元脉络。
一、复古求解放
“复古为解放”的思路是清季民初学术界的某种通识,清代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本有研究对象越来越古的趋势存在。魏源曾说:“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③廖平治学以复古为宗,“由西汉以追先秦,更由先秦以追邹鲁。言新则无义不新,言旧则无义非旧。”④叶德辉则从学术争论的角度预测说:“学既有变,争亦无已,由实入虚易,由虚入实难,有汉学之攘宋,必有西汉之攘东汉。吾恐异日必更有以战国诸子之学攘西汉者矣。”⑤正如陈柱所言:“吾国学术莫盛于周末。自秦以后,忽焉就衰。盖周末为创作时期,其所著书,虽称古先王,而实皆各有己意,唯一吾国民族,雅尚经验,故以古言为重,非真复古。”“以古学为重”仅是表达“己意”的途径,而非真为复古,“有清一代之学术,言古学则可谓总前代之大成,论思想则可谓开今后之先河”。⑥不过,民初接续此“先河”者,言古学的旨趣却大不相同。
1920年代初,在总结二百年清学时,梁启超指出:“有清一代学术,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后半期为今文学。”进而认为清代学术乃“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⑦“复古为解放”遂成为认知“清代学术”的典范,这一解释模式可自然过渡到梁启超一直所宣扬的清代思潮“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时人将清代学术与文艺复兴相类比,顺理成章地为引入“科学”提供了历史依据与学理基础。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环节,胡适、顾颉刚倡导的“整理国故”和“古史辨”运动则在今文学的影响下,力图以严肃的学术运动来参与和支持反孔非儒的“新思潮”,其起点正是回归原典,在继承乾嘉汉学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今文学复兴虽是“以复古为解放”过程中的关键步骤,但在新文化派眼中“解放”的目标不再是复古代经典的大义,而是西来的“德先生”与“赛先生”。
几乎同时,僻处西南一隅,毕业于四川国学院的蒙文通在平议二十年来汉学之时,对近三百年学术也勾勒出近似“以复古为解放”的系谱:“近三百年来的学术,可以说全是复古运动,愈讲愈精,也愈复愈古,恰似拾级而登的样子。这三百年间的进步和结果,真是可惊。”⑧近二十年的主流自然是今古文两派,两派的领袖分别是康有为、章太炎,但此二人又仅为廖平《今古学考》的修正派,不曾出离廖平学说的范畴,而蒙文通则要脱离《今古学考》而独立。与梁启超、胡适等人“解放”的目标不同,蒙文通所谓的解放是“现在讲经,是不能再守着两汉今古文那样讲,是要追向先秦去讲”,力图在经学上“博极群书、剖析毫芒”,明泰州王学业已“阐发尽致”的“孟子之道”。怀揣此种抱负,恰逢而立之年的蒙文通1923年底出川到清代经学大本营吴越求学问道。
蒙文通求学吴越志在“期观同光以来经学之流变”,然而原为经学大本营的江南,经学正统业已衰落,佛学等异军正突起,1923年则是投入到整理国故的洪流之中。江浙学人一面收吸新潮,一面整理国学,弘扬传统文化。虽然各派学人对“整理国故”见解各异,但都坚信“整理国学之声,洋溢于耳,国学终有复兴之一日,不过整理方法,颇费斟酌耳”。对立志于“输入学理”的学人而言,章太炎、康有为、陈衍等老辈的学问只能代表过去,不足以开创未来,因而与现在的学术无关:“其著作之精粹,可供吾人之诵读,其治学之方法,不能为吾人之楷式。虽诸先生在今日尚有存者,而于民国十二年之国学无与。”⑨
江浙整理国故的风气,与蒙文通求学问道本意相差甚远,蒙文通发出“故老潜遁”,“讲贯奚由”的慨叹,就不足为奇了,“遂从宜黄欧阳大师问成唯识义以归”。不过,蒙文通仍密切关注江浙学人整理国故的动向,并主动与之辩难。
二、今文学方士化辨
顾颉刚在1919年曾指出:“今文学的影响在学术上是‘深探孔子的微言’,在政治上是‘提倡改制’,在宗教上是‘建立孔教’。”⑩民初学人常以方士化为由诟病今文学。宋孔显即称:“儒家和方士的混合,有很明显的两时期:自秦至汉为第一时期,北宋为第二时期,第一时期的方士,竟和儒家不能分别。”(11)吕思勉与梁启超争辩阴阳五行学说时,指出“先秦学术,恐无能遗阴阳五行者”,“今文家说,能脱之者十无二三”,所谓“古代之哲学又原于古代之宗教”,“其不能无迷谬之谈,固然。”(12)
1922年10月,东南大学正式成立“国学研究会”,陈中凡、顾实为国学研究会的骨干,主编《国学丛刊》。陈中凡学承刘师培,重礼制以守古文学,顾实早年留学日本,受章太炎等人的影响很大,二人言论常与今文学针锋相对。1922年11月24日,陈钟凡在国学研究会演讲《秦汉之间的儒术与儒教》时,即称:“至隋此风乃息,而近之今文家,犹复盛倡孔教之说其亦知非所以尊孔,实所以诬孔也。”(13)在《国学丛刊》创刊号上,陈中凡则直斥“秦汉今文经师之方士化”,在他看来,中国学术之衰在于秦汉之际儒学一变而为儒教,“秦汉之际,儒者类方士,其学亦绝似宗教”,“方士之说,倡于齐人,采于秦皇,而秦经师亦多通其说。”汉代今文学出于齐人,伏生、辕固又皆为秦博士,到了汉武帝大兴方术阴阳学,则“汉儒者莫不杂糅其说以言五经”,从而导致“殽乱经旨,致古义湮晦,非常可怪之论,触目皆是”。(14)
陈氏此论一出,孙德谦即致信提出商榷:“经学在汉初以前只有口说,若阴阳五行,乃是汉儒别传,非尽方术家言也”,“汉儒释经均言阴阳五行,可见古之儒者,通于天人之故,非仅如考据家溺于声音训诂,而其弊支离破碎也”。孙德谦意在调和汉宋,熄今古之争,“今日治经,既不必为宋学,亦不必为汉学,徒争此门户之见,所为至要者,发明圣经垂世,本是经世之学。”(15)对孙德谦“圣经垂世”的态度,陈中凡不以为然:“谓为经学之别传,不知舍古文纯朴鲜述玑祥外,其正传又安在哉?”(16)此后,孙、陈二人又往来数函,各持己见,孙德谦坚持,“方士与阴阳家不可并为一谈”,“采之阴阳家言即以有方士化则不可”,“于学术贵求折衷”;(17)陈中凡尊古立场更坚:“至明验确据在前,不敢苟从,一惟古人是尊,宗教家对其所崇奉之教主则然,学者对古人不敢如是也。引学说各有主张,未容强天下以从同,考古贵有左证,欲磨灭捏造,并所不可。”(18)
陈氏之说源自刘师培,早在1905年《谶纬论》一文中,刘师培指出:“方士之流,欲售其术,乃援饰遗经之语,别立谶纬之名,淆杂今文,号称齐学。大约齐学多信谶纬,鲁则不信谶纬。”(19)对刘师培而言,谶纬乃是源自方士之手的文献,它并不是原属儒家学术体系的材料。并据此批判齐学为儒术之异端,“经学之淆,至此始矣”。蒙文通虽称赞陈中凡所作《泰誓年月考》等文意在“寻西京古文学,犹左庵之道”,但同时认为“近代今文家说经,皆好取义于纬,方士与今文并为一谈久矣。左庵论著(《孔子不改制考》诸篇),亦复如是”。所谓“学不可苟同,苟同则道不明”,蒙文通对“陈、孙之争”,“窃有疑焉”,并以此为契机对在《经学导言》中“未能畅论”的“内学”问题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看法,在蒙文通看来:“秦汉间,有经师之传统;有方士之传统;以经生而习阴阳家言有之;以阴阳家而习经生家言亦有之;而经生之与方士,终不可混也。”(20)两汉经学重师说、讲家法,蒙文通认为经学是传授给所有弟子,但阴阳灾变说之所以成为内学,正是因为只是传给部分弟子。经术与五行之传授不同,传五经者不必即传五行,经学之道未尝与方士之学相混;今古文两家,有许多都兼通经学与内学,不能因贾徽、郑玄通阴阳星历则称古文方士化;况且也有诸多今文家反对阴阳灾异之说,故“不必内学即今文,今文即内学”。此说自不脱廖平四变之学的影子,廖平学经四变,综合大纲立四门,第一即是微言门:“微言秘密传心,不足为外人道,此派自西汉以后绝响”,微言虽多非常可骇之论,但“言经必先微言”。(21)
另外,古文学批评今文家好“附会内学者”,矛头所指便是“公羊家”,陈中凡即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何休等欲兴《公羊》,亦莫不傅会谶说,以动时主”。(22)但在蒙文通看来,世之奢言《公羊》齐学者,根本不究于灾变之故,“探五胜之原,尤不知期间各家异同分合之所在”(23)。实际上,内学立说的根本并非《公羊传》,因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皆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而不在《春秋公羊传》,汉代经学自有经学之传统,而灾变阴阳又自为其传统,西汉混阴阳之说与经学始于董仲舒、夏侯始昌。在此之前,阴阳之说未尝淆于《公羊》,故不能“以其传学者之故”,而将《公羊》学称为灾变阴阳之学,“它经更可知”。
基于上述区分,蒙文通认为近代今学与汉代师儒往往好言内学,“是其一短”。实际上,今学与内学是两家之学,纯正的今文学应该“屏除阴阳,而一断于礼”(24)。不久,陈中凡便回复蒙文通,认为前文乃从大体而言,不免概括之失,“前言秦汉今文经师方士化,亦谓西汉学者,大抵皆推说灾异,以傅会《六经》之旨。固未尝言两汉经说与谶纬不分,两汉经师尽为方士也”。但陈中凡也不认同蒙文通所强调的师说家法,“诸家灾异之说,固不必上承之师,下传其徒,吾人亦绝不能以其师若徒无灾异之言,遂并诸家灾异之说否认之”。所谓“以一端而概全体,以全体而概一端,皆为逻辑所不许”,暗示蒙文通所言仅为“一端”,陈氏则仍坚持秦汉今文之方士化为“全体”,进而认为“西汉学涉阴阳,东汉学涉谶纬,两者并属今文经师,无预古学”,“正赖有此古学以相质证,今学内学乃终不致于混淆”。(25)相反,蒙文通始终认为,近代学者“仅止看到今文学与阴阳五行合在一起”,就将“今文家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相比傅”,这是“抓不住今文学的实质的。”(26)
三、三体石经之争
正始时,古学立为学官,由此立三体石经,故三体石经成为古学之依据,石经残文可补正许氏《说文》学,然“三字石经之争久矣”。1923年洛阳附近所新出土魏三体石经,立即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王国维认为,“此事于经学、小学关系至大”。(27)章太炎视认为“逮三体石经之立,《书》、《春秋》古文一时发露,然后学有一尊,受经者无所匡惑”。(28)故对此事非常重视,致信于右任说:“以此知书本壁中,春秋本张苍所献,汉世秘府所藏,特于斯一见之。”(29)随即撰文考订三体石经。
章太炎首要是确定三体石经的作者,以此判定三体石经的今古归属。卫恒《四体书势》认为邯郸淳撰三体石经,范晔《后汉书》则将三体石经归于蔡邕。章太炎考证卫家与邯郸淳“有旧”,且卫恒逝世离正始才五十年,而范晔则“去则去正始二百年”,所以“传闻之与目睹虚实易辨不须博征”。蔡邕与邯郸淳二人著作权之争,实有关石经今古文性质之别。蔡邕曾立一字石经(熹平石经),《诗》举鲁,《尚书》举伏生,《春秋》举《公羊》,皆当时官学所用今文经传。若三体石经也为蔡邕所立,则当亦属今文无疑。章太炎指出后人以正始石经视为熹平石经遭董卓之乱后之补刻,“此未知文有古今,学有纯驳,有匡正之义无补缮之责也。一字石经立于汉,三字石经立于魏”,二者有今古文师法之不同。其后又以两汉《尚书》之源流与邯郸淳《尚书》学的师承论定:邯郸淳乃“采获旧本,得其真迹,手写其文,以示博士弟子,无足怪者,不得以杜林事为疑也”。(30)随后,章太炎陆续将新出石经与《说文》两相参证,以经古文为前提,由拓本推测三体石经之总体字数与每面行数。章氏此论一出,胡朴安即刻致信于右任,“觉太炎与先生书中所论,韫玉有不能苟同者”(31),二人遂多方辩难。胡朴安以史籍记载以及真伪《尚书》之流别,否认章太炎以古文学推论石经之碑文字数与每面行数,章太炎亦同意“经古文形成诡异,有不可尽合者”。其二,胡朴安虽认为三体石经为古文,但三体石经为邯郸淳所书之说,顾炎武、冯登府、万斯同诸说早已否定,章氏“仅据《魏略》未遍及各书也”。(32)其三,胡朴安认为“三体石经之出土,大足以增长汉简之价值,若谓于文字学极有发明”,“尚未见及”。不过石经之发现,“不仅以稀见重,可以确定三体石经之行数,有益于考古甚巨。”(33)章太炎则认为胡氏过在“轻于论古”。(34)
蒙文通对“三体石经之争”,特别是章、胡的分歧,早已“观其梗概”。适逢此时,蒙文通在南京亦得见三体石经拓本,故“奉其謏闻从诸贤后之兴”。(35)蒙文通引《世说新语注》与《晋书·赵至传》论证“石经古文,非邯郸淳书,乃嵇康书”,“正始立石,叔夜殆与于从事也”,且谓“三字石经显不限于《尚书》、《春秋》二种”,亦有《毛诗》。但蒙文通并未仅以作者来质疑三体石经,而是将重点落于“博士与石经之关系”,以此怀疑石经《尚书》。章、胡二人均认为“当时马郑之学方盛行,故石经所写定为古文”,且“当魏立三体石经时,伪古文尚书未曾参见”,所以“石经所书之尚书,非伪孔传”。(36)并据《晋书·卫恒传》认为三体石经所书必孔壁古文。(37)蒙文通则考曹魏博士制度证明壁中古文与伪孔《尚书》在魏晋十九博士之内,此事可以汉末曹魏经学之演变证明。据丁晏所考《孔传》之作者为王肃,而据《王肃传》与王朗《易传》可知“肃注各经,一时皆在校官”,既然王肃之学“以姻娅之故已尊于魏,则出于子雍之《尚书》孔传宜得立于学官,而古文勒石非鲁壁之真审矣”。若真如章太炎所言正始石经为《九共》、《汨作》等五十七篇,为壁中古文,“则旧书煌煌共见”,伪孔何以能立于学官,而且当时郑学之徒,“于《家语》、《孔传》固未尝一辨真伪,则《伪孔》之学,得刊于石经,立于博士,无不可也”。(38)如此一来,“博士、石经同据《伪孔》,则古文亦未必真壁中文字”,那么魏初邯郸淳所传是否为真古文字,自然值得怀疑。蒙文通赞成胡朴安所言“只足以增《汉简》之价值,不敢谓于文字有所发明”。不仅石经《尚书》如是,石经《春秋》、《毛诗》之文字亦如是,由此可断定石经所刻,“非鲁壁故物”。
不过,在《经学抉原》中,蒙文通对三体石经却有所肯定,谓邯郸淳所传当为鲁壁中书,而正始立石之时,“壁书尚存,犹得可据”,视石经为“六经之支与流裔”。(39)蒙文通之所以有此转变,关键或在王国维。在作《与胡朴安论三体石经书》时,“前闻王静庵、罗叔言于此皆有考论,惜都未睹其文”。王国维早在1916年即作《魏石经考》一文,后来又根据新出土的三体石经残石进行续考,在1923年作《魏正始石经残石考》,在1925年又作《魏石经续考》。王国维以翔实的史料说明“魏时学官所立《尚书》,既为马、王、郑三家,则石经亦当用三家之本”,诸书“虽未必为壁中原书,亦当自壁中本出矣”,“魏石经古文出于壁中本,或其三写四写之本,当无大误”,“固不能以杜撰议之矣。至其与壁中本相异者,亦可得而言”。(40)蒙文通在《古史甄微》以及后续之周秦民族研究中,充分利用了王国维的相关成果,那么就“三体石经”一事参看王国维上述诸文,自在情理之中。其实,蒙文通致信胡朴安,实是有激于章太炎考证三体石经时浓厚的古文学色彩,“殊令人迷眩”,故让胡朴安“乞一衡之”。(41)因而,在参见王国维的成果之后,对三体石经态度为之一变,当在情理之中,而且就学理而言,蒙文通并未将“鲁壁中书”视为经古文之根基,故三体石经之事不必坚守门户。
蒙文通与“整理国故者”之辩难,各据其理,莫衷一是,实源于论辩多方的立场不同。若以今古文分界,《国学丛刊》、《华国》二系学人倾向经古文学,批评今文学,立古文门户,胡朴安于1923年即指出“《国故》与《华国》及东南大学之《国学丛刊》,皆《国粹学报》之一脉,而以太炎学说所左右者。”(42)胡氏立志为旧学之整理,则与学界老辈划清界限,主张治国学当戒除“怪异之说”(以章太炎为例)、“附会之谈”(以刘古愚、廖平为例)与望文生义(以刘师培为例)之弊。(43)蒙文通首次出川,与陈中凡论今文学方士化,以及针对章太炎论三体石经,其严辨今古文的意图毋庸置疑,正是与诸多整理国故者有所交涉,蒙文通才会返川之后即“议蜀学”,重构近代今文学系谱。
四、真伪今文学之辨
虽说求学问道的初衷未能达成,但江南一行,亲眼目睹“浮丽之论张、百家之言兴”,孔学隐而不彰的世风,使蒙文通治学意向最终确立。在1923年平议近三百年学术时,蒙文通仍是将廖平一系置于顾炎武所开创的清学系谱之下,此时则改弦更张,自树旗帜。蒙文通“议蜀学”,以廖平本于礼制,明今古家法,由传以明经,依经以决传,与以小学考据为本的清代考据学“各张其帜以相抗”。在蒙文通看来,考据之学最适合研究《诗》、《尚书》,终究不过是“要在声韵”,“详在名物”,而兴蜀学则是要本于《礼经》、《春秋》“济道术之穷”,发儒学之“新义”。刘咸炘亦致信蒙文通,谈到“饾饤之习乃近日中国日本所同,其所以趋此者,以么小考证易于安立,少引驳难,乃来名之捷径”(44)。蒙文通扬誉廖平以礼制剖析汉代今、古家法,提倡廖氏之春秋学:“廖氏之学,其要在《礼经》,其精在《春秋》”,“谓廖氏之说礼,诚魏、晋以来未之有也,至其考论《春秋》,则秦汉而下,无其偶也”(45)。
蒙文通认为当下最紧要之事,则是清理门户:“《议蜀学》一篇则拟质之同志者,盖昔儒多宗古文,其究心今文者,往往徒骋浮辞,不精礼学,或至比附毖纬,为世诟病,不祛此惑,学何由明,此则通之所为发愤忼慨者也。”(46)正如陈中凡言“秦汉今文经师之方士化”其意在于驳斥所谓“今文运动”,“末世妄人,生千载之下,乃犹思掘其泥而扬其波,以‘今文运动’之名,号召于世,闻吾说其亦废然知乎反乎?”(47)是时,对今文学的批评多集中于此,连廖平亦认为:“王(闿运)怪属于旧,章(太炎)怪属于新,要皆有以自成其学而独立,与夫近来口谈名教,依草附木,毫无新旧之可言者,诚有凤凰鸡鹜之别矣!”(48)因此,蒙文通首先即要摒除今文学内部的浮辞,以礼制为本,祛除世人对今文学的诟病和疑惑。
清代今文学复兴,导源于常州。道咸以降,流变于全国。20世纪初,梁启超就致力于梳理晚清今文学流派:“其最近数十年来,崛起之学术,与惠、戴争席,而骎骎相胜者,曰西汉今文之学。首倡之者为武进庄方耕存与,著《春秋正辞》。”其后刘逢禄,“为《公羊释例》,实为治今文学者不祧之祖。”至道光年间,其学寝盛,“最著者曰仁和龚定庵自珍,曰邵阳魏默深源”。与龚、魏相先后而其学统有因缘者,“则有若阳湖李申耆兆洛、长洲宋于庭翔凤、仁和邵位西懿辰”,“自是群经今文说皆出”,而“湘潭王壬秋闿运,壬秋弟子井研廖季平平,集其大成”。康有为治《公羊》、治今文,“其渊源颇出自井研,不可诬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畴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则言义。惟牵于例,故还珠而买椟;惟究于义,故藏往而知来。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也”。(49)1920年代初撰《清代学术概论》时,梁启超大大渲染了《公羊学》与康有为在近代今文学谱系中的地位:“今文学之中心在《公羊》”,刘逢禄之《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则在清人著述中,“实最有价值之创作”。并认定康有为将两汉今古文之全案,重提覆勘,视为“今文学运动之中心”。(50)
对梁氏此说持异议者不乏其人,钱基博便批评“梁氏叙考证学极盛之反响,为公羊今文学”,乃“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之论”,至于公羊今文学,“梁氏自以为学所自出,着意叙述,不知公羊今文学之张设门户,当以江都凌曙晓楼筦其枢。”钱氏推凌氏为别子之祖,“以礼言公羊,著有《公羊礼疏》十一卷,《公羊礼说》一卷,开湘学王闿运、蜀学廖平之途径。又以《春秋繁露》明何休,为《繁露注》十七卷,以开康有为《春秋董氏学》之先河”。(51)
不过,晚近学人大多接受了梁启超的核心观念,所谓言晚清学术者,“多以今文学派为主流,其说始自梁启超之《清代学术概论》。”(52)学界以康有为公羊改制与刘歆造伪为主线论近代今文学,晚近今文学的毁誉褒贬皆系于此,蒙文通与陈中凡“今文学方士化”之辩即是明证。邓实曾批评“今文学者,学术之末流,而今文学盛行之世,亦世运之末流”。(53)顾实进一步指摘“康有为更拾廖平之唾余,倡为一切古文,皆刘歆伪造”,“康氏何必以己之所能责人以必然,康氏又倡为六经本无须文字,一切惟口说可凭。其弟子梁启超,至今稍变师说,而又主张今文排斥古文。总之,康梁之今文云云。不过借为弋取名利之具也。”(54)胡朴安则将今文学兴起视作清代汉学之衰落,廖平“著书颇多,时有怪诞之说”,康有为乃“窃廖氏之论,好为放言,不足道矣。”(55)章太炎1922年在国学演讲中即宣称:“今文学家的后起,王闿运、廖平、康有为辈一无足取,今文家因此大衰。”(56)
基于此,蒙文通在1920-1930年代屡次梳理近代今文学之谱系。1920年代末,蒙文通在《古史甄微·后序》称,“两汉言学,严守师法,各有义类统宗,于同道则交午旁通,于异家则不相杂越,笃信谨守,说不厌详。而晚近言学者则异是。”宋翔凤、魏源、龚自珍、康有为“肆为险怪之辩,不探师法之原,徒讥讪康成,诋诟子骏,即以是为今文”,“谓之能讪郑学则可,谓之今文学则不可”;惠士奇、金锷、陈奂、邹汉勋“陈说礼数,亦何尝不征之先秦、以易后郑,途径岂出龚、魏下。彼固不自命为今文,此则张毖纬以自表”,“张惠言、陈寿祺之述论,则庶近之也。”所谓“前代之今文学惟一,而近代之今文学有二,鱼目混珠,已非一日。”(57)《古史甄微·后序》在1933年被改作成《古史甄微·自序》,在“伪今文学”的行列中增加了刘逢禄和崔适。
1932年,蒙文通作《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仍持“前代之今文学惟一,而近代之今文学有二”之见,更系统地论述了清代今文学的传承。蒙文通曾褒奖孔广森、张惠言之流专门名家者,于六经传记能“倡家法,明条例,钩深抉微,实能阐二千年来不传之坠绪”,此乃有清三百年“复古求解放”过程中的上乘之作。但若以经今文学而言,张惠言、刘逢禄之流皆是未成熟之今文学,前者懂得依据家法条例,明一经之意,但“一经之义明,而各经相互间之关系尚未窥其全,是则所知者各家一隅之今文说,尚无综合各家以成整个之今文学派”,此乃“有见一隅而不窥全体之今文学”;后者虽能从整体上联系各经与古文学划清界限,但“徒以立学官与否为断,是则知表而仍不知其里”,此乃“有知其大概而不得其重心之今文学”。在这两派之外便是“本师”廖平“综合群言而建其枢极”,此乃“成熟之今文学”,“廖师推本清代经术,尝称二陈著论,渐别今古。廖师之今文学固出自王湘绮之门,然实接近两陈一派之今文学”。(58)廖平曾言:“国朝经学,顾、阎杂事汉宋,惠戴专申训诂,二陈(左海、卓人)渐及今古,由粗而精,其势然也。鄙人继二陈而述两汉学派,撰《今古学考》”。(59)蒙文通也认为陈寿祺、乔枞父子的《五经异义疏证》专门区分今古二学家法,陈立的《白虎通义疏证》则致力疏通汉代今文经说,“义例谨严”,实为依家法条例治汉学的代表作,只是因为“不以诡词异论高自标诩”,才为人所忽视,不附于今文学之列。(60)在蒙文通的今文学系谱里是将以廖氏上接二陈,而排斥王闿运,正是因为他认定善说礼制、家法条例之学才是正宗的今文学。
被蒙文通誉为齐学巨擘的邵瑞彭亦认为公羊学言今文与以家法条例治今文经二派有别,“庄、刘诸子,好言公羊春秋,则为今文之学,由是学者,始言门户。”陈寿祺、乔枞,陈硕甫、陈立,“接踵而作,大氐以寻绎师法,辩章条贯为主”。二派“趣舍不尽同,要之各能自名其家。咸同以降,风气益变矣。”龚自珍、魏源传庄、刘之学,皮锡瑞与廖平则谨守四陈之法,“以董理旧义,区分家法为己任”。(61)蒙文通则更进一步,认为廖平集“成熟今文学”之大成,“至廖师而后今文之说乃大明,道以渐推而渐备”。皮锡瑞则是近代经师中唯一能“远绍二陈,近取廖师以治今文者”。“伪今文学”一派,蒙文通则点出了龚自珍、魏源二人:“他若魏源、龚自珍之流,亦以今文之学自诩,然诗书古微之作,固不必求之师说,究其家法,汉宋杂陈,又出以新奇臆说,徒以攻郑为事,究不知郑氏之学已今古并取,异郑不必即为今文……固龚、魏之学别为一派,别为伪今文学,去道已远。”(62)
蒙文通所谓“汉代之今文学惟一,今世之今文学有二”,即认为晚清今文学分为成熟今文学与伪今文学。成熟今文学善说礼制、通晓家法条例;伪今文学不懂师说,不明家法,汉宋杂陈,又出以新奇臆说,特别是伪今文学将“今文之义悉在《公羊》”,“言无检束”,“书无汉宋”。简言之,“伪今文学”者治今文学以公羊为中心,刘逢禄、宋翔凤重公羊之微言大义,龚自珍、魏源则进而“阐发公羊三世、三统之义,论及时政,以为致用之方”。到了康有为则以公羊学倡言变法改制之说。刘逢禄、宋翔凤尚且能立今文学之门户,龚自珍和魏源则不仅重微言大义,“由公羊而推至群经”,其所谓经术,实政论也,此风气一开,使得晚清今文学流于政论一派。(63)齐思和即认定“晚清今文运动,本为一政治运动。”(64)蒙文通早年一直认定此脉络为伪今文学。李源澄也称,康有为“以改制为利禄之阶”,廖平则不谈政治;“近世公羊学者,刘宋不善师学,其失也愚,犹未至于叛道”,康有为“所谓大义微言,直董何污垢秽浊之物”;“世方有懵懵然以今古学家自表异者,更有不治经术而斤斤于今古之争以为名高者”,此乃“井研之旨不明,而流毒至是。”(65)
这里,自然会遇到一个绕不过的问题,廖平以《公羊》学而显于世,学界褒贬廖平学术亦多系于此。有学人称,“廖平之思想自成一家,不在康有为下。”(66)张鹏一则认为清季为今文学者,凡三人,皮锡瑞、康有为、廖平,廖平之《公羊学》尤当表彰,“六译诸作,以《解诂三十论》、《春秋图表》,《公羊补正》,《今古学考》为上乘,全得力于今学。”(67)钟泰则批评“定庵后,习《公羊》之学者,有蜀人廖平,然支离怪诞,有识之儒所不道。”(68)若治公羊学者为伪今文学,何以廖平反成为成熟今文学之集大成者?
以今文学而言,传《春秋》者,惟《公羊》、《榖梁》二家。如俞樾所言:“本朝经学昌明,超越前代,而治《春秋》者喜言《公羊》,谓孔子立素王之制,托王于鲁,变文从质,新周故宋,陈义甚高,立说甚辨……数十年来学术之大变即伏于此”。然则《公羊》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榖梁》则“体例甚精而义理甚正,无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是故“《公羊》有弊而《榖梁》无弊”,而“方今学术之弊皆误于公羊者,积而成之,欲救其弊,非治《榖梁》不可”。(69)《榖梁》“文省而理密”(70),如孔子故宋之说,《公羊》无明文,《榖梁》有之。以《榖梁》言尊周亲鲁故宋之说可谓独得大义,可将何休之公羊家所谓“非常异义”一扫而空。(71)廖平早年治学,“专求大义”,曾集中研究《榖梁》学,随后所著《今古学考》中,以礼制平分今古,参照何休公羊学以《榖梁》与《王制》言今文学。蒙文通以此对廖氏之学予以重新解释,首先申明廖平治学虽出自王湘绮之门,然实接近二陈一派,廖平学术之根荄在于以礼制言《榖梁》。他仅是以余力说《公羊》,因为举世治《公羊》学者皆未能领会《公羊》之义,廖平便以《公羊》名于世。廖平以治《榖梁》而兼治《公羊》,是以鲁学而兼治齐学,《公羊》学并非其学术根本。在蒙文通看来廖平并非是齐学大师,而是鲁学巨擘,所以在其它学者多将廖平归于讲公羊学一派时,蒙文通则认为廖平以礼制讲榖梁学,乃成熟今文学(即经生派)的集大成者。
可见,在蒙文通看来,“近代今文有二”不仅是因为有治汉学方法的区别,更因为有治《公羊》与治《榖梁》之别,晚清公羊学近乎伪今文学,所谓“清世言今学者皆主于《公羊》,遂以支庶而继大统,若言学脉,则固不如此”(72)。李源澄也认为“近世治公羊者,往往失之附会,遂为世诟病,或者竟谓无大谊微言”,故主张“治《春秋》者,如能先以《榖梁》立其本,再求之于《公羊》,于董何之说,分别去取,亦可以弗叛矣。”(73)蒙文通认为只有以礼制为本,按家法条例治《榖梁》才是真今文学,而论定《榖梁》为今文正宗的途径,即证明《榖梁》符合孔门原意,为孔子之嫡传。蒙文通遂“作《经学抉原》,深信齐鲁学外,而古文为三晋之学,则经术亦以地域而分”(74),以地域解释今古文经学的形成及其差异,今文学是糅合鲁学与齐学而成,鲁学最纯,是儒学正宗,齐学驳杂,出入诸子,古文学则是孔氏之学传于三晋、杂以旧法世传之史者。
不过,刘咸炘、钱穆等学友对蒙文通重构的今文学系谱均持有异议。刘咸炘认为“今文学之极,若廖季平”,其说“太过”,且其今文说多“弃旧说”而从康有为。廖氏论述“古书、孔子、孔经、刘歆、世间事理、为学方法”语多“滑稽”,欲“尊经于古史之上”,“反使经等于诸子”。(75)钱穆虽称康有为“言《公羊》改制,终不脱廖季平牢笼”,但钱氏梳理近三百年学术流变,依旧附廖平学说于康有为,批评“学人之以戏论自炫为实见,未有如季平之尤也。”(76)钱穆以此批评晚清今文学家走的是“一条夹缝中之死路,既非乾嘉学派所理想,亦非浙东史学派之意见。考据义理,两俱无当。心性身世,内外落空。既不能说是实事求是,亦不能说是经世致用。清儒到道咸以下,学术走入歧道,早无前程”。(77)蒙文通恰恰认为“新起之学”“未得正途”是指今文学流入公羊改制一派。那么,救弊的关键在重新阐释今文学,蒙氏对今文学系谱的重构为其以史证经,以经御史埋下伏笔。
五、经学与史学
民国以降,学人勾勒近代经今文学系谱以康有为为轴心展开,渊源有自。贺麟曾言:“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体’与‘用’的关系。学术是体,政治是用。学术不能够推动政治,学术就无用,政治不能够植基于学术,政治就无体。”(78)胡朴安亦称:“政治与学术相表里,政治表也,学术里也。自来政治之良否,无不由于学术。”而清末民初政局之转变,与今文学之兴起,实有莫大之关系。“道咸以来,西汉之今文学派代古文学派而兴,方耕、申受开其先,定庵、默深继之”,然“仅影响于思想而已,未能影响于政治”;直至廖平“今文之学独深,本《礼运》而为‘三世’之说,本《论语》而为‘先进’‘后进’之说,其说多奇而可喜。南海康氏承之,更张大其词,以召学者,号为维新,公车上书,为今文学派影响于政治之始,慷慨之言论,风靡于一时”,然“今文学有发扬宏肆之才,而无刚毅木讷之度,所以能促清廷之新,而不能绵清廷之祚。”(79)康有为以公羊学言改制,通经致用,经今文学由此影响了清末民初政治、学术的走向,廖平学术成为康有为公羊变法学说的注脚。
皮锡瑞梳理道咸学风时称,“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期初,一变而至于道。学者不特知汉宋之别,且皆知今古之分”,“西汉今文近始发明,犹有待于后人之推阐者,有志之士,其更加之意乎!”(80)康门弟子自是不断宣扬,康有为集今文学大成,为今文学运动之中心。(81)在学术与政治的纠葛之中,对近代今古文学的探讨集中于公羊改制;在经史递嬗的洪流中,今文学之重心被归结于刘歆造伪;相反,自廖平《今古学考》所开启的讨论两汉今古学之争的经义、学理倾向却寥落无闻。(82)
其实,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之初,廖平即致信康有为,称:“经学有经学之根柢门径,史学亦然。今观《伪经考》,外貌虽极炳烺,足以耸一时之耳目,而内则无底蕴,不出史学、目录二派之窠臼”,“纵观全书,其于目录之学,尚有心得;然未能深明大义,乃敢排斥旧说,诋毁先儒,实经学之真贼也。其以新学名篇者,不过即所谓今古文者而略为变通之。”(83)吕思勉也注意到了廖平、康有为的分别,康长素“昌言孔子改制托古”,“廖氏发明今古文之别,在于其所说之制度”,乃“经学上之两大发明”。“有康氏之说,而后古胜于今之观念全破,考究古事,乃一无障碍。有廖氏之说,而后今古文之分野,得以判然分明。”(84)康有为破除“后古胜于今之观念”,为进化的历史观开道,古史辨运动即是有选择的扬弃了康氏学说。近代今文学的疑古思潮为整理国故与古史辨运动变经学为古史学,以史代经提供思想资源。顾颉刚曾言:“清之经学渐走向科学化的途径,脱离家派之纠缠,则经学遂成古史学,而经学之结束期至矣”,“故至我辈之后,经学自变而为史学。”(85)廖平分野今古文,旨在“复古求解放”,寻孔孟大义。蒙文通重构近代今文学系谱,表彰廖氏《春秋》学,志在复古求解放,由廖平以今古讲两汉,进而以《春秋》论先秦。此时,蒙文通著《古史甄微》便意图重建上古国史,澄清经史关系,以史证经,申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1930年代,蒙文通由经今文学入史,以经御史,以《春秋》之义区分“撰述”与“记注”,旨在弘扬儒学义理性立场的史学。国难之际,蒙文通提倡“秦汉新儒学”,称“惟今文之学有其中心,至井研之学出,乃有论定。不知今文之中心者,不足以知周秦学脉之相毕注于此。知其中心而不求之周秦,亦不足以见今文之恢宏。”(86)
王国维曾言“道咸以后之学新”,“龚璱人、魏默深之俦”为其代表,道咸“新学”极大影响到后人对清代学术的认知,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因此有学人主张“写出更具有包容性的清代学术史论著”。(87)此诚为真知灼见。其实,在道咸“新学”之内,学人对清代学术脉络的认知即有异议,今文学内部的分歧丝毫不逊于经今古文之争。以康有为或者廖平为核心构建的两条近代今文学系谱,实开启了传统学术近代转型的两种路径。廖平弟子对近代今文学系谱的重构,不仅丰富了对道咸学术流变的认识,更呈现传统学术近代转型的多元路径。
*本文初稿承桑兵教授审阅,提出宝贵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注释:
①桑兵:《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39页。
②陈其泰以进化论为视角勾勒出清代公羊学“有序的合乎逻辑的展开”系谱,见《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蔡长林则以考证与义理分别近代今文学与公羊学,强调二者的差异性,却割裂学者自身的学术脉络与本意。见《清代今文学派发展的两条路向》,载于《经学研究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③魏源:《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第152页。
④廖平:《与康长素书》,《中国学报》第8期,1913年6月。
⑤叶德辉:《与戴宣翘书》,苏舆编:《翼教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74页。清季“古学复兴”问题可参见罗志田:《中国文艺复兴之梦:从清季的古学复兴到民国的新潮》,《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年。
⑥陈柱:《清儒学术讨论集序》,《清儒学术讨论集》,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1-2页。
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6页。
⑧蒙文通:《经学导言》,《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第10页。
⑨胡朴安:《民国十二年国学之趋势》,《民国日报·国学周刊》国庆日增刊,1923年10月10日,第1版。
⑩顾颉刚:《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中国哲学》第11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7页。
(11)宋孔显:《由道士而道学》,《浙江一中周刊》第1期,1923年10月1日。
(12)吕思勉:《辩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东方杂志》第20卷第20号,1923年10月。
(13)陈中凡:《秦汉间中国之儒术与儒教》,《国学研究会演讲录》第1集,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81页。
(14)陈中凡:《秦汉今文经师之方士化》,《国学丛刊》第1卷第1期,1923年3月。
(15)孙德谦:《孙益庵论学三书》,《国学丛刊》第1卷第3期,1923年9月。
(16)陈中凡:《陈斠玄答孙益庵书》,《国学丛刊》第1卷第3期,1923年9月。
(17)孙德谦:《孙益庵来书》,《国学丛刊》,第1卷第4期,1923年12月。
(18)陈中凡:《陈斠玄复孙益庵书》,《国学丛刊》,第1卷第4期,1923年12月。
(19)刘师培:《左傗外集·谶纬论》,《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371页。
(20)蒙文通:《蒙文通先生与陈斠玄先生论学书》,《陈中凡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04页。
(21)廖平:《尊孔论》,《四益馆杂著》,《六译馆丛书》,四川存古书局,1921年。
(22)陈中凡:《秦汉今文经师之方士化》,《国学丛刊》第1卷第1期,1923年3月。
(23)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经史抉原》,第107页。
(24)蒙文通:《蒙文通先生与陈斠玄先生论学书》,《陈中凡论文集》,第106页。
(25)陈中凡:《答蒙文通先生论学书》,《国学丛刊》第2卷第2期,1924年6月。
(26)蒙文通:《治学杂语》,《蒙文通学记》(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4页。
(27)王国维:《与神田喜一郎书》,《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348页。
(28)章太炎:《太炎文录续编·汉学论(下)》,《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页。
(29)章太炎:《与于右任论三体石经书》,上海《民国日报·国学周刊》第5期,1923年6月6日,第1版。
(30)章太炎:《新出三体石经考》,《华国月刊》第1卷第1期,1923年9月。
(31)胡朴安:《与于右任论三体石经书》,上海《民国日报·国学周刊》第15期,1923年8月15日,第1版。
(32)章太炎:《与于右任论三体石经书》,《华国月刊》第1卷第4期,1923年12月。
(33)胡朴安:《三体石经跋尾》,上海《民国日报·国学周刊》第33期,1923年12月19日,第4版。
(34)章太炎:《与于右任论三体石经书》,《华国月刊》第1卷第4期,1923年12月。
(35)蒙文通:《与胡朴安书》,《国学汇编》第2集,上海:国学研究社,1924年9月。
(36)胡朴安:《三体石经跋尾》,上海《民国日报·国学周刊》第33期,1923年12月19日,第4版。
(37)胡朴安:《与章太炎论三体石经书》,上海《民国日报·国学周刊》第29期,1923年11月21日,第1版。
(38)蒙文通:《与胡朴安书》,《国学汇编》第2集,国学研究社,1924年9月。
(39)蒙文通:《经学抉原》,《经史抉原》,第100页。
(40)王国维:《魏石经考三》,《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99-601页。
(41)蒙文通:《与胡朴安书》,《国学汇编》第2集,国学研究社,1924年9月。
(42)胡朴安:《民国十二年国学之趋势》,上海《民国日报·国学周刊》国庆日增刊,1923年10月10日,第1版。
(43)胡朴安:《论研究国学当戒除之二弊》,上海《民国日报·国学周刊》第3期,1923年5月23日,第1版。
(44)刘咸炘:《推十文集·复蒙文通书》,《推十书》,成都古籍书店影印,1996年,第2209页。
(45)蒙文通:《议蜀学》,《经史抉原》,第101-103页。
(46)蒙文通:《在昔》,《甲寅周刊》第1卷第21期,1925年12月。
(47)陈中凡:《秦汉今文经师之方士化》,《国学丛刊》第1卷第1期,1923年3月。
(48)吴虞:《爱智庐随笔》,《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4页。
(49)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第58号,1904年12月。
(5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61-63页。
(51)钱基博:《后东塾读书记》,《青鹤》第1卷第5期,1933年1月。
(52)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燕京学报》第39期,1950年。
(53)邓实:《国学今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4期。
(54)顾实:《常州文学之回顾》,《国学汇编》第1集,国学研究社,1924年9月。
(55)胡朴安:《历代研究群经者之派别》,《国学汇编》第3集,国学研究社,1924年9月。
(56)章太炎演讲,曹聚仁编述:《国学概论》,中国文化服务社,1943年,第38页。
(57)蒙文通:《古史甄微·后序》,《史学杂志》第2卷第2期,1930年5月。
(58)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经史抉原》,第105页。
(59)廖平:《论学三书·与宋芸子论学书》,《四益馆杂著》,成都:四川存古书局,1921年。
(60)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传》,《新四川月刊》第1卷第1期,1939年5月。
(61)邵次公:《重刊皮氏驳五经异义疏证序》,《河南儒效月刊》,1935年。
(62)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经史抉原》,第105页。
(6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宾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53-492页。
(64)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燕京学报》第39期,1950年。
(65)李源澄:《上章先生书》,《学术世界》第1卷第2期,1935年7月。
(66)直声:《评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40期,1932年8月8日,第8版。
(67)张鹏一:《读廖季平六译馆丛书评语》,《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第2期,1933年3~4月。
(68)钟泰:《中国哲学史》,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362页。
(69)俞樾:《春秋榖梁传条例十卷·叙》,《国粹学报》第68期,1910年7月。
(70)柯劭忞:《春秋榖梁传注序》,《学衡》第64期,1928年7月。
(71)牟润孙:《蓼园问学记》,《注史斋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39页。
(72)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经史抉原》,第106页。
(73)李源澄:《与陈柱尊教授论公羊学书》,《学术世界》第1卷第11期,1936年5月。
(74)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第32页。
(75)刘咸炘:《经今文学论》,《推十书》,第109-112页。
(7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宾四卷》,第604、562页。
(77)钱穆:《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8),第397页。
(78)贺麟:《学术与政治》,《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48页
(79)胡朴安:《二十年学术与政治之关系》,《东方杂志》第21卷纪念号,1924年1月。
(80)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250-252。
(81)甘蛰仙:《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学术蠡测》,《东方杂志》第21卷纪念号,1924年1月。
(82)郜积意:《汉代今、古学的礼制之分——以廖平《今古学考》为讨论中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7卷第1册,2006年3月。
(83)廖平:《致某人书》,《四益馆杂著》,《六译馆丛书》,四川存古书局,1921年。廖季平遗稿:《评新学伪经考》,《孔学》第1期,1943年8月。
(84)吕思勉:《论经学今古文之别》,《吕思勉读史札记》(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25页。
(85)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五,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2788页。
(86)蒙文通:《论经学遗稿三篇》,《经史抉原》,第148页。1940年代,蒙文通对“伪今文学”的认知有所改变,此转变牵涉民国三四十年代蒙文通与言“超今文”的学者分殊,另文详述。
(87)罗志田:《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5期。
来源:《中国哲学史》2012年4期
【考古词条】铁器时代 · 成都凤凰山明墓
明蜀王世子朱悦燫墓。在四川省成都市北郊凤凰山南麓。朱悦燫葬于永乐八年(1410),墓制反映了明永乐至弘治时期的亲王陵墓制度。197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四川省博物馆发掘。我要新鲜事2023-05-25 18:50:230003夏朝都亡了 商朝频繁迁都究竟躲谁 考古显示:商朝避的并非洪水
都城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通常集聚了一个国家的大部分经济、政治和军事资源。因此,都城的选择对于新兴王朝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旦被攻破,意味着国家的灭亡。然而,商朝却频繁进行都城的迁移,几乎显得“随性”而不受拘束。1、商朝的迁都现象我要新鲜事2023-06-09 21:36:440000海外国宝:东周王陵,金村遗珍
金村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主要收藏在以下地方,一个是弗利尔美术馆,另一个是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当然还有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的金链玉佩饰是金村玉器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组,是目前为止艺术水平特别高且有代表性的一组佩玉。但是如图所见的形式是复原的结果,由于缺乏原始出土资料,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我要新鲜事2023-06-03 10:33:380000杨立华和李零关于《丧家狗》一书的争论
2007-05-1822:54:40杨立华发文评价《丧家狗》。题目:《丧家狗》与“哗众取辱”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0434cc0100096u.html现在,“哗众取辱”的人越来越多了。想在一个“自我媒介”的时代引起关注,最便捷的莫过于“哗众”。至于通过“哗众”取来的是宠是辱,就无足轻重了。0000四川遂宁一工地挖出古墓:为宋代小型石室墓,墓室结构被损坏
据四川遂宁市文物保护所消息,5月18日,在遂宁市河东新区灵泉大道的僧家沟社区四组景观大道工程施工现场,发现一处古墓和一些陶器随葬品。我要新鲜事2023-05-22 10:04:5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