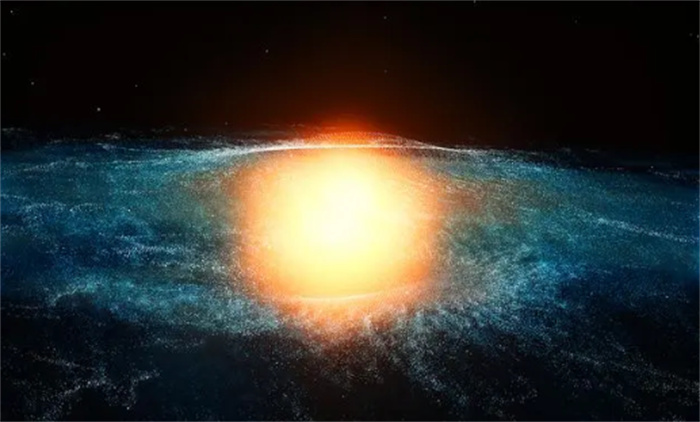曾入选高考卷的文章|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下
(接上)
3.等级身份与奴隶制
1952年郭沫若写成《奴隶制时代》一文[89],第二节是“殷代是奴隶制”,其根据除了认为殷墟发掘大墓中大批的殉人是奴隶外,另一重要根据即是认为甲骨卜辞中所见从事农耕的“众”(“众人”)是奴隶。对郭氏这一看法,50年代中叶有少数学者持不同意见,如认为“众”是“自由民”,是“家长制家庭公社成员”[90],但未引起重视。直到70年代末,多数教科书与论著仍从此说,有的还发挥了郭氏的看法,如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91]。1973年张政烺曾发表《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92],虽亦在奴隶社会前提下论及众人身份,但强调“众”生活在百家为族的农业共同体中,为殷王担负师、田、行、役等徭役,因此区别于以往将“众”视为类似希腊、罗马奴隶制中的那种奴隶形态,对于促进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有相当重要的启示作用。
进入8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相继对殷墟卜辞中“众”的身份作了新的探讨,其共同见解是“众”(“众”与“众人”为一)非奴隶。1981年笔者发表论文主张“众”是生活于族组织中的商人族众,属平民阶级,有着某种独立的族的经济,能参加一定宗教活动,是商王国的主要军事力量,以服劳役的形式受商王与贵族的剥削;并将殷墟西区族墓地中的小型墓葬中的墓主人与众相联系[93]。1983年杨宝成、杨锡璋两位长期从事殷墟发掘的学者亦撰文指出,殷墟小型墓的墓主人生前应属于聚族而居的平民,身份与甲骨卜辞中的众相吻合[94]。尤其需要提到的是裘锡圭1982年的论文[95],文中认为,从卜辞看,广义的“众”意思就是众多的人,大概可以用来指除奴隶等贱民以外各个阶层的人;而狭义的“众”应是为商王服农业劳役的主要力量,他们无疑也是广义的“众”里面数量最多的那一种人,应该就是相当于周代国人下层的平民。这种看法是相当全面、稳妥的。对以上见解有的学者不以为然,仍坚持“众”是奴隶说,认为以上文章在对卜辞的分析与对文献史料的解释上未有突破性的进展,且缺乏理论的阐明,并认为众人是保存有族氏组织的奴隶,而在中国被征服的族保存族组织是研究中国奴隶制类型的一个重要课题[96]。
有关等级身份与奴隶制问题的研究,还应该提到对有关战俘、人牲与奴隶关系问题的讨论。1979年姚孝遂发表的《商代的俘虏》一文[97],强调不应把见于甲骨刻辞早、中期用作牺牲的俘虏定为奴隶,俘虏只有当其活下来从事劳役时才有奴隶身份。对姚氏提出相反意见的是1982年杨升南的《对商代人祭身份的考察》一文[98],认为用作牺牲的人应已是奴隶而不是刚抓来的俘虏。1982年罗琨的论文《商代人祭及相关问题》[99]赞成将用作人牲的俘虏与奴隶相区别,但羌人已多被用为畜牧奴隶,成批杀祭羌人是为了给过去的先王补充财富与臣民。
卜辞中的“众”与人牲的身份直接关系到商代晚期商王国内是否存在着大量的作为农业劳动者的奴隶,因此也影响到对商代社会形态的看法,所以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此类问题还可能会继续引起古史研究者的兴趣。
4.家族形态及宗法制度
以往对商人家族的研究大致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较宏观的研究,即论述商人家族的类型、分布与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及其与王朝的关系;另一个是微观式的研究,深入家族内部,具体地剖析商人家族内部的组织结构、等级结构及经济生活。这两个侧面在诸家的论著中往往兼顾,但时有侧重。
1950年出版的丁山遗著《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100]试图将文献与甲骨文资料相结合,以说明“殷商后半期的国家组织以氏族为基础”。在当时能有这样的眼光是十分难得的。遗憾的是,他将记事刻辞中的“示”读为“氏”,从而将示龟、示骨者均当作族氏名称,并以此作为立论基点,这样就影响了他见解的可靠性。1950年发表的张政烺的论文《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101]是一篇名作。他将商代家族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论证了商人族氏不仅是商王的军事组织,也是为商王服役的农业组织,使古史研究者们对商代家族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有深刻印象,对促进这一问题的研究有较大影响。
由于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大陆的古史研究偏重于政治与经济制度,对社会结构关注不够,所以对商人家族的研究,特别是对商人家族的类型及其在当时国家内的地位很少有文章涉及。50年代中叶日本白川静有《殷代雄族考》7篇[102],具体地考察了与王室同出一族而后立于王都周围的7个商人强宗的地望及在商代社会内的作用。1968年林巳奈夫发表《殷周时代的图象记号》[103],将商金文中的族氏名号与甲骨文中出现的地名、人名、贞人名相比较,对商人族氏的诸种类型作了分析。
80年代以后,国内古史研究者对古代社会史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对商代家族的研究也有较多的成果。笔者在《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一书中用专门章节论述了商人家族的类型(子姓与非子姓宗族,子姓中的王族、子族及其他家族的构成及相互关系),商人诸宗族与商王室在宗教、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关系,肯定了商人诸宗族对商王国的支柱作用[104]。从宏观上讨论商人家族类型的论文还有刘昭瑞《关于甲骨文中子称和族的几个问题》[105]与葛英会《殷墟卜辞所见王族及其相关问题》[106]。葛文对“王族”、“子族”的内涵作了许多新的解释,他也提出当时存在多王族,这与前述齐文心、高明论述商代多王的论文有某些相合处,唯葛氏将其理解为部族的联合。
促进商代家族研究走向深入,进入上述第二个层面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是甲骨卜辞中“非王卜辞”的发现与论证。“非王卜辞”即王以外商人贵族的卜辞,这种卜辞的内容直接关系到占卜者贵族所在家族的事务,是了解商人家族内部形态与制度的弥足珍贵的资料。早在1936年,董作宾在《五等爵在殷商》一文中即讲到,卜辞中有称“子卜”或“子卜贞”的,“疑此子乃王子某,但称子不自署名而已”[107]。1938年日本贝塚茂树著文肯定了这个说法,并认为这个“子”是多子族的族长[108]。后来他在与伊藤道治合写的论文中又称这种卜辞为“多子族卜辞”[109]。1958年李学勤发表《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一文[110],首次提出“非王卜辞”的概念,并从称谓系统、字体、内容诸方面将非王卜辞作了分类,推定了诸类非王卜辞问疑者的身份,说明他们与商王室有一定的亲属关系,他们各自家族有封地,有的拥有师旅,参加政治与军事活动。在此文中,李氏将他所划定的几种非王卜辞时代定为帝乙,但后来又改变了这一看法,赞成其为武丁时期卜辞[111]。继李氏后,林沄在60年代完成的论文《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家族形态》[112]中正确地将“子”解释为当时对男性贵族的尊称,同时指出几种非王卜辞占卜主体的家族属商人父权家族,并对此种家族之形态(如家族构成、族长权力、经济情况等)作了具体论述,从而将对商人家族的研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对商代家族制度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宗法制度的探讨上,自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否定商人有宗法制与嫡庶制后,长时间内少有学者持异议。1944年胡厚宣在《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一文[113]中,根据商晚期康丁后已传位于长子,提出宗法在殷代已萌牙[114]。1982年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一文中[115],进一步论证了在甲骨文时代已存在宗法制度,认为其表现是强调宗子世袭与大小宗统属关系。杨升南《从殷墟卜辞中的“示”“宗”说到商代的宗法制度》一文[116],通过卜辞中反映出来的王位继承制上的嫡庶制论证商代宗法制度的存在。
嫡庶制的存在在古代社会主要是在多妻因而多子的父系家族内为选择家长继承人所建立的一种习惯法,以避免权力继承上的混乱。但事实上立嫡长子之制往往会受到干扰而不能严格实行,此种情况下不能说即没有宗法。所以宗法制的实质是什么,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从商周时代情况看,似应主要是指宗子在家族内的主祭权与对族人政治、经济上的控制与支配权。在卜辞中可见到子姓商人贵族参加由王主持的王室祭祀活动,商王具有相当于宗子的地位,表明其与子姓诸贵族间的确存在着大小宗的宗法关系[117]。
由甲骨卜辞揭示的生动细致的商代家族形态与家族制度不仅使我们对商代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的了解更丰富充实,更立体化,而且由商代家族的存在与社会功能也可以看到当时国家的形态特征,所以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商史研究中很重要的收获之一。
5.宗教、祭祀与宗庙制度
对商代宗教观念与宗教活动的深入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了解商代社会的关键。由殷墟卜辞中能够感悟到,商人宗教发展阶段实质上已由自然宗教(亦称自发宗教)发展到了人为宗教第一阶段的民族宗教阶段。此时商王室故去的祖先已被奉为商民族与国家之神。同时商人还在思索、寻求一种在能力上超出祖先神与自然神的统一世界的力量,在此过程中所创造的神即是“上帝”,但它只是此种思索不成熟的产物。于殷墟卜辞中频频出现的“上帝”早就引起学者们的注意。30年代初,傅斯年即据卜辞、西周金文与文献评论过殷周之际帝天观念的演变[118]。50年代中叶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出版,其中亦专有几节论帝,总结了商人上帝之权威,并认为当时上帝不受祭。但迄今对卜辞中有关上帝内容所作最系统、全面解说的论著,还应说是胡厚宣的《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119]。文章论证了上帝是殷人的至上神,是殷王形象在天国的反映,而且将卜辞中的“王帝”之称解释为是死去的帝王,为王权神化的表现[120]。文中亦主张上帝不享祭。这篇论文的见解长期以来被学者们所信从,于多处被引用。但近年来陆续有学者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1990年晁福林在《论殷代神权》[121]一文中,认为在殷代尚未出现至高无上的王权,天上也未出现至高无上的神。1993年笔者在《商周时期的天神崇拜》[122]一文中,亦根据卜辞资料与宗教学理论提出上帝虽在商人神灵系统中地位崇高,但并未与祖先神、自然神形成明确的上下统属关系,故并非至上神。由于对商人上帝的研究是对殷代宗教研究的一个重点,牵涉到对古代中国宗教与思想文化的认识,研究者间尚有较大的分歧,这显然需要在今后加强讨论。
在商代祭祀的研究上最重要的成果,是董作宾对周祭制度的研究。1945年董作宾公布卜辞中有一种用五种祀典轮番祭祀其祖先、周而复始的制度,他称之为“五祀统”[123]。有的学者评价这一发现是“他把那散落在沧海里的珍珠,从深水淤河里捡出来,再穿贯成恰到好处的项圈,这真是一个伟大而精细的工作”[124]。董氏的见解后来又经岛邦男[125]与陈梦家作补充与修正,陈氏并称之为“周祭”[126]。1968年许进雄《殷卜辞中五种祭祀的研究》一书出版,系统论证了周祭之特性,受祭者之资格,重新排定了祭谱,在祀首拟定上与诸家以“肜祀”、“祭祀”为祀首不同,而是以翌祀为祀首[127]。这方面最新最重要的成果是1987年出版的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一书[128],因是在以上诸家工作基础上所作,搜集材料更为齐备,论证亦更为精密,因而纠正了前此诸家不少错误。本书还进一步论证了黄组卜辞(及商金文与雕骨刻辞)之周祭有三个系统,应分属三王,这对甲骨分组、分期及确定帝辛卜辞的存在有重要意义。
陈梦家的《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129]系统考证了卜辞诸祭名内涵。张秉权《殷代的祭祀与巫术》[130]一文,分析祭祀对象、种类、用牲与场所,全面检讨了卜辞中的祭祀制度。此外还有一些论著对卜辞中所见的一种或几种祭礼作专门研究,如胡厚宣对四方风神祭祀的研究[131],张政烺论□[上劦下口]田为祭田祖之祈年祭[132],宋镇豪、常正光对“出日”“入日”之祭的考察[133],连劭名对“血祭”的研究[134]等,都有独到的见解。
至于卜辞中所常见到的作为祭祀对象之神主其“示”的类型与内涵的研究,近年来也有新的进展。1985年杨升南发表论文[135],认为商王直系为“大示”,旁系为“小示”,大小示在受祭的礼数隆盛程度、宗庙保存与配偶受祭与否上有不同待遇。但大示的含义是否如以上传统看法为直系先王,近年来已有学者提出异议。如1982年曹锦炎著文认为大示为上甲至示癸六示,并非直系[136]。1989年笔者提出大示只包括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戊、大庚六先王,小示仍解释为旁系为妥[137]。
与祭祀制度研究相联系的是宗庙制度的研究,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将商王室宗庙作了类型的分划,并具体讨论了各类宗庙及附设祭所的庙主、功能、结构等问题,为以后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继陈氏后,金祥恒、杨升南、晁福林先后有文章专论或涉及商王室宗庙制度[138]。1990年笔者亦有专文讨论商王室宗庙的设置原则与意义,附属祭所的作用及宗庙制度对王室统治的作用,内中涉及宗庙占卜等问题[139]。最近石璋如在作殷墟建筑基址复原研究时,联系甲骨卜辞与文献,认为甲四、六、十二、三基址分别是祭上甲、三报二示、大乙至祖丁九示、及它示(迁殷后诸王神主)的宗庙[140]。石氏还有文章认为乙二基址为早期的右示(祭先公远祖及自然神所在),乙一(黄土台)为传说中的“高宗”[141]。这是第一次具体地将殷墟建筑遗存与卜辞中所见到的宗庙相联系。存在的问题是这样做不免有较多的推测成分,而且卜辞中的宗庙与殷墟建筑基址的关系似应该是在对整个基址群(甲、乙、丙组)进行综合考虑的基础上进行判断。
6.商代的历法与地理
殷墟甲骨刻辞的发现亦为研究商代历法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数十年来在这方面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1945年在四川石印出版的《殷历谱》是董作宾以12年时间利用甲骨文等资料撰写的研究殷代历法与周祭祀谱的巨著。在本书第一卷中提出商人采用干支纪日,一直连续至今日而未间断;商人之月为太阴月,有大小月之制(小月29日,大月30日),过14或16月后连置两大月;他认为当时采用阴阳合历之年,故有置闰月之法,19年而7闰,并依其新旧派之分的见解,指出旧派(如武丁)年终置闰(设13月),新派(如祖甲)则为年中置闰。在第三卷他还讨论了卜辞所见日、月食,企图证明当时已有古四分术与正月建丑之制。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进一步肯定了董氏的一些说法,同时作了修正,认为年终或年中置闰在一个时期(祖庚、祖甲)内曾并行。但陈氏批评董氏所提出的殷代历法为古四分术及正月建丑之说,认为“是完全错误的”。1981年出版的由天文史学家撰写的《中国天文学史》肯定了董、陈氏对阴阳合历与大小月的看法及董氏提出的干支纪日从殷代至今未间断的看法,并肯定了年终置闰,但否定了殷代有年中置闰的可能性[142]。
殷代以太阴纪月,治甲骨文的学者如董作宾过去多认为是朔日为首。上举《中国天文学史》与1984年张培瑜等发表的论文[143]均认为应是以新月出现为首。同样的看法,日本学者薮内清在1957年即已提出[144]。但1990年冯时发表《殷历月首研究》[145]一文仍认为殷人是以朔日为月首,因为相对疏阔的朔还是可以通过观测取得。由此可见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有关商代地理的知识对于商代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文献中有关的记载寥寥可数,因此殷墟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便格外引起学者的注意。开殷墟卜辞地理研究之先河者为王国维,他在1914(或1915)年撰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从当时已能见到的200余地名中选了8个距今安阳较近而又见载于文献的地名,考释了其地望。此时还谈不上地名间系联。真正为卜辞地理研究创立了一种行之有效而又科学的方法的学者是郭沫若。他在1933年出版的《卜辞通纂》(日本文求堂)中以商王田猎卜辞为研究对象(此种卜辞多附记当日占卜地名,即田猎驻地),通过同版几条卜辞干支之日差计算地点间的距离,而后又通过异版同名联系其他地名,从而结合文献记载建立起地理区域构架。此后,虽有不少学者继续开拓商代地理研究领域,但采用的方法皆本自于郭氏的干支系联法。至80年代末,治商代地理成绩突出的有董作宾、陈梦家、李学勤、岛邦男、松丸道雄与钟柏生[146]。董氏的成绩在于将黄组卜辞的征人方卜辞中经过地点系统地收集起来,按干支系联,借以考释其地望,并绘出路线图。陈氏则较全面地讨论了商晚期诸种地理结构,如大邑商所在之王畿地区与沁阳田猎区,勾画了卜辞地名网,并在伐人方路线上修正了董氏之说。李氏的专著将沁阳田猎区作了更细致的区域分划,更正了郭沫若将“衣逐”之“衣”释为地名的错误,指出“衣”当读为“殷”,训“同”或“合”。松丸道雄的著作则从理论上讨论了田猎地之间距离的推定方法,这是他超出其他诸家之处。钟柏生的论文集将卜辞地名作了分类,分为田游地理、农业地理、部族方国地理等。他详细评析了以前诸家研究的成绩与方法、观点上存在的问题,在田猎地名研究上虽仍主要采用干支系联法,但对辞例的条件作了较严格的规定[147]。
有关殷墟卜辞地理研究的最新成果是1994年出版的郑杰祥的《商代地理概论》[148],其特点首先是对地名作详细的文字考证,以求字识准确;其次是卜辞资料更为齐全,不仅利用了《甲骨文合集》,而且有《小屯南地甲骨》等新资料,是他书所未采用的;三是书中充分利用了最新的田野考古资料。
商代地理的研究虽然有较多成果,但由于卜辞资料本身的限制,对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之地望的看法分歧仍比较大。其中最明显的如商王田猎卜辞中所反映出来的主要田猎区究竟在哪里,现在即有河南沁阳、山东泰山、河南濮阳(及新乡以东、山东以西)三个地区三种看法;此外“大邑商”是一块区域名还是都城名?卜辞中的“商”地究竟在何处?这些重要问题都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深入讨论。
四
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到1999年即是100周年了,这对于中国史学界乃至世界史学界都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在甲骨学这一奇妙而又异常艰深的学术领域辛勤耕耘,收获了丰硕的果实。使这门学问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我们自然会想到今后应该如何使殷墟甲骨文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从而为中国与世界古代文明的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要做的工作很多,但以下几方面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一)继续致力于甲骨文字的考释
甲骨文研究要想继续深入,识别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难字是首先要做的一件基础性的事。甲骨文中有些字,仅是人名、地名暂时不识还无关大局,但有些字经常出现,对于理解辞义很关键,如长久不能识读或者不明确其字义,自然会影响到正确运用卜辞去研究史学问题。甲骨文字有其特殊的书写形式,在不同组、不同时期的卜辞中字形也有变化,此外还会有一字异体的情况。只有通过搜集更齐备的资料,搞清某些难识的甲骨文字字形演变的线索,寻找其与商周金文及战国、秦汉文字字形上的联系,同时注意文例的比较与同文的比勘,联系具体辞例疏通其字义,才有可能在文字考释上有所进展。最近饶宗颐先生谈到目前甲骨文字考释上有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是不注意弄清字形演变的过程,仅是孤立地分析字形构造,曲解字形;二是脱离文义搞纯字形考释,这样的考释对理解文义、通读卜辞于事无补[149]。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
(二)加强甲骨卜辞的分类、断代工作的科学性
甲骨卜辞发展的“两系说”、历组卜辞时代的提前等新见解是建立在对卜辞内涵深入分析基础之上的,如果新说能够较好地解决董氏五期分法不好解释的一些现象,当然是可以用来改造旧说的。但目前甲骨卜辞的分类与断代工作要更深入一步,还需增强科学性,要有科学的理论根据。例如新说欲成立,有以下几方面问题即需更好地解决:其一是分类的标准问题。近年来有的学者强调字体可以作唯一分类标准,但实际上几乎所有学者在分类时仍然未能脱离开陈梦家最先使用的以贞人组为基础的分类方法,而且这样的同一组卜辞在字体与时代风格方面总有某些较相近之处。所以,以贞人为基础分类与按字体分类还是可以有相适合的一面。现在,有些学者采用以贞人分组[150],同组下又按字体及风格更细致的差别再分小类,这种方法是可行的。比单纯用字体分类有较强的操作性,标准亦较好掌握。有些组之间从字体上看呈过渡状态的卜辞似可以采取依主要字形特征归入其上或其下某一贞人组范畴内的方法,似不宜分得过细,以致在实践中不好掌握。其二是“两系说”如何从史学角度作解释。上文曾引用有的学者的见解,认为两系甲骨出土坑位分布有区域差异,是持不同卜法的贞人(原说称卜人)将其占卜所用甲骨分别带回其居所之故。这牵涉到甲骨出土坑位地点与殷墟建筑基址的关系问题。甲骨出土于宗庙(及其他祭所)、宫室建筑附近,则这些宗庙宫室可能即是用甲骨占卜时的处所,在有的卜辞下还明记“在某宗卜”。所以要在宗庙占卜,可能与宗庙(及其它祭所)通过祭祀活动可以降神,因而可以更直接地得到神灵启示有关。如可以这样理解,则不同系统的甲骨出土坑位分布区域的差异也可能与不同的贞人组经常从事占卜的宗庙(及其它祭所)与宫室地点不同有关,不一定与贞人居所不同有关(

、宾等组卜辞出土坑位在小屯村北分布较散,贞人似不可能居住得如此分散)。与“两系说”有关的还有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同一个王会需要同时并存持两套属不同占卜体系的贞卜班子?特别是为同一事也需要由两套贞卜班子分卜,其缘由何在?是否与占卜制度有关?这一问题也是需要解释的。其三,历组卜辞时代提前亦有待于甲骨出土的地层根据作证明。而与此相关的问题是,甲骨本身使用年代与其在地层中的分布状况二者之间的关系(较早的卜辞何以常出现于晚期地层中,同一坑中不同组、不同时期的卜辞何以会混合堆积)还需作合理的解释,这也涉及到对甲骨(特别是刻辞甲骨)为什么会分置于窖穴、灰坑与散布于一般地层中的不同原因的探讨。所以甲骨卜辞的分类断代工作应更好地与田野考古工作相联系。
甲骨卜辞的分类、断代工作除了从上述几方面去努力外,对于不同类组卜辞内涵的分析、比较也是确定先后发展次序与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例如对于不同类组卜辞祭祀制度的考察即有助于分类与断代,因为同一个王世贞人组可能不同,占卜制可能有差别,但其祭祀礼制不应有两套。合理的分类、断代方案在类似这样的卜辞内涵上也应该是协调的。
(三)更好地利用甲骨文资料,深化对商代社会形态的认识
用甲骨文研究商史固然已取得许多收获,但在有关商代社会形态及等级身份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上,仍存在较多分歧。这些分歧的造成,有的在于对具体卜辞字释与辞义的理解不同,如“丧众”之“丧”,或解释为“丧失”,认为“丧众”指在战事中损失师旅;或解释为逃亡,认为“丧众”是指众人的逃亡,如果将众的身份理解作奴隶的话,即更可认为是奴隶的一种反抗斗争。当然,这种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深入考察有关的关键字词在商、西周时代使用的习惯并与相近同的文例相比勘;另一方面则需要从卜辞以及时代相近的文献语法角度来作论证。但是,对于有些关于商代社会形态的较重要问题所以产生分歧,可能主要还不在于对卜辞及一些考古资料的理解不同,而在于对应如何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如何认识奴隶制与奴隶社会等问题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内中当然也包括应本着什么原则去处理史料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中国社会在商代可以认为还处于早期阶级社会,商王国也可称为早期国家。从殷墟卜辞资料看,其有着许多不同于后世国家的特点。如此时虽有了实行专制主义统治的王、非居民自动武装的军队与一整套国家官吏机构,具备了作为恩格斯所说的“国家的本质特征”的“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151],但国家的基层组织并未完全实现地域化,以贵族阶级为主干的各宗族仍在亲族范围内保留着血缘关系,当然其总体已非单纯的血缘关系,而是一种经过改造的国家政治与军事单位。在此种国家内,各宗族内部占多数的平民族众与族中的贵族阶层已存在阶级差别,平民族众成为国家的主要兵源与诸种劳役(主要是农业劳役)的实际担负者,从战俘与被征服民中转化的奴隶多用于王室或各宗族内专为贵族阶层服务的手工业机构及畜牧业中,或用作贵族家内奴仆。如果以上特征可以认为是事实的话,那么像商王国这种早期国家,应该像张光直先生所讲的,可作为世界历史中的国家的基本类型之一[152]。更好地利用甲骨卜辞资料与其它多种考古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实事求是地阐明商代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与人文、地理环境下国家与阶级社会的实况与特点,从而丰富我们对中国国家起源与其早期形态的认识,这不仅是对中国古史研究,也是对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极有意义的事情。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古史研究者能有共识,则在对殷墟卜辞中反映社会等级身份与经济形态、国家形态的许多资料的解释上,即能够展开更为热烈而又更富学术意义的讨论,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商史研究的深入。
(四)加强对商代祭祀制度的研究
有关祭祀制度的内容在殷墟甲骨文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作为“国之大事”之一的祭祀,在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自然应是甲骨文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但是至今除了对周祭制度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外,其他诸种祭祀制度的研究仍相当薄弱,尤其是诸种祭祀制度之间的体系关系没有搞清,其间还有不少难点。例如在卜辞中与周祭卜辞形式相近的岁祭至今尚很少有学者作深入研究,其与周祭的关系也需要探讨。即使是周祭制度也有问题,出组、黄组存在此种制度,但年代处于出组与黄组间的卜辞,以至于宾组卜辞也有类似的祭名,是否也有类似的周祭,只是未见于卜辞?董作宾用新派、旧派解释,赞同者不多,但如非新、旧派所致,何以会在祭祀制度上有如此大的起伏?又如常见的*[左酉右彡]祭,总附带其它祭名,其间必有祭礼之间的属从关系。再有,常说的“祭名”、“用牲法”是否能分清?诸祭名的内涵是什么?凡此都是需要今后甲骨学者们作深入考察的重要问题。
(五)在甲骨文研究中积极采用新技术手段
首先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早在1987年南京大学范毓周等即设计了“计算机甲骨文信息处理系统”,采用义形四位等长码输入甲骨文,与激光照排系统连接,用于印刷甲骨文书刊,并可用于教学与科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土文献研究中心于1995年9月开始筹备甲骨文资料库电脑检索系统,预计在1998年底可以完成全部工程,其成果同时可以用来修订、补充现有的类纂一类工具书。台湾成功大学也有学者在采用电子计算机技术编制“世界甲骨检索全集”,其成果将可以方便地检索甲骨卜辞的全文与片语。总之,可以预知,将有更多的单位与学者致力于将电子计算机技术运用于甲骨文研究,大大地提高研究的科学性与效率。此外,1996年5月16日开始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采用加速器质谱法(AMS)测定有年祀、称谓和天象记录的甲骨的年代。毫无疑问,将诸种高科技手段应用于甲骨文研究是今后甲骨文研究的新途径。
注释
[89]收入《奴隶制时代》一书,科学出版社1956年11月版。
[90]“自由民”说见斯维至《关于殷周土地所有制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徐喜辰《商殷奴隶制特征的探讨》,《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历史)1956年第1期。“家长制家庭公社成员”说见赵锡元《试论殷代的主要生产者“众”和“众人”的社会身分》,《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4期。
[91]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92]载《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93]《殷墟卜辞中的“众”的身份问题》,《南开学报》1981年第2期。1982年张永山也有《论商代的“众人”》一文,除引甲骨卜辞资料外,深刻分析了《盘庚》篇里众的身份,并认为众属平民,但内部两级分化,文章收入《甲骨探史录》,三联书店1982年9月版。
[94]《从殷墟小型墓葬看殷代社会的平民》,《中原文物》1983年第1期。
[95]《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文史》第17辑,1982年。
[96]王贵民:《商代“众人”身份为奴隶论》,《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
[97]载《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
[98]载《先秦史论文集》,《人文杂志》增刊,1982年5月。
[99]收入《甲骨探史录》,三联书店1982年9月版。
[100]《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编辑,科学出版社1956年9月版,此书含《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殷商氏族方国志》(未完稿)两篇文章。
[101]《历史教学》2卷3期(1951年9月)、2卷4期(1951年10月)、2卷6期(1951年12月)。
[102]收入《甲骨金文学论丛》5至8集,油印本。
[103]载《东方学报》(京都)第39册,1968年。
[104]按:这方面的论述是以80年代发表的有关论文为基础的。
[105]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06]收入《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1990年6月。
[107]《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本3分,1936年。
[108]《关于殷代金文中所见图象文字

》,《东方学报》(京都)第9册,1938年10月。
[109]《甲骨文断代研究法的再探讨》,收入《殷代青铜文化的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3年。
[110]载《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111]李学勤:《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文物》1981年第5期。
[112]《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113]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之一,1944年出版。
[114]但他释卜辞“妇某”之某为姓,以证明殷代女子称姓,属族外婚,也作为宗法存在之证明,今日看来并不确切,“妇某”之某似是指父家之氏名。
[115]《文史》第17辑,1982年。
[116]《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
[117]参见拙作《商周家族形态研究》。
[118]《安阳发掘报告》第2期,1930年。
[119]《历史研究》1959年第9、10期。
[120]李学勤认为殷墟甲骨文的“王帝”其实就是“皇帝”。见其为刘桓《殷契存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所作“序言”。
[121]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122]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123]《殷历谱》,《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年。
[124]屈万里:《殷虚文字甲编考释·自序》(小屯·第二本),台北,1961年。
[125]《殷虚卜辞研究》,日本弘前大学文理学部中国学研究会,1958年。
[126]《殷虚卜辞综述》。
[127]许氏后又有《第五期五种祭祀祀谱的复原》,载《大陆杂志》第73卷第2期。
[1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129]《燕京学报》第20期,1936年12月。
[130]《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9本3分。
[131]《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复旦学报》1956年第1期。
[132]收入《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33]宋镇豪:《甲骨文“出日”、“入日”考》,收入《出土文献研究》第1辑,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常正光:《殷人祭“出入日”文化对后世的影响》,《中原文物》1990年第3期。
[134]连劭名:《甲骨刻辞中的血祭》,《古文字研究》第16辑,1990年。
[135]杨升南:《从殷墟卜辞中的“示”、“宗”说到商代的宗法制度》,《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
[136]曹锦炎:《论卜辞中的示》,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1987年成都。
[137]《论殷墟卜辞中的“大示”及其相关问题》,《古文字研究》第16辑,1989年。
[138]金祥恒:《卜辞中所见殷商宗庙及殷祭考》(上、中、下),《大陆杂志》第20卷第8—10期,1960年4—5月;晁福林:《关于殷墟卜辞中的“示”和“宗”的探讨》,《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杨升南文见前页注[14]。
[139]《殷墟卜辞所见商王室宗庙制度》,《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
[140]《殷墟地上建筑复原第六例——兼论甲十三基址与柁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5本3分,1984年9月。
[141]《殷墟地上建筑复原第七例——论乙一及乙三两个基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本4分,1995年12月。
[142]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43]张培瑜等:《试论殷代历法的月与月相的关系》,《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144]《关于殷历的两三个问题》,郑清茂译《大陆杂志》第14卷第1期,1957年7月。
[145]载《考古》1990年第2期。
[146]董作宾:《殷历谱》,《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年;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岛邦男:《殷虚卜辞研究》,日本弘前大学文理学部中国学研究会,1958年;松丸道雄:《关于殷虚卜辞中的田猎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0册,1963年;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台湾艺文印书馆,1989年。
[147]钟氏在选择辞例时注重严谨性是非常正确的。但田猎卜辞资料本身总显得比较粗疏,如该书第93页所举《前》2.44.5辞,在甲、乙、丙三个占卜地点(田猎驻地)各自占卜时间是壬申、戊寅、壬午三日,壬申、戊寅间相隔五日,戊寅至壬午间相隔三日,但似乎不能据此就可以肯定甲至乙地是“需时六日”,乙至丙地“需时四日”,因为商王究竟何时动身,何时到达都没交待,这样估计两地间距离总有不严格处。即使是钟氏书中30页所举典型辞例也不是没有这种问题,某日在甲地贞今日“王步于乙地”,又于某日在乙地贞“今日步于丙地”,何以能知道王从甲地到乙地是什么时间到达的呢?未必是两个干支日之差所走的路程。所以利用田猎卜辞作地理研究有较大的推测性,需依靠文献与实际地名相联系,调整相对位置。
[148]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6月版。
[149]《甲骨文研究断想——为纪念于省吾先生百年诞辰而作》,《史学集刊》1996年第3期。
[150]无贞人称“无名组”,亦是建立在以贞人为标准基础上的。历组无贞人组,是按与历卜辞字形有共同特征这个因素归为一组的,黄组情况亦近似。
[151]《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
[152]参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53、54页。
来源:《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非洲角鼻恐龙:轻巧龙 小腿比大腿长很多(堪称奔跑能手)
轻巧龙是一种角鼻龙下目恐龙,诞生于侏罗纪末期,也就是差不多1亿5千万年前,属于植食性恐龙的一种,体长可达6米,属于中型恐龙,身材修长,非常的善于奔跑。第一批轻巧龙的化石是在非洲坦桑尼亚发掘出来,非常幸运的是这具化石还算是非常完整,只是缺少部分颅骨化石。轻巧龙的外形特征我要新鲜事2023-05-08 11:43:380000观展:古国觅踪:关于刘家洼和古芮国的故事
翻阅史籍,有关芮国的记载寥寥数笔,时隐时现,这难免让人产生许多想象。近日,“古国觅踪:关于刘家洼和古芮国的故事”展览在渭南市博物馆展出,243件文物展品、别出心裁的展厅布置,以寻幽探秘的方式,带领观众走进神秘的古芮国,感受周代庄重典雅的礼乐文化,和古芮国的发现及历史脉络。我要新鲜事2023-05-26 21:21:170000惊天大发现:江苏挖出9座西晋皇陵,内藏无数奇珍异宝!
2015年夏天,江苏省邳州市煎药庙村正在进行宅基地退耕工程。施工人员挖掘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村民们怕有意外发生,立即报警,并得到了民警的及时赶到。在现场,工人们还在进行挖掘工作,但突然听到砰的一声,挖掘机碰到了什么东西,还出现了几块很大的青砖,旁边是一个积满水的洞穴。经过初步勘探,邳州市文物局的专家认为这个地方并不是煎药庙的遗址,而是一座东汉时期的古墓。我要新鲜事2023-04-11 21:12:560001死神龙:蒙古小型镰刀龙类(拥有镰刀状前爪/长4.5米)
死神龙是一种兽脚亚目下的镰刀龙亚科恐龙,诞生于9200万年前-83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它们的平均体长可以达到4.5米左右,前肢生长着典型的镰刀爪,属于植食性恐龙的一种,最早的一批化石发现于蒙古国。死神龙的体型我要新鲜事2023-05-10 12:48:260000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中华智慧
【说明】本文为郭静云教授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陈禹同采访所写(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0月24日第3版),现在全文刊出。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其实与中国传统中古老的天地人“三才”观念相符。根据此概念,天地的长久,天与地的交合是人的作用,是从每一个人,到天与地之间的所有人,经过各自生命及携手合作而达致的。人类合作只能基于尊重和包容各自的差异,做到和而不同。我要新鲜事2023-05-25 13:40:17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