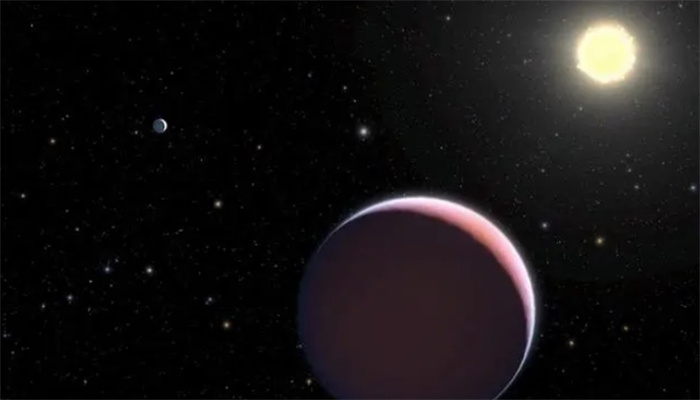人类最早的用火行为出现在什么时候
用火是人类史前史上的重大技术发明,对于人类演化和社会文化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人类可以用火加工食物、取暖、照明,驱赶野兽。在火的诸多功用之中,对早期人类生存和演化产生尤为关键影响的是加工食物,这也是我们能够在遗址中发现相对较多线索的一个方面。化石证据显示,在直立人阶段人类的身体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与考古证据所显示的该阶段肉食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构成密切相关。然而,食用没有加工过的生肉,一方面在咀嚼上费时费力,另一方面不利于消化。除了使用石器把肉切割成小片或小块这种方式,早期人类还可能使用火把生肉转变成易于咀嚼和消化的熟肉。块茎类等植物性食物也很可能被早期人类加热后食用。大脑和肠道器官的运作需要耗费大量能量,它们每单位质量消耗的能量差不多,由于熟食更利于消化和吸收,用火加工食物可能促使较少的能量被用于消化,而更多的能量被投入到大脑。直立人的身体体型和脑量与南方古猿相比有显著增加,有可能与吃熟食减少了咀嚼的时间以及咀嚼和消化过程中的能量耗费有关,同时人体从熟食中获得了更多的能量。

总之,用火加工食物能够改善食物质量,拓展人类的可食用资源,对于人脑的增大和人类身体结构的演化起到关键作用。从长期来看,吃熟食为人类成功繁衍与生存奠定了基础。用火还为早期人类走出热带非洲,扩散到温带环境,特别是在气候寒冷或干凉的冰期的迁移提供保障,为人类生存地域的开拓创造了条件。随着人类认知和技术的发展,火被应用于更多的方面,例如制作粘合剂、木器、骨器以及复合工具,对石料进行热处理、烧制陶器等,促进了史前人类改变生计策略,赋予人类更多的适应生存优势。使用火还具有社会效应,可以创造出把群体成员聚集在一起的环境氛围。人们围火而坐,分享食物、交流沟通,有助于促进成员之间的合作,加强社会关系。随着狩猎采集社会的发展,用火在人类社会的仪式活动中也扮演重要角色。总之,控制性用火的行为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为人类开辟了新的生活方式。

那么,火何时开始在人类生活中发挥作用,人类从何时起习惯性地使用火或控制性用火呢?早期用火行为的出现与发展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经常存在争论的热点问题。有观点认为,一些含有燃烧遗存的遗址揭示了在匠人或直立人出现时期(距今约200万年前)人类使用火的可能,这有助于解释早期直立人大脑的显著增大、身体结构的演化、食物构成的转变——更高质量、热量的食物被纳入食谱以及早更新世人群走出非洲扩散到欧亚大陆等现象。需要注意的是,人类用火的最初阶段可能与自然火关系密切,特别是在非洲赤道附近地区,因为该区域存在着发生自然火的较多可能。早期人类有可能对自然火进行利用,然后逐渐学会控制用火。
然而,早更新世,特别是距今100万年以前直到中更新世中期用火的考古证据非常缺乏,既有的一些证据从埋藏学的角度看还存在不确定性。非洲发现了年代最早的疑似人类用火的证据。例如,肯尼亚库比·福拉地区FxJj20遗址(东地点和主地点) (距今150万年)发现了4块可能为烧土的堆积,直径大约30—40cm,厚度10—15cm,其中三块“烧土”由大块胶结的砂质黏土构成,颜色为淡红色或橘色,有些部位为深红色。热释光研究表明,这些土块确实被烧过。另一块“烧土”为灰黑色砂质黏土,有的部分发生了炭化。肯尼亚柴索万嘉(Chesowanja)遗址也发现有烧过的土,受热温度可达400℃,年代距今140万年。肯尼亚奥罗格赛利(Olorgesailie)遗址发现了似“火塘”的结构,是一处下凹的堆积结构,其中包含石制品和动物骨骼,不见木炭。南非施瓦特克朗(Swartkrans)遗址发现距今150万年前的烧骨。然而,这些发现都存在着一些疑问,即不能确定燃烧遗存是人类用火还是自然野火燃烧的结果,或者有些燃烧遗存可能经过了自然作用力的搬运,因而不足以证明遗址上发生过原地用火活动。

近些年,库比·福拉地区FxJj20 AB地点的新发掘发现了人类用火的证据。遗址位于一个由东向西倾斜的缓坡上,分析显示,斜坡没有影响到遗物的分布位置。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和骨骼碎片,小于20mm的石制品占40%,石制品倾向分布没有规律。遗址的自然堆积物由细砂和粉砂组成,分选很差,反映了遗址形成过程中较弱的流水动力。微形态分析显示,遗址有可能因为季节性洪水被快速掩埋,没有受到流水和生物活动的明显扰动与破坏。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表明遗址中存在烧过的物质。从空间分布来看,烧过的物质存在集中分布区,这个区域与动物骨骼分布区存在较大面积的重叠。此外,遗址中存在四个较大尺寸石制品的高密度分布区、两个小型—微小型石制品的高密度分布区,前者和后者均没有重叠,但小型—微小型石制品的集中分布区与动物骨骼和燃烧物质的分布区重叠。这一发现虽然不能完全证明非洲早更新世早期人类控制用火,但反映了人类活动与火之间存在着关联。这个地区经常有野火发生,人类可能以某种方式对自然火进行了利用。南非万德威尔克(Wonderwerk)洞穴距今100万年前的堆积中发现了保存状况良好的灰化植物遗存和烧骨、具有壶盖形破裂的石制品以及加热过的沉积物,微形态和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证明这些遗存反映了原地燃烧事件。燃烧遗存数量多,在洞穴的第10层整个堆积中都有分布,并且堆积物中缺少动物粪便,从这些现象判断,燃烧遗存的形成很可能与人类行为有关,而不是自然燃烧事件的结果。
西亚黎凡特地区的亚科夫女儿桥(Gesher Benot Ya aqov)遗址发现了距今约78万年前人类用火的证据。然而,该地区缺乏此后很长一段时期里的人类用火证据,直到距今约40—30万年前,甚至更晚时期,用火证据才有所增加。以色列凯泽姆(Qesem)洞穴距今42万年前的用火遗存以及塔布恩(Tabun)洞穴距今35—32万年前的用火遗存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凯泽姆洞穴中发现有烧骨、烧过的石制品和沉积物,这些遗存普遍分布在7.5m厚的堆积中。下部堆积中只有一些不连续的燃烧遗存透镜体,而上部堆积中存在较厚的富含灰烬的堆积,其中还包含大量烧骨碎片和烧土块。塔布恩(Tabun)洞穴E层中发现有深棕色或黄色的燃烧遗迹,与其周边堆积物的颜色不同。这一层中还分布着若干块易碎的白色堆积物,其中包含受过热的燧石。
欧洲也同样缺乏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用火遗存,仅有零星的距今40万年前的证据。英国山毛榉坑(Beeches Pit)遗址(距今约40万年)是欧洲旧石器时代早期用火证据的重要代表。该遗址记录了丰富的人类打制石器活动(很可能存在多次活动事件)。当时该地点靠近水边,且距离燧石原料产地很近。拼合研究显示,遗物受到的扰动破坏很有限。遗址中常见燃烧遗存,包括烧过的燧石——大多呈红色、破碎状,热释光分析显示其燃烧温度超过了400℃。遗址中还发现了具有清晰界限的遗迹,其底部和边缘为发生氧化的红色沉积物,上边覆盖深色的堆积物,周围分布有密集的烧骨以及烧过的燧石石制品,研究人员推测该遗迹有可能是火塘。德国北部薛宁根遗址13 II—4层中发现有变红的沉积物以及疑似燃烧过的植物遗存,曾经也被视为欧洲的早期用火证据之一。然而,微观研究(岩相学和微形态)显示:变红的沉积物是堆积形成后铁的沉淀和氧化造成的,少量炭化植物遗存很可能是在自然野火中形成的。同样,薛宁根13 II—3层中疑似烧过的沉积物和薛宁根12B中疑似的烧木经检测都没有被加热过。这项研究表明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在欧洲较高纬度地区的生活似乎并不必须依赖火,同时揭示出微观方法在用火遗存的埋藏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也有观点认为,不同时期的用火风格和方式会造成用火遗存的不同保存状况,所以很难根据可见的考古材料复原欧洲早期人类用火和适应生存的历史。
东亚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用火证据曾以北京周口店遗址第一地点第10层和第4层的发现为代表。后来对遗址西剖面的微形态和矿物学分析指出:曾经被判断为“灰烬”的堆积物,其真实成分并不是燃烧形成的,比如第10层的“燃烧遗存”是静水环境中富含有机物的堆积物,其中包含烧骨和石制品,但不存在燃烧遗迹或典型火塘结构。堆积中没有发现烧木材所形成的灰烬成分,也没有发现燃烧留下的植硅石和硅聚集(如果灰烬由于成岩作用发生溶解而没有被保存下来,那么堆积中至少应当能够发现在相同埋藏环境下不易溶的植硅石和硅聚集)。第10层中有些骨骼确实经过了燃烧,但由于堆积在静水环境中,它们不能反映原地的用火事件。第4层主要是崩积作用改造后的黄土堆积,也存在具有层理结构的流水沉积物,没有发现灰烬堆积。虽然存在红色沉积物,但应当是成岩作用下形成的(第4层总体上经历了很强的成岩作用改造。这些认识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周口店遗址人类原地用火问题也没有最终的结论,但这些争论引发了我们对遗址环境、遗存埋藏过程、堆积物与人类活动关系的特别关注,推动了我们对旧石器时代遗址埋藏学研究的思考。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微形态分析的样品是从遗址的西剖面获取的,从取样位置来说具有局限性。此外,近10年来,研究人员对西剖面所在区域展开了新的发掘,在第4层中发现了带有围石结构的火塘,其附近分布有烧骨和石制品。堆积中还存在丰富的植硅石,堆积物具有高磁化率值和红度值,这一发现提供了周口店第一地点以及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用火的新证据。然而,尽管我国较多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报道了燃烧遗存的发现,但经过埋藏学分析的材料极为有限。因此,有关早期人类控制性用火在我国出现与发展的问题仍然有待探讨。

综上,旧石器时代早期(特别是较早阶段)旧大陆用火遗存的发现非常有限,燃烧遗迹不容易得到保存和判断,燃烧遗存形成的原因和埋藏过程经常存在争议。有些遗存表面看上去像是用火形成的,但是通过微观视角和遗址形成过程的整体分析,我们会发现它们与人类用火或原地用火行为无关。从更新世早期与燃烧有关的现有考古材料来看,早期人类对火的利用是比较偶然的、零星的。直到中更新世晚期,距今25—20万年前人类对火的控制使用才明显加强,稳定地用火成为人类技术和行为组合中的一部分(含有明确的直接和间接用火证据的遗址数量明显增加,这类遗址的规模增加或者占用时间相对更长),与人类文化更加充分地交织在一起——人们在日常生活和象征行为中都会使用火。晚更新世,常见用火遗迹尺寸和结构多样、多个用火遗迹在平面上重叠,反映了人类对火的利用的加强、适应行为的发展,同时这些发现能够为分析遗址空间结构和遗址占用过程提供非常重要的信息。
人类用火行为最早何时出现,在怎样的背景下出现,特定时空背景中人类用火行为的细节、强度以及与用火活动相关的空间利用与维护等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人类演化历程的认识以及对旧石器时代人类适应行为和栖居模式的复原。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必须以对遗址中燃烧遗存的准确识别以及对其形成过程的认识为前提。在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灰烬、木炭、烧骨、烧过的沉积物、烧过的石制品、烧裂的岩块经常被视为遗址上发生用火活动的证据。然而,我们必须要分析这些遗存如何形成、如何被保存或者如何从遗址中消失。这些遗存中某一类的存在,甚至多种燃烧遗存的组合并不一定反映人类控制性用火或者原地用火。有些遗存也可以在自然作用过程中产生或者形成堆积。若要证明遗址中存在过人类用火行为,我们首先需要判定曾经发生过燃烧事件,其次证明燃烧遗存与人类的活动有关,然后才能进一步提取有关人类用火和占用遗址行为的信息。对此,我们需要将微观和宏观视野的研究结合起来,对物质材料受热或燃烧的状况进行判断,对燃烧过的物质材料或者与燃烧有关的堆积结构的形成与变化过程进行谨慎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燃烧遗存的空间结构,解读它们与遗址占用事件之间的关联。
本文摘自:曲彤丽《旧石器时代埋藏学》
盗墓者不要的棺材,专家看到后赶紧收进博物馆,上绘房中私密图像
莒县博物馆收藏的一块特别画像石本文作者倪方六在国内文博圈,有“全国汉碑半山东”一说,《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画像石全集》总共8卷,前面3卷都是山东的,可见山东出土汉朝碑石之丰富。山东画像石,不只山东省博物馆有大量精美而珍贵的碑石藏品,就是县域博物馆也有这一类珍物。如嘉祥、莒县、东平、沂南、章丘等很多地方,都曾出土了大量画像石,如嘉祥县,武梁祠石刻名气很大,当地还专门建了“武氏祠博物馆”。我要新鲜事2023-05-26 17:23:500001湖南一禁地传言被“阴兵”看守,村民从不上前,专家进入却发现奇
如果细细也阅读每一个国家的文化,就会发现,其实在每一个国家都有着类似于鬼怪的传闻,并且经过多年的成绩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潮流,就像在如今的电影类型当中,经常会有恐怖片,惊悚片这些,而这些恐怖片的题材很多都取材于民间的传说。我要新鲜事2023-05-04 18:57:410002世界级别的神秘考古发现 其中中国的一项是最神秘的 外国人都羡
考古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历史,还可以探索历史中的谜团。在世界各地,有很多神秘的考古发现,其中中国的一些发现尤其引人注目。中国最著名的考古发现之一就是秦始皇兵马俑。虽然已经发掘了大量的兵马俑,但专家们仍然无法完全了解秦始皇的墓葬。这个谜团一直困扰着考古专家和历史学家,但我们相信,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会找到更多的答案。我要新鲜事2023-05-09 14:51:040001国外网友:为了证明夏朝的存在,中国对夏朝的考古有多少进展?加
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按照时期来分,一共有二十九个朝代,当然实际的国家数量可能更多,而我们所熟知的就是中国自夏朝以来,清朝结束的历史。但是外国人认为夏朝可能不存在,对此他们认为因为考古证据的不足,夏朝可能不是第一个王朝而是部落群体。我要新鲜事2023-05-09 13:52:08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