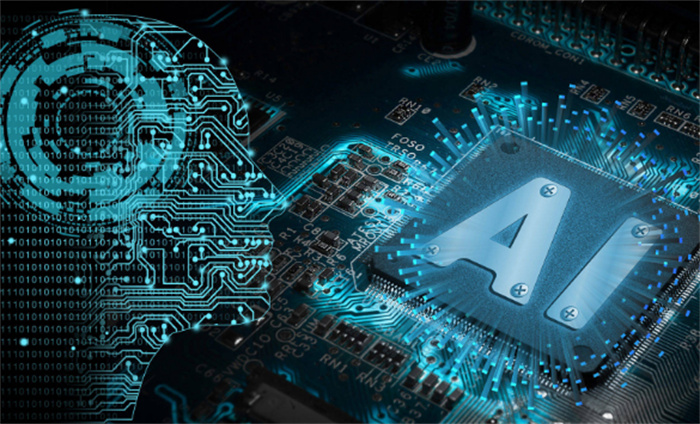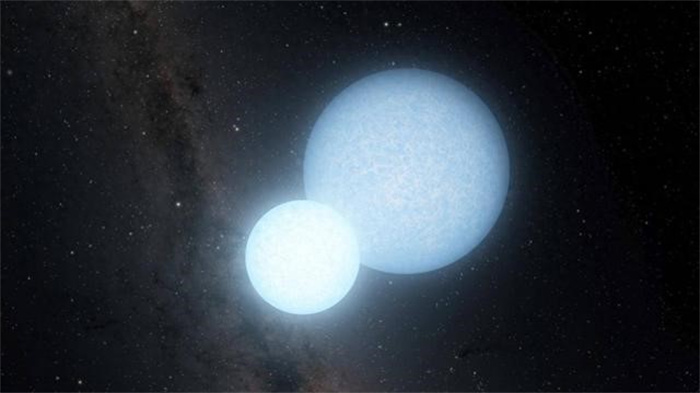陈胜前:文化考古刍议
虽然考古学研究古老的材料,却是一个年轻的学科,我们熟悉的近代考古学体系直到19世纪末期才形成。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考古学研究发展出了若干范式,每一种范式似乎都希望建立一个完整的考古学体系,贯穿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在考古学的不同领域都能够普遍适用。而且,还希望考古学的研究能够为其他学科、乃至于社会大众所理解与利用,改变考古学作为一门冷僻学科的形象。其中,文化是一个应用最广泛的概念,从近代考古学形成至今,“文化”是不同范式都会用到的概念。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是考古学家有最大共识的概念,虽然歧义也最多。笔者曾经就考古学的文化观做过分析,提出要发展多维的考古学文化观①,这里希望进一步拓展这个问题的讨论,尝试运用“文化”的概念来建构一个考古学理论体系,弥合当前考古学研究不同范式之间,以及考古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断裂。由于这个问题牵涉众多,相关研究匮乏,所以只能说是一个初步的理论探索,期望能够促进更多更精彩的考古学理论思考。
一、分裂的考古学
考古学虽然称为一门学科,但是它从其形成至今,基本都是分裂的。近代考古学由三个先后形成的分支组成。首先出现的是艺术史,它扩展为古典研究,历史考古与之一脉相承,这个分支视考古材料为物质文化(物质跟文献一样都是古代历史的载体),强调研究其意义,以延续文化精神为己任。稍后在北欧科学古物学的基础上发展出史前考古学,它扩展成为史前—原史考古(即新石器—原史考古)。这一分支的形成深受19世纪民族主义潮流的影响,其主要目的是要建立地区或民族的早期社会历史序列,了解“祖先的荣光”或社会生活状况。旧石器—古人类考古出现最晚,它立足于地质学的均变论以及当时还在雏形阶段的生物进化论(其中还混合着斯宾塞的社会进步论),其目的是要探索人类的古老性,突破《圣经》思想的约束。在三个分支之外,还有一个小的旁支,殖民地考古,它更接近史前—原史考古,其中贯穿着明显的种族主义思想,不过原住民与考古遗存的直接历史关联的方法促进了史前—原史考古的发展,广义上,它属于史前—原史考古。
从考古学术史分析的外史(与时代背景、思潮与相关科学进展的关联)与内史(与理论、方法与实践的关联)来看,这三个分支都是不同的。唯一能够把它们联系起来就是物质遗存以及部分获取、研究物质遗存的方法。其实,即使在发掘层面上,旧石器考古也有所不同,它更接近地质、古生物学,无法运用较晚阶段考古的方法。理论层面上,考古学实际缺乏统一的理论。在史前—原史考古中更流行文化历史考古,过程考古学的主要应用领域还是旧石器考古,后过程考古经过二三十年的摸索,如今更多应用于历史考古领域。尽管不乏交叉领域,但是适用性的偏向还是非常明显的。究其原因,差异的背后是不同的外在与内在关联。文化历史方法强调研究特定群体的史前史,关注其文化成就,因此特别适合民族国家的考古学研究,至今仍在许多国家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在那些感到受到剥夺、压迫、威胁的国家与那些需要民族团结的国家。其重要的意义是促进民族自豪感与凝聚力。而旧石器考古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人类的演化史,对于人类的研究,除了生物特征之外,就是人类行为。因为缺乏直接历史关联,物质材料的文化意义极难追寻。那时候的人们游动采食,群体边界模糊,器物风格因素贫乏,不可能如史前—原史考古那样建立明确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编年。历史考古领域因为有文献的帮助,研究者与所研究的对象之间存在文化的直接关联,行为研究或是谱系编年都不是研究的重点,重要的是通过物质文化来传承意义,物质文化就像文献经典一样,或者说文献经典也是一种物质文化②,它们保存了我们的文化传统。
考古学是一门年轻的边缘与交叉的学科,从考古学的分支演化历程来看,它处在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之间。虽然说每个学科都会有类似的牵涉关联,但是很少有学科像考古学这样,三个主要分支实际上分属不同的学科大门类,从艺术史发展而来的历史考古,更多属于人文领域,至今其顶层的研究(底层研究是以材料为中心的)仍然注重研究文化意义,包括风格的、艺术的、礼仪的、宗教的意义等。史前—原史考古是当代考古学的代表,它明显属于社会科学研究,关注的是社会历史问题,如民族文明起源。旧石器考古更接近自然科学,实际上,这在现实科研、教育体系设置中也有反映,如我国就将旧石器考古归入自然科学系统中。因为牵涉的领域如此广阔,不同分支之间差异又如此明显,某种意义上说,考古学就是一个分裂的学科。这种分裂跟它的发展历史有关,跟它多样的研究目的相关。不同分支立足的共同基础仅仅是实物材料,但是考古学的发展不能局限于此,考古学需要整合地发展。
二、考古学家研究什么?
促进考古学整合的条件其实已经出现了。近二三十年来,考古学的发展出现三个引人关注的趋势。首先是理论考古学的兴起,过程考古学一直强调发展考古学理论,但是理论考古学形成一股研究力量还是近二十多年来的事③。考古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思考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第二个趋势是考古科学的繁荣,大量的考古科学分支形成,从相对传统的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到以基因为对象的生物考古,还有诸如地质考古、绝对年代测定、GIS、特征成分分析与鉴定等等。考古学实验室相继成立,大量的研究资金投入其中,大大改变了考古学的传统面貌。第三个趋势是文化遗产管理、博物馆、公众考古学等涉及社会历史文化传承项目获得相当的关注。三个发展趋势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考古学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考古学家研究什么?因为第二三个趋势使得考古学的发展大大复杂化了,当考古学家发现古代遗存之后,很快进入到考古科学分析的各个领域,然后进入到文化遗产管理、博物馆等社会历史文化领域。这是否意味着考古学家就仅仅负责去发现、发掘与初步整理考古材料呢?这样的压力无疑是存在的。另一方面,理论考古学的发展推动我们进一步思考这样的问题,考古学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仅仅因为是研究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材料么?
中国考古学中,考古学被定义为“属于人文科学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实物资料包括各种遗迹和遗物,它们多埋没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因此,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④。这是一个复杂的定义,它高度强调了考古学通过田野调查发掘来获取实物研究材料的重要性。它指出考古学的目的是要去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同时又说它属于人文科学领域。这就意味着考古学研究的历史应该更着重文化意义,更多符合从艺术史而来的历史考古的目的。这与提出定义的两位研究者夏鼐与王仲殊先生都是历史考古学家是一致的。显然,这个定义不大可能为史前—原史考古学家或旧石器考古学家完全认同,不过都会认同实物材料的重要性,这几乎是不同考古学分支唯一的共识。
是否考古学家除了调查发掘实物材料之外,就别无身份认同了呢?中国考古学中,田野调查与发掘的大量工作都是由技术工人完成的,考古学家需要做什么呢?如果考古学家不能在理论研究上有发展,那么其身份就可能泡沫化。考古学家应该是那些研究考古之“理”的专业人群。我们何以可能通过实物材料了解古代社会呢?我们的研究途径以什么“理”为基础呢?我们希望了解古代社会的什么信息呢?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如此等等的问题促使我们去思考考古学存在的理论基础。而贯穿于考古学理论基础的核心就是“文化”,这可能是我们在理论上首先能够寻找到的共识。
三、考古学与文化的关联
理论上来说,“文化”这一概念是不同考古学分支、流派或范式之间少有的共同概念。诸如社会、历史等概念都缺少理论的内涵。“文化”的概念是研究者的构建,它是对某种存在状态的人为设定,而非描述,就像社会、历史这样的概念所做的。其最广义的认识就是,文化包括人类的一切物质与精神产品,也就是说,它是针对人类自身而言的,具有很强的排他性。我们一般不会说其他物种有文化,即便提及,也只是说类似人类,或者说是萌芽状态的文化。人类学家泰勒提出过一个经典的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⑤。这个定义更强调文化的精神性与社会性,它启发了考古学中对“文化”概念的商用。虽然这个概念跟考古学研究由实物材料所代表的文化有较大的差异,但是它为考古学讨论文化提供一个参考的框架,即何其为现实社会生活中之文化。不论是从研究人类的角度出发,还是基于考古学发展历程的考虑,文化都是考古学研究的核心。文化的定义众多,我们或许不能就此达成共识,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在不同层面上把握它。
1.文化的起源与作为适应的文化
偏重于研究旧石器考古的过程考古学特别关注文化的起源,其形成也是人类演化的重要标志,文化是人类适应外在世界的基本手段。也就是说,文化是功能的,人类运用文化,比如工具,去获取必要的食物资源与安全防护。人类通过文化来弥补自身体质上的不足,如通过用火烤熟食物,使之更容易消化;使用锋利的石片,弥补牙齿撕咬能力的不足,如此等等。人类的文化并不仅限于制作与使用工具,而是一个包括众多因子的系统,不同因子之间相互作用。宾福德将这些因子分为三个层次:技术的、社会的以及意识形态的⑥,而其基础则是自然环境,人类文化与环境之间通过长期的互相影响形成文化—生态系统,包括狩猎采集者的文化生态系统、农业文化生态系统等,其中还有许多按照时间、空间、特定属性区分的类型。如狩猎采集者文化系统中存在依赖水生资源的类型⑦,包括民族学中的北极海洋哺乳动物狩猎者、北美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史前时期的西北欧洲中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日本绳文时代居民等。因为依赖类似性质的资源,他们的文化适应方式具有某些共同点,其定居能力明显比一般狩猎采集者群体更高,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加复杂的社会组织,其礼仪式也更复杂,如北美印第安人中类似“夸富宴”(Potlatch)的仪式⑧。文化系统在不同层面上都可能反映出文化适应的基本特征。简言之,旧石器考古研究中文化是考古学家研究的基本对象,不过他们侧重的是文化的功能、文化适应的机制与形态、文化—生态系统中诸因子之间的相互关联等。这样的文化观在研究人类适应方式变迁如农业起源的过程能够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它可以帮助我们回答为什么农业能够起源⑨。
2.考古学文化与文化历史
“文化”的概念引入考古学研究中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就是在史前—原史考古分支中。19世纪末的考古学家面对一个难题就是面对丰富的考古材料,在分期、分区的基础上无法了解物质材料特征组合的归属。在19世纪的社会背景关联中,族群属性问题是主要的关注点。蒙特留斯等使类型学方法系统化,但是没有提出相应的概念以研究史前人类社会群体。种族主义者科西纳较早运用“考古学文化”来定义考古材料特征组合,暗示它指代某种人群,在他看来,那就是德意志民族的直系祖先。柴尔德是集大成者,他首先运用“考古学文化”的概念来构建欧洲史前时代的历史框架。在这类研究中,“考古学文化”都被假定为某个史前人类社会群体的标志。同一时期,北美考古学者也提出类似“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并且区分出大小不同的级别,但影响均不及“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广泛。
何其为“考古学文化”?现代考古学理论研究者注意到,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是以共同性为基础的,因为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考古特征组合而被归为同一文化。这种共同性即是一种标准,一种区分是否属于同一文化的标准。作为标准的考古材料特征组合大多是风格意义上,比如陶器纹饰、器形等,它暗示着从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人群具有某种观念上一致性,或称心灵同一性。所以说,“考古学文化”虽然是一个立足于实物材料的概念,但是其内在的前提是观念或心灵上的。史前—原史考古领域的研究者正因为具有“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他们才有可能研究史前人类社会群体,尽管他们并不知道划分群体的确切标准,显然,“考古学文化”并不对应于民族认同、语言、血缘、宗教、阶级等现代划分社会群体的标准,它甚至不能对应经济形态、政治组织,而是更接近“乡土地域”的概念。
有趣的是,在史前—原史考古领域流行的文化历史考古范式并不是如过程考古学所批评的那样完全不考虑古人的生活方式的。特里格注意到在过程考古学产生之前的“功能主义考古”,如英国的格拉汉姆·克拉克的“生态考古”以及他的学生建立的“剑桥古经济学派”,北美戈登·威利的“聚落考古”。包括晚期的柴尔德也注意古代社会的经济形态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其实,还可以追溯到史前—原史考古的早期渊源,北欧的科学古物学与史前考古,同样在分析考古材料特征的同时,注重史前人类生活方式的研究,如沃尔塞的多学科研究。国内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点,如指出苏秉琦先生面向海洋与面向内陆的两大文化区系⑩,不只有风格特征的意义,也有生态适应上的意义(11)。
当然,必须承认文化历史考古中“文化”的主要意义不是功能上,而是风格上,也即是形式上的,暗示的是心灵的同一性,而非文化适应方式(生计形态)的统一性。但是运用“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考古学家可以把具有一定时空范围的某个“考古学文化”视作一个人类社会群体进行分析,这在旧石器考古领域难以实现。总之,在史前—原史考古领域,“文化”同样是最基本的概念,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历史考古范式主要赋予“文化”以一种社会历史意义,以之指代某个时代一定地域的某个社会群体,而且这个群体与当代社会群体有历史关联。
3.文化的意义与作为文化研究的考古学
近代考古学的最早前身是艺术史研究,主要研究古希腊罗马时期遗留下来的艺术品,这也是文艺复兴精神的延续。近代欧洲经过中世纪黑暗时期,重新从伊斯兰文明中翻译古希腊的经典文献,从中获取古希腊的科学理性精神、政治文化传统、审美观念等。艺术史是以实物研究的方式来揭示其中所包含的古代文化内涵。这里实物就相当于文献,也就是所谓的“文本”,但它比文本更加直观、更真实,更需要研究者的切身体验与感知。这里所说的文化内涵乃是一种历史的积淀,它不是革新与破坏,而是继承与关联。比如古希腊罗马雕塑所传递的美学原则,它为西方文化所继承。因为具有这样的历史关联,所以今天的西方人能够感受其美。而这种美跟我们中国文化缺乏历史关联,所以当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不懂西方文化的时候,他就不会体会到其中的美,不会被触动,也恰如不懂中国文化的西方人面对唐诗宋词、《红楼梦》一样。文化的历史积淀形成丰富的文化意义,积淀的形式不仅仅是文献经典,更主要的方式是物质文化,甚至文献也可以说是一种物质文化。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比西方的艺术史研究更早,它们所关注的内容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吕大临认为金石学的研究宗旨在于:探其制作之意,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对于宋代金石学者而言,金石古物之中蕴含这三代时期完善的政治文化理想。对这样的研究而言,古代遗物就是浓缩了古代文化的宝藏,需要后人不断地揭示,从而完成文化的延续。
在西方,在艺术史的基础上发展出古典研究,拓展出埃及与亚述学,这些研究都关乎西方文化的渊源脉络。再后,历史考古兴起,成为更大规模的考古学分支,但是它们所秉承的“文化”观念是一致的,即考古学研究的是物质文化,即物质具有丰富的文化含义,恰如历史学研究文本一样,其意义可以反复地阐释,在此过程中实现文化的传承。在历史考古领域擅长的后过程考古强调的正是物质材料是有意义的,是历史的,关乎人类的能动性——文化通过一代代人的阐释而意义得到丰富,意义的存在取决于历史的关联背景,或称为历史潮流,而不是因为某种意义是科学的,其他意义都是不科学的。意义的阐释可能存在伦理上对错,而非科学意义上的对错。男性的解释与女性的解释一样合理,社会上层与下层,西方与东方之间也是如此。在这里物质文化不是功能的,更多是一种象征,类似于文字符号;物质文化意义重要的地方并不是其族群属性,或者说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心灵同一性,而是处在历史关联中的人们的阐释。就好比我们理解一句话需要情境一样,历史关联是理解物质文化的基本前提。我们通常把这种具有历史积淀的文化称为文化传统,它的形态是物质的,但实质是精神上的。
4.文化与考古关联的新发展
上面我们看到在考古学发展史上,“文化”这一概念与考古学的关联,它的应用标志着近代考古学的成熟。作为研究的核心,它一直引领考古学研究。考古学对于“文化”的探讨从形制(如文化历史)到功能(如过程)再到意义(如后过程),体现出逐层深入揭示的研究过程,所以文化的涵义一直在变化。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种螺旋式的结构,比如晚近出现的后过程考古学与最早出现的艺术史都强调文化意义的研究。从另一方面来看,当代考古学研究还在不断强调文化与考古学的关联。也就是说,除了近似于螺旋式的逐层深入研究之外,还有在广度上的关联拓展,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多样,考古学研究的视野也愈加开阔。
当代进化考古学强调文化与自然关联,其中双重演化理论提出人类演化存在两条并行的途径:一条是自然的途径,一如其他生物,通过基因传递遗传特征;另一条途径是文化,它具有类似于基因的特征,或称为“模因”(memes),文化通过它来传递。按照双重进化理论,物质材料特征是“模因”的表现型,考古学可以通过研究物质材料特征来探讨文化的演化形态。至于“模因”的内在本质,目前还不得而知。进化考古学中比较极端的观点认为文化的演化同样服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需要借助“模因说”。进化考古学看待文化的角度与过程考古学类似,尤其是其中的文化生态、行为生态的观点本身就是过程考古学的基础,但是进化考古学并没有局限于从功能的角度来理解文化,而是进一步拓展了文化,试图将“文化”的地位提升到类似于基因之于当代生物学的地位,即文化应该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对象。
而从当代认知理论看来,文化乃是社会认知的积淀,也是人之区别其他动物最重要的特点。正是通过文化不断的积累,在不同代际与群体之间有效传递,并在传递过程中不断革新、改良,成就今天我们看到的人类极为复杂与高级的文化(12)。当代认知考古学特别注意到人类文化的社会认知属性,强调考古学研究人类认知的起源,以及社会认知的表现形式(13)。广义上说,认知考古是过程考古学的延伸,其代表人物如科林·伦福儒、肯特·弗兰纳里都是过程考古学的代表人物。但有趣的是,认知考古学所依赖的文化概念并不像典型过程考古学那样,将之视为功能的,甚至是技术的,它在功能之外还有象征的含义,通过长期历史积淀、选择,形成群体共同认同的意义。所以,从文化的含义来说,认知考古学介于过程与后过程考古学之间,但是它强调是文化另一类属性。
从历史发展进程中,我们很容易注意到文化的扩散与消亡,比如19世纪殖民主义狂潮以来迅速消失的狩猎采集者文化。文化消失的途径包括人口的绝灭(如塔斯马尼亚人)与锐减(北美印第安人)、人群的融合、语言的消失等等,在现代急剧扩张的工商业社会面前,许多传统文化都在迅速消亡。在当代国际竞争中,我们也看到文化作为软实力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作为社会选择的单位存在。与进化考古学不同之处,文化在这里不是可还原的单位(如模因),而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整体。体质上,人群本身可能并没有消失,但其文化已经消亡。考古学研究关注文化多样性的变化,某种意义上说,它映射了我们当代社会对于文化多样性丧失的关注。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把文化视为一个完整的社会群体单位,跟文化历史考古有较好的关联,或可以成为文化历史考古发展的方向之一。
文化的另一种关联是将文化视为人类能动性的体现:从人的属性来看,除了自然性、社会性之外,人还有一个属性,就是文化性。文化是人的非自然属性,是为人所独有的性质。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与使用者,也就是说,文化体现了人的能动性。当代考古学运用能动性范式来研究物质材料,将之视为渗透了人之活动、认知与精神构建的存在,即并不存在纯粹客观之物(14)。不同研究者对能动性的理解十分多样,如布迪厄将之理解为“无意识的认知结构的复制”,这里文化是人浸淫其中的所谓“惯习”(habitus)(15);霍德则将之视为“个体在创造自身生活过程中行动的经验”(16),文化是个体的经验;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观点将之视为“通过社会创造活动改造物质的形式”(17),文化是人类社会群体的行动。如此等等的观点将文化的关联拓展为一个极为广阔的领域,考古学研究的主题因此可以包括身体、体现、物质参与、权力等。
四、文化考古的概念体系
我们通常说考古学是一门研究实物材料的学科,按照中国学术界对考古学的定义,它属于人文科学,以研究历史为目的。然而,当代考古学的研究实践表明这个定义其实过于狭窄了。20世纪年代以来过程考古学兴起,其目的是要把考古学发展成为一门科学,最好能达到地质学那样的程度。80年代出现的后过程考古学更具有颠覆性,实证科学遭到批判。而最近一二十年考古学多样化的发展使得学科的领域进一步拓展。某种意义上说,考古学概念体系的建设落后于考古学的研究实践,即当前的概念体系并不能包括考古学的发展范畴。前文我们看到,考古学很大程度上是一门分裂的学科,我们可以说出若干个特色鲜明的考古学分支,它们各有其核心概念、学术目标、相关学科,甚至是社会应用领域,但很难说它们有统一的考古学概念体系。当前,我们将其统称为考古学的基本理由就是,它们都研究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材料。这是否是说考古学是一门关于考古材料的科学呢?显然,按照这样的视角,考古学就是一种技术或方法,是工具或手段,称不上是一门科学(广义的)。考古学的现实是严峻的,因为缺乏必要的理论建设,考古学有沦为工具化的危险。这也就使得理论体系的建设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即使是一种尝试。
当代考古学的分裂是多重的,最大的裂痕是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其次是三大考古学分支由来已久的裂痕。再者,考古学理论体系还面临传统与现代的难题,每一个理论体系若都是重起炉灶,那么前人的劳动也就将前功尽弃,这实际上是不符合知识发展的一般规律的。革新与改良需要兼而思之,实践证明现代主义式的割裂历史只是一种空想。对于中国考古学而言,还存在另外一种矛盾,那就是西方与中国,我们是否仅仅需要向西方考古学学习技术方法,而无须考虑它的理论呢?或是仅仅考虑某些理论教条而无须考虑其思想基础呢?这是否是将西方学术工具化的考古学版呢?在这个矛盾之中,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现实,那就是中国考古学亟待一个概念体系,能够兼容传统与现代,兼容科学与人文,能够会通中西。当然这样的目标可能过于庞大,但这无疑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契机是存在的,从考古学的发展史与现状来看,不同时期、分支、流派或范式的考古学都是以文化为核心展开的,文化是考古学中罕有的共同理论基础。考古学目的是通过研究实物遗留来研究人本身,关于实物遗留争议不大,但是何其为“人本身”,众说纷纭。作为实体的人首先是个生物学的存在;然后是一种社会历史存在;再者,人还不局限于此,人还是精神的存在。还需要强调的是,人的诸种存在是高度关联的,并没有独立于精神的生物学存在,或是孤悬世外的存在。所以,“文化”就成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概念,能够很好地表达人的属性,文化即人,人就是文化的存在。文化囊括了人类所有重要的属性,最重要的也许是,文化是考古学家可以研究的对象;若没有这个专属的领域,考古学就存在着工具化的风险,或是泡沫化,即考古学家并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似乎什么都可以,但是每一项工作都有更专业的群体来从事,考古学家成了局外人。
当然,风险同样存在,以文化为中心的考古学研究并不是什么特别新潮的看法,考古学其实一直都是以之为中心的,只是没有人专门指出来而已。文化是一个极端泛化的概念,如果它什么都包括在内,那么也就是说,它什么也没有说明。所以,这里提出一个分层与关联的方法,以使得文化考古现实可行。考古学理论一直存在分层的认识,特里格就将考古学理论分为低层、中层与高层理论(18),笔者则更详细地将考古学理论分为五个层次(19),并将之与考古学的“透物见人”的推理过程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考古学研究的过程本来就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这也就意味着在过程的不同阶段(即层面或层次)上需要不同的概念支撑。与之相应,文化考古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上展开。首先是功能层面上的,经典的案例是文化适应方式的研究,比如狩猎采集者为什么会放弃既有的生活方式转而从事农业生产,考古学家通过探索狩猎采集者的文化适应机制进而来回答这个问题。次之,可以从社会历史层面上进行研究,典型的如文明起源机制的研究,文明起源涉及社会组织的复杂化,它不是一个生计层面的问题,而由权力、阶层等新的社会组织因素形成。最后,还需要从文化意义层面上研究,这里文化更多是一种精神形态。这三个层面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广泛的交融,比如研究农业起源现在也有社会与象征的视角。跟宾福德所说文化系统的三个层次相比,这里更强调文化概念的弹性,不同层面上所强调的文化涵义是不同的,并不秉承同一个功能的模式。
功能—社会—意义是文化考古推理的基本顺序,这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需要组织的材料也不断增加,在意义研究的层面上,甚至还需要加入研究者个人的体验。功能的研究相对比较具体,一件陶器的生产与使用通过实验室分析、实验考古研究以及出土关联的分析可以大致了解。而在社会层面上探讨,就需要考虑器物的风格,风格代表一个社会群体,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通过风格反映出来。当我们探讨意义的时候,必须要将它放在历史中去考察,一件器物可能反映了一个时代心理与精神结构。更好理解的例子是穿衣,服饰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写照,而在当时社会的人们看来,怎么穿着是社会关系规定的,而其最基本的功能不过是保暖遮盖而已。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分层研究是过程,而非最终的目的。我们最终希望得到的是对一个文化体系的认识。以辽西史前农业社会研究为例,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不同考古学文化阶段农业生产的状况,然后了解其社会关系的发展,再后探索物质文化的意义,整体融合起来,形成我们对这一地区史前时代的宏观认识。我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文化考古是一项寻求“见森林”的努力。当然,在具体研究层面上,还需要细致的工作,这两者并不矛盾。而在当前,我们的考古学研究最欠缺的可能还是目标的缺失。文化考古无疑是一个可行的方向。
在分层研究之外,就是要去拓展关联,探索文化更多的内涵,从认知考古、进化考古、能动性考古等出发是目前已有的角度。如当前在环境考古之外兴起景观考古,注重古代人之于环境的认知——人生活在所认识的环境中,他们把自己融入到环境中,一草一木都是有意义的。内蒙古白音长汗遗址包含从小河西到小河沿共五个阶段的考古学文化,这个遗址的朝向偏北,历史与现代村落都没有再选择这个位置。但它隔河正好面对一处风化石,当地称“蛤蟆石”这样一处景观可能对白音长汗的五个史前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例子表明我们在聚落的位置分析上还可以有更多的拓展空间的。在关联的探索上是没有止境的,人类生活的关联因素有多少,那么可以探索的因素就有多少。把分层与关联区分开来的好处就是,考古学家知道自己的基本任务,然后还可以去扩充自己的研究领域。
最后,我们可能实现对史前时代文化体系的建构与理解。文化体系其实是建立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文化系统、结构、象征等概念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把这些概念视为不同层次的研究工具的话,那么文化体系就是广义的文化最深层、最稳定的内涵。它没有将自然与人、物质与精神视为二元对立的,而是视为相互关联的一体。一方面它具有明显的相对性,即不同的体系可能有其自身标准;另一方面,体系又具有绝对性,它是明确存在之物,并不是一个神秘的心理结构。当然,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结构。它考虑到了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也包括心理因素在其中。这样的话,考古学的研究就上升到了非常宏观的层次,考古学也就不再仅仅是一门研究物质材料的学科了。
文化考古是一个宏观的视角,它旨在解决分裂的考古学缺乏共同认同的概念体系的困难,避免考古学家研究空心化的趋向。它并没有试图去建立一个全新的体系,而是寻求立足于考古学的历史与当代的实践,超越过程与后过程考古的简单对立,也就是寻求弥合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文化考古也没有简单排斥文化历史考古,而是认为它具有发展社会历史层面研究的实力。文化考古同样欢迎最新的考古学理论探索,如进化、认知、能动性、景观等等因素的关注,它强调在功能—社会—意义之外进行广泛的关联探索,最终构成对文化体系的了解与理解。文化考古体系的建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探索过程,一方面,从功能到文化意义,逐层深入;另一方面,从模因到能动性,不断拓展关联。从深度与广度两个维度上发展。我们可以将文化考古视为考古学研究的核心,其实,考古学家如果不能研究文化,他们就可能什么都研究不了,即便是实物材料;考古学家若不是文化人,考古学也就失去了其终极意义。
①陈胜前:《考古学的文化观》,《考古》2009年第10期。
②Hodder,I.Reading the Past,3rd ed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2003.
⑤肯·达柯:《理论考古学》,刘文锁,卓文静译,岳麓书社,2005年。
④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⑤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⑥Binford,L.R.Archaeology as anthropology.American Antiquity 28:217-225,1962.
⑦Binford,L.R.Constructing Frames of Reference:an Analytical Method for Archaeological Theory Building Using Ethnographic and Environmental Data Set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2001.
⑧Arima,E.,DeWhirst,J.Nootkans of Vancouver Island.In Handbook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s,vol.7,Northwest Coast,edited by W.Suttles,pp.391-411.Washington,DC:Smithsornian Institution.
⑨陈胜前:《史前的现代化》,科学出版社,2014年。
⑩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11)曹兵武的发言,见《上山遗址与上山文化——中国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暨上山遗址学术研讨会上专家谈“上山文化”》,《中国文物报》2006年12月29日第7版。
(12)迈克尔·托马塞洛:《人类认知的文化起源》,张敦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13)Dunbar,R.I.M.The social brain:mind,language and society i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2:163-181.
(14)Barret J.C.Agency,the duality of structure,and the problem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In Archaeological Theory Today,edited by I.Hodder,pp.141-164.Polity Press,Cambridge,2001.
(15)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
(16)Hodder,I.Agency and individuals in longer-term processes.In Agency in Archaeology,edited by M.Dobres and J.E.Robb,pp.21-33.London:Routledge.
(17)Wobst,J.M.Agency in(spite of)material culture.In Agency in Archaeology,edited by M.Dobres and J.E.Robb,pp.40~50.London:Routledge.
(18)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19)陈胜前:《考古学理论的层次问题》,《东南文化》2013年第1期。
来源:《南方文物》(南昌)2014年第2期,第15-21页。
读《世纪敦煌》:“彼时与此时”的变迁,是敦煌故事的另一种讲述方式
在敦煌莫高窟第45窟唐代塑像低垂的目光注视下,小心地拆开书的塑封时,心中还暗暗地想着,没有拆封的新书一定没有作者签名,太遗憾了!我要新鲜事2023-05-07 07:34:390000刘备的儿子刘禅为什么会轻易投降? 历史学家: 此举救了很多人命
“轻易”二字说不上。刘禅的确不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圣君,但称之为仁君是不过分的。蜀汉在三国之中原本国力最弱、土地最小、人口最小,又经过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早已是民生凋敝。而刘禅又无足够的才能治理朝廷,于是在邓艾入蜀之前,整个蜀汉的处境就是“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有菜色。所谓‘燕雀处堂,不知大厦之将焚’者也”。我要新鲜事2023-05-25 18:31:360000考古队打开千年古墓 尸体突然动了(古墓尸体)
尸体因为外界空气进入,所以发生肿胀。在1985年湖南的一个村子里面发现了一个古墓,当时的考古技术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考古队在用了很大力气之后才终于进入到了墓穴当中,你在里面发现了一口棺材,当他们打开了棺材之后,发现里面有着十分浑浊的液体,液体当中有着一个女人的尸体,之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尸体是一个女人,是因为没根本没有腐烂,随后这个尸体发生了更加奇怪的事情。巨型古墓我要新鲜事2023-05-10 22:42:310000中国四个直辖市中,为什么设立最晚的重庆比北京更有故事?
重庆“母城”小考本文作者倪方六中国有四大直辖市,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其中设立最晚的,是重庆市。但是,重庆成为直辖市虽然最晚,城市史可一点不晚,有3000多年的历史,甚至比北京更早些,更有故事。我要新鲜事2023-05-27 01:41:080000在充满性暗示的墓地上,年轻考古专家遇到了无法忘记的高贵公主
原题:瑞典人西域“探险”记(五)——小河墓地上又现“神秘微笑的公主”本文作者倪方六前面,连说了几篇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中国西域寻宝、挖墓的故事,这篇再说另一个年轻的瑞典男人、考古学家贝格曼在中国西域探险生涯中的“艳遇”——小河公主的发现,这一篇就来聊聊此事。图:1934年5月底,瑞典考古学家F·贝格曼沿着这条支流向东南行进就西域墓葬方面的发现而言,值得斯文·赫定骄傲的还是小河墓地。我要新鲜事2023-05-27 14:47:15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