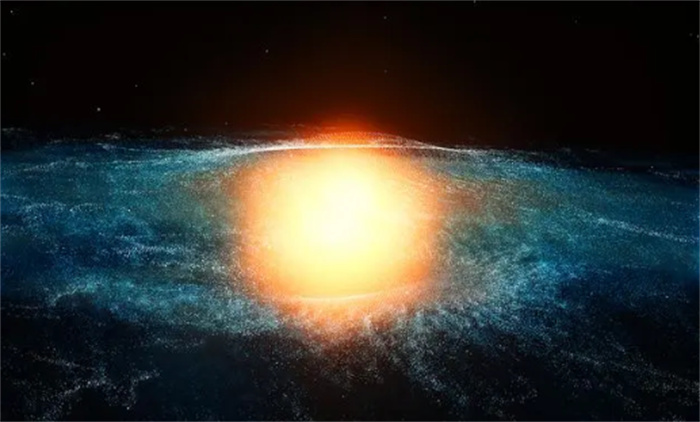李学勤:疑古思潮与重构古史
一
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来总结、回顾二十世纪的疑古思潮,确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我个人来说,我想首先应该强调,要充分估计疑古思潮所起的进步的、正面的作用,估价它的重要贡献。大家看我出了本书,叫《走出疑古时代》,但并没有意思要抹杀疑古思潮的进步,我在文章里首先就是肯定疑古思潮的进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在二十世纪,实际上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开始出现一种对于中国传统的古史观进行怀疑和批评的态度,这完全是进步的。从我们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冲决网罗,打倒偶像,在当时起了一个解放思想的重大作用。
当然也有学者们指出,说这个是不是顾先生受外国的影响?因为我个人是比较仔细地读过顾先生的日记。当然早期日记不太全了,可是我敢说,因为我有特别的机会把顾先生的日记差不多整个读过一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说顾先生并非是这样的。顾先生日常不太看国外书,他主要是继承了宋清以来的辨伪思潮,与当时新的思想相结合,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新的想法的。可是我必须要说一下,因为有人提到,我们的古史辨派受到日本的白鸟库吉、法国的马伯乐的影响。是不是这样的呢?当然,他们之间是有共同点的,特别像白鸟库吉,他的著名的说法就是“尧舜禹抹杀论”,这就很像顾先生他们的一些论点了。我认为,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从日本的史学史上来看,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当然,白鸟库吉后来的一些东西,我们是很不敢苟同的,后来他讲满蒙,为当时的日本政治起了相当的服务作用,不管主观上怎么讲,它是起了相当的作用。可是,“尧舜禹抹杀论”从日本的思想史、学术史上来看,应该说还是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那时日本的情况和我们差不多,白鸟库吉的观点提出后,就在当时引起一场争论。站在他的对立面和他争论的,是日本当时最有权威的汉学家,即以林泰辅为代表的那些。大家知道林泰辅的文集叫做《支那古代之研究》。林泰辅这一家日本发音是特别的,它是念“はゃし”,“はゃし”这个“林”在日本是研究中国《诗》《书》的一个世家。林已奈夫也属一家,但他比较远一点,不好说他是不是和林泰辅有直接关系。可是林泰辅是直接的,他们这一派在日本是极有根基的。所以在我看起来,就和我们中国的情况一样,一派是从当时的思想史来看,作出了巨大贡献;另外一派是对于考证历史史实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看林泰辅的那些书,看他和王国维的讨论,都可以了解一些。
二
第二直到今天,疑古思潮对我们整个学术界还影响特别大。而且我特别要说,不但在我们今天国内的学术界还有相当的影响,对于海外、国际上的汉学界影响更大。你看一些外国人,如果你跟他谈起疑古思潮的论点,他一定非常高兴,非常兴奋。你要是相反呢,他一定大不高兴!而且最后他就提出来了:“你们中国人是不是不想做文献研究了?”他们叫"text criticism",“你们是不是不做text criticism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疑古思潮的产生和欧洲的"text criticism"的产生是类似的。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学术界对过去的传统观点进行了批判,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从而出现了一个学科,叫"text criticism",用我们国家的说法叫做文献学。"criticism"就是批判,我们因为“文革”批判多了,所以今天听起来太刺耳。"text criticism"就是文献批判,影响实在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些方面,不可不估计整个国际的学术背景。
三
大家都非常熟悉冯友兰先生在《古史辨》第六册序言里面提出的那个三段论说法,叫做“信古、疑古、释古”的三段论。冯先生因为是我的老师,他的书我也是读的,我自己觉得他提的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可是现在大家对信古、疑古、释古的解释跟冯先生有点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个人建议我们还是读读原文。
就此而言,这个“古史辨”、“古史辨派”的说法,就有点不太合适。顾先生本人就不赞成说“古史辨派”。为什么呢?因为《古史辨》是一个讨论集,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派的集子,而是有多种观点的。而且顾先生本人,历史所的人都知道,我和顾先生关系极好,我和顾先生住街坊,并是邻居,我们一起住了十几年,并有很多请教,知道他的情况,他的思想。他是不愿意跟人家说是古史辨派的,因为正如刚才说的《古史辨》是多种观点组成的。
就顾先生本人而言,他胸怀极其宽广,特别能够包容,所以只要有反对他的文章,他首先要推荐发表。钱穆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是反对康有为一直包括到崔觯甫崔适和顾先生这一派最激烈的。这个稿子送到北京来,当时顾颉刚先生在燕京大学,便将这个稿子拿到《燕京大学学报》上发表。钱宾四先生之所以能够到北京来当教授,就是因为这个,完全是顾先生的推荐。顾先生的这种气度、海量,我认为是今人不可及的。所以在顾先生的纪念会(指1993年召开的“顾颉刚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我就讲了这一点,顾先生当然有他自己的看法,可是他不反对反对他的人。他不但不压制,而且推荐、保举反对他的人。我看这个真是不可及!是我们后辈、晚辈所不可及的。
为什么我要说这个话呢?因为在古史辨派最盛行的时候,王国维先生就有批评。这一点因为过去大家不太清楚,不太清楚的原因,就是由于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那个讲义《古史新证》流传太少了。虽然书有过赵斐云赵万里先生影印的一个本子,玻璃版的,可是当时一共印了100本,除了极个别人,没有人看过。现在清华大学已经把这本书重新出版了,人们可以看到他对古史辨的批评,我们也可以印证他的几位学生是怎么转述他对古史辨的批评。以我个人的妄断,揣测王国维先生所以取名叫《古史新证》,也跟《古史辨》之名有关。这是我个人的揣测。因为你叫《古史辨》,我就叫《新证》,正好是一个补充。不过这是后辈的揣测,未必可靠。
但我个人认为,这个不一致是相辅相成的。王国维先生对于古史辨的成绩,在《古史新证》里也是给予充分肯定的。另一方面,现在从《顾颉刚先生年谱》可知,王国维之所以能够进清华,也是顾先生的推荐。这件事我们谁也不知道,因为过去都知道王国维进清华是胡适推荐的,由胡适来推荐王国维是比较合适的。顾颉刚先生当时是晚辈,很年轻,居然能给胡适写信推荐,那真是宽宏大量。我们可以看到顾先生的风度。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对疑古思潮有什么议论,如果顾先生在世的话,我想他也不会太见怪的。
这里已经谈了《古史辨》与《古史新证》,我想还有一个应该提的口号,就是“古史重建”,它是现代考古学最早的奠基人李济先生提出来的。李济先生在美国哈佛是学体质人类学的,可是他回来以后实际上做考古。他是我国第一个真正开始进行科学发掘工作的中国人,那是1926年,在夏县西阴村。我们现在从材料看,他和王国维先生是有合作的。他刚从西阴村发掘出的材料,王国维先生就来看了,然后他们进行了很多讨论。对之,他的弟子,还有当时的材料记载,都非常明确。李济先生,在几年以后这段时间里面,也就是他刚到中央研究院来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的时候,就提出来了我们要“重建古史”。
他写了好几篇文章,一直到50年代,他还写了文章,1954年发表了《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他所谓“重建古史”,在我今天看起来的话,他的思想就是以考古学为主来重建中国的上古史。所以最后,在他的倡议之下,台湾出了一套《中国上古史》,大家看到那本书了,有四大本。《中国上古史》待定稿第一卷就是李济先生主编的。
关于古史重建,它的基本思想就是用考古学来重建历史。这个思想在我看,正好是由于疑古思潮的结果。因为疑古思潮对于那些文献的东西已经否定得差不多了,所以现在主要可依据的就是考古学。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和古史辨派、《古史新证》是相辅相成的。所以,看到这一点以后,我就想起夏鼐先生在文章里写的一句话,他说疑古这一派为考古在中国的发展开了路。因为大家以前不觉得考古重要,因为中国的古器太多了,中国的古史是现成的,要你们考古干什么?所以是疑古思潮为考古学开了路。当然,王国维先生的《古史新证》,以其“二重证据法”,从理论和方法上为现代考古学奠定了基础。
四
最后一点,我要说的就很简单了。现在大家都说已经看到二十一世纪的曙光了,我们这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听了就觉得可怕。可是时间是不能阻挡的。那么,在现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对于过去一段二十世纪学术史,应该进行总结和评价,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从新的材料、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高度,站在新的历史背景之下,整个学术史确实有重写的必要。重写学术史应该特别包括续写和新写二十世纪的学术史。像胡适先生、顾颉刚先生、钱穆先生等等上一代的学者,他们的著作都有研究清代学术史的部分。梁启超从1923年,在南开和清华就讲《清代学术概论》,后来又有一本书叫做《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当时做这个,因为处在清末民初、二十世纪的开始,就有总结前一段学术的必要。我们今天不能像他们那样再去把重点放在清代,因为清代离我们已经远了。清代讨论的一些问题,什么今古文这一类的问题,离我们比较远,那是上一代的事。跟我们最接近的是二十世纪学术史。而今天提出来的关于疑古思潮回顾的问题当然应该是二十世纪学术史里的一个中心问题。
来源:《中国文化》
1960年代,杜甫墓被挖开后发现了什么?人骨呢?
杜甫墓被挖开后本文作者倪方六在古代诗人中,葬地有争议的不少,其中杜甫死后到底埋葬在哪?争议最大。我曾在“梧桐树下戏凤凰”头条号中,谈过杜甫葬地湖南与河南之争。从各地反映来看,“杜甫墓”目前至少8处,分布在湖南、河南、陕西、四川4个省,即在湖南耒阳、平江、湖北襄阳、河南偃师、巩县、陕西华阴、鄜县和四川成都,当地都有一座杜甫墓。我要新鲜事2023-05-26 15:39:460000云南考古:古滇国考古重大突破:实证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历史进程
我要新鲜事2023-05-27 21:31:090000男子挖自家的祖坟 最后被判死刑(私自盗墓)
男子挖祖坟把文物卖到黑市最后被判死刑。西安蓝田的吕富平整天游手好闲,当他得知自家祖坟里头埋着一位北宋时期的宰相以后,便想着自己先人能当上宰相,那他的墓里头一定埋着金银珠宝或者宋朝的瓷器,这要是能从先人的阴宅里头搞点值钱的玩意儿,那下半辈子基本上就可以天天游山玩水,吃山珍海味了。私自盗墓我要新鲜事2023-12-17 11:16:280000秦始皇墓穴中的神秘人 仅仅出现了四次(墓穴神秘人)
秦始皇墓穴里的“神秘人”是一个绿色的兵马俑。1974年,兵马俑一经问世,就引爆全球,被评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此后世界各地的游客也都纷纷慕名前来观赏,并且毫不吝啬的发出赞美之声。毕竟这些兵马俑的形象呢与气质多是栩栩如生,神奇的是他们神态各异,就像真人站在你眼前一样。绿色兵马俑我要新鲜事2023-03-23 19:56:180000史上最“敬业”的盗墓贼 居然挖了20年(盗墓贼)
盗墓贼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违法工作。可能有很多人在看过《盗墓笔记》或者是《鬼吹灯》之后想着自己是不是也能够通过盗墓的方式赚一些钱,不过大多数人因为害怕或者是没有毅力,尝试了一下就放弃了,更多人是因为知道盗墓是一个违法的工作。可是在前些年真的出现过一个十分敬业的盗墓贼,甚至在这旁边住了20年。敬业的盗墓贼我要新鲜事2023-05-11 07:51:34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