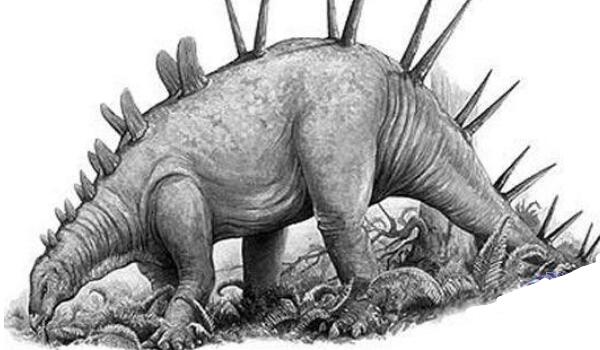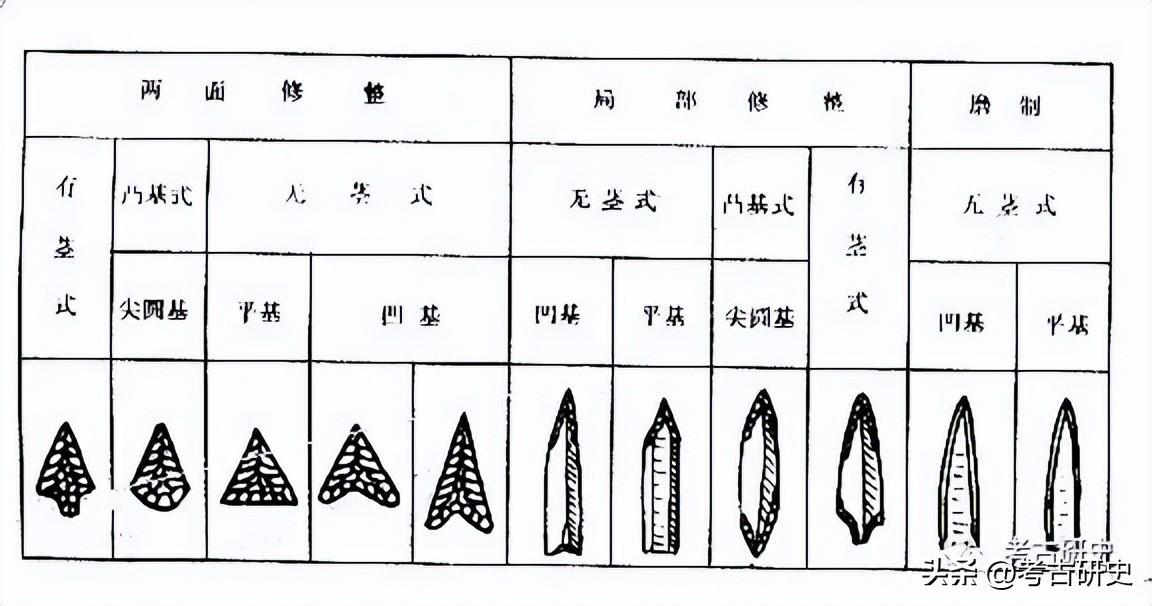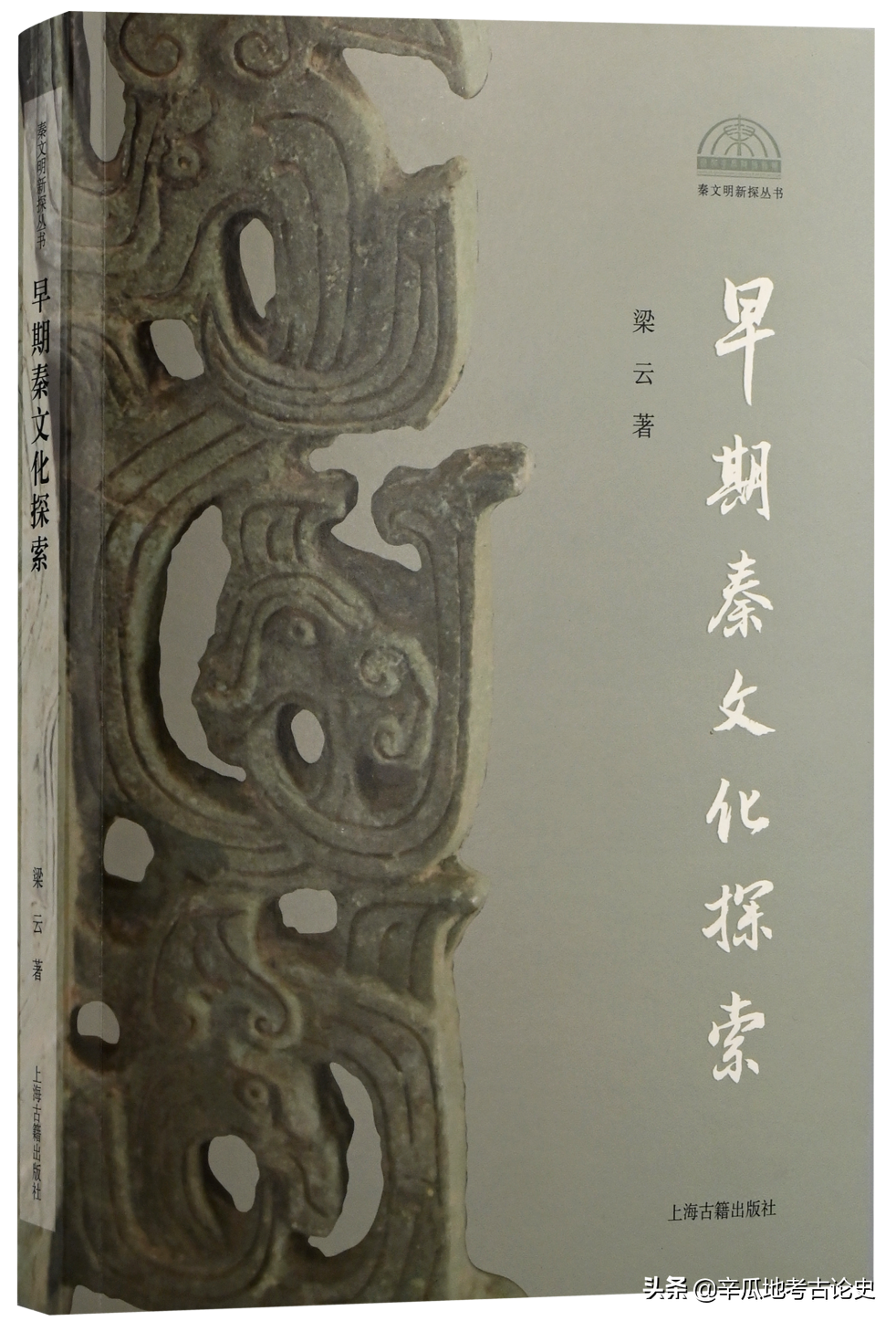黄剑华: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关系
一
轰动世界的三星堆考古发现,为我们揭示了古蜀文化的灿烂辉煌。三星堆古蜀文明具有自身的鲜明特色,学术界对此已作了许多深入的探讨。而三星堆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以及周边其他区域文明的关系,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我们知道,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由于古代“内诸夏而外夷狄”观念的影响,自上古以来即盛行中原王朝为正统,他们很长时期都将中原视作惟一的文明中心。随着考古新发现提供的丰富资料日益增多,中华文明起源呈现为满天星斗多元一体的格局,已为学术界所公认。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文明的起源,恰似满天星斗。虽然,各地、各民族跨入文明门槛的步伐有先有后,同步或不同步,但都以自己特有的文明组成,丰富了中华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注:童明康:《进一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苏秉琦关于辽西考古新发现的谈话》,《史学情报》1987年第1期。)。三星堆考古发现便为中华文明起源多元论提供了重要佐证,揭示了古蜀国就是长江上游的一个重要文明中心。诚如隗瀛涛先生所说:三星堆遗址内发现的三四千年前的一大堆令人叹为观止的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以青铜雕像群为代表的古蜀文物,以及古城墙、古祭祀礼仪中心残迹等,“证明了三四千年前的川西平原已具有了可以同殷商中原文明媲美的高度发达的奴隶制文明形态,并进而使人们再一次地确认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化特点。三星堆文明无疑是辉煌的,举世瞩目的,是古蜀先民的一大杰作,是中华文明的一大骄傲”(注:隗瀛涛:《一项填补空白的工作——三星堆文化序》,《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苏秉琦先生也曾精辟地指出:“四川盆地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广汉等地出土的陶片“说明在成都和广汉各有着不少于五千年的文化根基。三星堆两个大祭祀坑以及后来1986年在成都十二桥所发现的三千多年前的跨度12米的四根地梁所显现的规模宏大的建筑遗存,都使我们确认,四川盆地不仅有着源远流长的自成一系的古文化,而且在三四千年前,这里已有了既同中原夏商文化有明显联系,又独具特征、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并毫无疑问已处于方国时代”。苏秉琦先生同时提出了“按照考古学文化渊源、特征与发展道路的差异,把中国分为面向欧亚大陆的三区和面向太平洋的三区”,以建立中国考古文化发展的体系结构,“即在六大文化区系范围内可以涵盖为大致平衡又不平衡的多源一体的格局”的观点。他强调:“中国国家的多源一体的格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是经过超百万年,特别是近万年以来多区系文化的交汇、撞击、相互影响作用的结果,是中华民族祖先各族群无数次组合与重组、团聚的结果,是文化逐渐认同、经济逐渐融合的结果”(注:苏秉琦:《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244页、245页、249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这些论述对我们深入认识和正确评价古蜀文明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大格局中的地位,以及古蜀文明与其他区系文明相互之间的交流影响,是有重要启发意义的。
古蜀文明具有自成一系的鲜明特色,与中原文明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或差异,不仅表现在礼仪制度、观念习俗、宗族或部族构成、社会生活、艺术情趣等诸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农业生产方式上。中原是旱地农业起源的核心地区,中国南方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应该说,正是由于史前时期就形成了南北两种农业体系,从而促进和形成了南北文化体系发展的各自特色。古蜀文明作为南方文化系统长江上游的一个重要文明中心,虽然与中原文明有着许多明显的不同,同时又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从考古资料看,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密切关系,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影响,都是源远流长的。上古时期已有黄帝和蜀山氏联姻的记述,夏禹治水曾多次往返于岷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尚书·禹贡》对此有较多的记载,有学者提出了夏禹文化西兴东渐的见解。考古资料也揭示了三星堆遗址第二期所出器物与中原二里头文化之间的关系,“两者均出陶盉、觚、器盖、豆、罐类器物,都是以小平底为主。尤其是陶盉,二者极为相似……联系到陶盉起源于山东,向中原传播的事实,以及二里头文化早期略早于三星堆二期的情况,不难确定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因此在文化上呈现了一些相同的因素。但若据此便认为前者渊源于后者,则嫌证据不足”(注:范勇:《试论早蜀文化的渊源及族属》,《三星堆与巴蜀文化》18~19页,巴蜀书社,1993年。)。邹衡先生也指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盉同二里头的陶盉,“除了陶质和大小以外,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它肯定是从二里头文化传来的,因为别的地方没有”。“又如陶豆,基本上也同二里头文化的一样。现在所见到的三星堆陶豆,其形制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早期……不过三星堆的陶豆较大,要比二里头的陶豆大三倍到四倍。但是从它的特征来看,应该也是从二里头文化传来的。”“第三件最重要的陶器是‘将军盔’,即熔铜的坩锅。它是与铜器有关系的。在三星堆看到的‘将军盔’,从它的样子来看同殷墟第一期的非常相似,但也有区别。”还有“三星堆铜罍同湖北宜都发现的同类铜罍销有区别,而同陕西城固的铜罍几乎没有区别,连花纹的作风都一样。但是它同殷墟的铜罍多少有些不同,当然其时代同‘将军盔’的时代还应该是一致的”(注:邹衡:《三星堆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四川考古论文集》57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这些都说明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源远流长,特别是在夏商时期关系密切。
三星堆出土器物中,如果说陶盉陶豆是接受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那么铜尊铜罍则显示出受到了殷商青铜礼器的影响。这起码说明两点:一是古蜀与中原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在夏代甚至更早就开始了,二是这种文化传播和交流在殷商时期变得更加密切了。正如俞伟超先生所说:“从总体看,三星堆的遗存,主要是相当于商时期的。其中的两个祭祀坑,则是相当于殷墟阶段的。这时期的蜀文化,已接受了大量商文化的影响。在青铜工艺方面,最突出的是有大量商式戈与商式的罍和尊”。这展现了在造型艺术和青铜铸造工艺方面,具有高超水平的古代蜀人对商文化中青铜礼器的模仿,而这种模仿主要是仿造罍和尊,其他礼器极难见到,说明这是有所保留和有选择的模仿,是不失主体的一种文化交流。俞伟超先生进而指出:“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是分别位于成都平原至川东及三峡一带的两支青铜文化,但其文化面貌有很多相似之处,因而又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大文化圈(区),自夏时期起,这个文化圈内开始渗入了一些二里头文化的因素,而至商时期,则又大量接受了二里冈和殷墟文化的影响。这就是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在我国考古学文化总谱系中的位置”(注:俞伟超:《三星堆文化在我国文化总谱系中的位置、地望及其土地崇拜》,《四川考古论文集》61页、62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可谓是很有见地的看法。
二
古蜀与中原的关系,特别是古蜀王国与夏商周三代的关系,历来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古籍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是比较少的,自从甲骨文大量出土之后,这方面可供研究的资料才多起来。晋代常璩《华阳国志》卷十二说:“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老彭’。则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孔子所述,见《论语·述而篇》。关于老彭,《世本》中有“在商为藏史”之说,《大戴礼记》卷九亦有“商老彭”之称。顾颉刚先生指出:“老彭是蜀人而仕于商,可以推想蜀人在商朝做官的一定不止他一个。古代的史官是知识的总汇,不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应当都懂。蜀人而作王朝的史官,可见蜀中文化的高超。古书里提到蜀和商发生关系的,似乎只有《华阳国志》这一句话。可是近来就不然了。自从甲骨文出土,人们见到了商代的最正确的史料,在这里边不但发见了‘蜀’字,而且发现了商和蜀的关系。”顾颉刚先生还提到了综合各种记载,“可知古代的巴蜀和中原的王朝关系何等密切”(注: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19页、3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当然,记载中有不少是传说,也有附会。但甲骨文提供的则是翔实而可信的资料。
关于甲骨文中的蜀,学者们也有争论,其分歧主要是蜀的地理位置究竟在哪里。陈梦家先生认为“见于卜辞者有蜀、羌、微、濮四国,皆殷之敌国。当时地望已无可考,大约皆在殷之西北、西南,决不若今日之远处边陲也”(注:陈梦家:《殷代地理小记》,《禹贡》第7卷第6、7期合刊,北平禹贡学会,1937年。)。后又释蜀为旬,认为在晋西南“古城在今(山西)新绛西”(注: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295页,中华书局,1988年。)。胡厚宣先生认为蜀在鲁“自今之(山东)泰安南至汶上皆蜀疆土”(注:胡厚宣:《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甲骨学商史论丛》第2集(1944年)。)。董作宾先生认为蜀“约当今之陕南或四川境”(注:董作宾:《殷代的羌与蜀》,《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1942年)。)。日本学者岛邦男认为蜀“在河曲西南”,约在今陕西东南商县、洛南附近(注:〔日〕邦岛男:《殷墟卜辞研究》374~383页,台北鼎文书局,1975年。)。郭沫若先生认为蜀“乃殷西北方之敌”(注:郭沫若:《卜辞通纂》,《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2卷453页,科学出版社,1983年。)。邓少琴先生认为“殷墟卜辞蜀有人方之称”,而卜辞中的“伐羌蜀”(铁1053)“挞缶于(与)蜀”(后上·9·7),可知“羌为羌方,在殷之西,蜀在羌之南,缶应即褒,缶之南是为蜀国,殷之出征,先羌而后蜀,先缶以及于蜀,应无疑义”(注: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130页、15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段渝先生也认为确定殷卜辞中蜀的地望,“关键在于确定卜辞中与蜀相关的一系列方国的地望。与蜀同在一辞的,有羌、缶等方国。羌为西羌,古今无异词”。“缶,应即文献中的褒。古无轻唇音,读褒为缶。褒即夏代褒姒之国,地在汉中盆地故褒城。卜辞记‘伐缶与蜀’(《粹》1175),又记‘缶眔蜀受年’(《乙》6423),显然两国地相毗邻。缶既在陕南,则蜀亦当在此,殆无疑义。但陕南之蜀并非独立方国,它是成都平原蜀国的北疆重镇,故亦称蜀。”(注: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44~4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
除了殷墟卜辞中有许多蜀的记述外,在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辞中也有蜀字,学者们对此也有不同看法。李伯谦先生认为蜀“在汉水上游,只是在西周时期,才转移到成都平原”(注:李伯谦:《城固铜器群与早期蜀文化》,《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李学勤先生认为周原卜辞中的蜀也在鲁地(注:李学勤:《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文物》1981年第9期。),这同胡厚宣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林向先生指出,关于蜀在鲁地的说法,“清人朱右曾《逸周书集校释》即倡此说。《左传》宣公十八年杜预注‘蜀,鲁地,泰山博县西北有蜀亭’,《嘉庆一统志》:‘蜀亭在泰安县西’,说明今之山东确有地名蜀亭者。至于说‘南至汶上,皆蜀之疆土’,主要根据《嘉庆一统志》说‘汶上县西南四十里有蜀山,其下即蜀山湖’。其实不然,汶上有蜀山是因蜀有‘一’、‘独’之古训而得名,与蜀人之国无涉”。林向先生认为,“蜀非自称,也非一族,只是商周王及其卜人集团对这一大片‘华阳之地’的称呼。近年来,成都平原发现的一系列商代遗存,其中以广汉三星堆遗址最重要,为我们进一步标定蜀的地理位置,提供了新的证据。现在可以这样说:殷墟卜辞中的‘蜀’的中心地区在成都平原,蜀文化圈的范围大体上和后来《汉书·地理志》所载与‘巴蜀同俗’的地域相当,它在江汉地区与南传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相遇,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在渭滨与周文化相遇,蜀应该是殷商的西土外服方国”,之后“蜀作为西土诸侯参加周的灭殷联盟,取得了成功,是周初西南方国中的强者”,成为周初西南强国(注:林向:《巴蜀文化新论》85~86页、57~58页、69页,成都出版社,1995年。)。
上述的这些争论,显示了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对深入探讨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关系是大有益处的。随着考古新发现提供的丰富资料日益增多,有些长期争论悬而未决的问题已经迎刃而解,许多历史疑问都逐渐获得了破译,学术探讨也不断深化有了许多新的收获。虽然对殷墟卜辞和周原卜辞中的蜀仍有不同解释,但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的古蜀文明,以其鲜明的特色和丰富的内涵,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认识。
殷商时期的古蜀王国,不仅在三星堆建立了雄伟的都城,而且有着同中原一样灿烂而又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在长江上游成都平原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辉煌的文明中心。作为这样一个文明中心,古蜀与中原一直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有着文化上的交流和经济上的往来。但古蜀与中原这种关系究竟属于什么性质?是相互隶属还是相对独立?前面提到林向先生认为古蜀应是殷商的西土外服方国,还有学者曾认为蜀文化是受商文化传播影响发展起来的,这代表了以前学术界比较流行的一种看法。但也有另一种认识,段渝先生就认为:“从卜辞看,蜀与殷王朝和战不定,是国际关系,而不是方国与共主的关系”,“卜辞对蜀绝不称方。而卜辞所见之蜀,均在蜀之北疆重镇陕南地,不是蜀的中央王朝。可见蜀王不是殷代外服方伯,蜀国并未成为殷王朝的外服方国。考古资料可以得出同样结论……按照商王朝的内、外服制度和匠人营国之制,王都必定大于方国之都,故卜辞屡称商都为‘大邑商’……但蜀都却大于早商都城,又与中商都城不相上下。如将蜀国纳入商代外服体制,显然是严重逾制,在当时根本无法想象。只能表明蜀国都制与商王朝都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政权体系,二者之间不存在权力大小的区别”(注: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46~47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这些分析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是很有见地的一种观点。三是堆青铜造像群所展现的浓郁的古蜀特色,在王权与神权方面自成体系的象征含义,对此也是一个很好的印证。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青铜罍等形制,玉石器中的璋、戈等形制,都显示出对商文化的模仿,反映了商文化对蜀文化的影响,说明了这是古蜀与中原经济文化交往的结果。值得强调的是,古蜀与中原文化交流是不丧失主体的交流。三星堆出土器物告诉我们,在接受商文化影响的时候,以高超的青铜雕像造型艺术为代表的古蜀文化特色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应是我们客观认识和正确评价古蜀文明和殷商文明相互交流影响的关键所在。
三
三星堆古蜀文明与中原殷商文明之间的交往,可能有水陆两途,而顺长江上下则是一条主要途径。徐中舒先生曾指出:“古代四川的交通有栈道和索桥,并不如想象的困难,而且长江由三峡顺流东下,更不能限制习惯于水居民族的来往。”考古出土资料显示“至迟在殷商的末期,四川与中原地区就已经有紧密的联系了”。“从黑陶遗物陶鬶、陶豆出土地址的分布,可以清楚地看出古代四川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其主要道路应是沿江上下的。”(注:徐中舒:《论巴蜀文化》3~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李学勤先生通过对出土青铜器物的比较研究,也认为“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化向南推进,经淮至江,越过洞庭湖,又溯江穿入蜀地。这很可能是商文化通往成都平原的一条主要途径”(注:李学勤:《商文化怎样传入四川》,《中国文物报》1989年7月21日。)。他指出:“蜀是一个发端于上古的民族。这一民族有自己的悠久文化,并长期保持着文化的特色。”蜀人原居于四川西部山区,其后,才发展到成都平原一带。很多人以为蜀地僻远,交通封闭,长期与中原不通,甚至怀疑随武王伐纣的蜀国的地理方位。现代考古学的发现已足以纠正这种误解,有充分证据表明,在商代及其以前,蜀地已与中原有文化上的沟通。广汉三星堆的发掘,更以大量材料印证了这一点。“从三星堆器物坑的发现看,商代的蜀不仅有自己的礼乐,而且受到中原礼乐的强烈影响。”“至于商代的荆楚,即今湖北、湖南间的地区,更与蜀地有较密切的文化关系。三星堆不少青铜器和两湖所出类同,是很好的证据。”(注:李学勤:《帝系传说与蜀文化》,《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6~17页。)他还说:三星堆“一号坑相当商文化的殷墟早期,二号坑相当殷墟晚期,是互相一致的。这说明当地的文化(蜀文化)发展是与商文化的发展平行的,彼此的影响传播是畅通的”。三星堆两座器物坑中与中原所出近似的青铜礼器,是当地文化接受中原影响的证据。不过,这种影响不是直接传入当地的,其媒介应该是今湖北、湖南地区当时的文化。三星堆礼器的饕餮纹,最接近于湖北、湖南所发现,指示我们这种媒介作用的存在。有的纹饰则反映出有可能是接受由东而来的影响,又加以本地的创造。同出的别的器物上,还有纯属地方特色的纹饰。“这样中原与地方特点骈列杂陈的状态,反映着蜀与中原王朝的沟通。总的说来,蜀文化是有自身的渊源,自身的演变的。在接受了长期的中原和其他地区的文化影响之后,才逐渐融会到全国的文化进程中去”(注:李学勤:《三星堆饕餮纹的分析》,《三星堆与巴蜀文化》79页,巴蜀书社,1993年。)。这些精辟的见解,已经把问题说得相当透彻了,对我们深入探讨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关系是大有益处的。
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流经由汉中之地,陇蜀之间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途径。西周初武王伐纣,联合西土八国会师牧野,古蜀国人马就是由这条途径参与征伐行动的。在开明王朝开凿石牛道之前,古蜀国北面的交通显然早就存在了,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资料都为此提供了印证,古代蜀人使用栈道的历史可能远比见诸文字记载的要久远。扬雄《蜀王本纪》中有“蜀王从万余人东猎褒谷”(注:《全汉文》卷53。)的记述,这种大规模的行动也是对这种交通情形的一个说明。《华阳国志·蜀志》中说杜宇时期“以褒斜为前门”,开明三世卢帝“攻秦至雍”。褒斜即褒谷与斜谷,在汉中之北的秦岭山脉,雍城则在秦岭之北的宝鸡(注: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9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或说在今陕西凤翔县南(注:刘琳:《华阳国志校注》186页注文,巴蜀书社,1984年。),都说明了古蜀国北面的交通状况。
褒斜道早在商代即已开通,在商周之际开通的可能还有故道,因其沿嘉陵江东源故道水河谷行进而得名。《散氏盘》铭文中有“周道”。据王国维先生考证,“周道即周道谷,大沽者,即漾水注之故道”(注: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8,第3册887页,中华书局,1959年。)。邓少琴先生指出,“是则蜀当夏殷周之世均与中原有其交通之迹也”,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记,“是时雍蜀之间已有商业之发展。下至石牛道之开凿,以蜀绕资用,南御滇僰,西近邛笮,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注:邓少琴:《巴蜀史迹探原》15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从考古发现看,陕西成固出土的铜器物群中,即有属于殷商文化的器物,如鼎、尊、罍、瓿、簋、戈、钺等;又有属于早蜀文化的器物,如青铜面具、铺首形器,以及陶器中的尖底罐等。“由于三星堆文化同类器都早于或等于成固铜器群的年代”,“说明陕南乃是商与蜀接壤,两种文化交错共存的边缘地区。就蜀而言陕南乃其北境,就商而言陕南则为其西土也”(注:林向:《巴蜀文化新论》67页,成都出版社,1995年。)。前面提到邹衡先生指出三星堆出土的铜罍与城固出土的铜罍在器形和纹饰上都相似,显然便是两种文化交流的结果。
古蜀文明通过陕南接受了殷商文明的传播,仿造了中原礼器中的铜尊与铜罍,同时也使古蜀文明在与殷商文明接壤的地方产生了影响,留下了富于古蜀文明特色的遗存。在陕西宝鸡地区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等处发掘出土的一批西周时期

国墓地,呈现出一种复合的文化面貌,学者们认为有三种文化因素并存:“居址和墓地的出土遗物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揭示出商周时期传统的周文化同西南地区早期蜀文化、西北地区寺洼文化(主要是安国文化类型)的有机联系,展现出一幅五彩缤纷的历史画面。毫无疑问,这对于研究当时的民族关系、文化交流与融合都具有重要意义”(注:卢连成、胡智生:《宝鸡

国墓地》上册6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参见下册彩版二三。)。
值得注意的是茹家庄一、二号墓出土的青铜人,那夸张的握成环形的巨大双手,完全继承了三星堆青铜立人像双手造型的风格。这对商周时期蜀文化的影响应是一个绝好的说明。林向先生认为:“

国文化中明显占优势的早蜀文化因素是不能单用外部传播来解释的,必然是与蜀人势力直接抵达渭滨,蜀文化圈在此与周文化圈相重叠有关。”(注:林向:《巴蜀文化新论》71页,成都出版社,1995年。)段渝先生认为:“从各种文化现象分析,

氏文化是古蜀人沿嘉陵江向北发展的一支,是古蜀国在渭水上游的一个拓殖点。”(注:段渝:《嫘祖文化研究(之四)》,《成都文物》1998年第2期。)展示了“古蜀文化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和辐射性”(注: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三星堆文化》60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四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中原与各区系文化的关系和影响,苏秉琦先生曾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资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之后,目前全国还有五十六个民族,在史前时期,部落和部族的数目一定更多。他们在各自活动的地域内,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是可以理解的。”(注: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苏秉琦考古学论文选集》226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三星堆考古发现等大量材料提示的辉煌的古蜀文明,以及古蜀文明和中原文明的交流与影响,便是很好的例证。从三星堆出土遗物总体来看,以青铜造像群为代表的文化主题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展现出自成一系的浓郁的本土特色,同时又显示出许多外来文化因素,但外来文化影响只居于次要地位,而且在模仿过程中大都有新的发挥。这应该是古代蜀人既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的长处,又对本土文化的优越充满自信的表现。
这里还应该提到的是,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模仿商文化的礼器,数量较少,只有龙虎尊、羊首牺尊、铜瓿、铜盘等。二号坑出土的礼器种类和数量都大为增多,据发掘报告介绍的就有圆尊8件、圆尊残片3件、方尊残片1件、圆罍5件、圆罍残片2件、方罍1件等。据一些学者研究,一号坑与二号坑的时代相差100年左右。一号坑相当于殷墟早期,二号坑相当于殷墟晚期。这是否说明,随着历名的发展,古蜀文化与殷商文化的交流也比以前增多了。如果我们再结合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青铜器物来看,中原商周文化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强烈了。这显示的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统发展的历史趋势。蜀文化正是在这个历史发展趋势中,逐渐融合到了全国统一的文明进程中去。但在三星堆时期,古蜀王国灿烂的青铜文明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鲜明特色,显示出其国势足以与中原殷商王朝相抗衡。蜀与商是相互独立同时又有着较为密切的文化与经济交流,是分属于南北两个文化系统的文明中心。
在古蜀王国和殷商王朝的关系方面,还应提到青铜文化的比较研究。我们知道,纹饰是青铜器物的一种语言,通常表达着器物的文化性质和特点。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三星堆出土青铜容器在形制、纹饰、工艺等方面与长江中游和陕南等地出土青铜器的相似之外。例如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龙虎尊,与安徽阜南朱砦润河出土的一件龙虎尊在造型和花纹上几乎一模一样。二号坑出土的四羊罍在纹饰上接近于殷墟三期的一例,在形制上与湖南岳阳鲂鱼山、湖北沙市东岳山出土的两件类似。还有二号坑出土的四牛尊、三羊尊与湖南华容、湖北枣阳新店村、陕西城固苏村等处出土的几件相似,等等(注:参见李学勤:《三星堆饕餮纹的分析》,《三星堆与巴蜀文化》76~79页,巴蜀书社,1993年。)。通过这些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三星堆青铜容器罍、尊之类在器形和纹饰上与殷商青铜器风格的许多一致之处,同时也有不少差异。有学者认为,三星堆“铜罍的肩、腹、圈足部都装饰有凸弦纹、饕餮纹和云雷纹。尊的腹部饰有羽状云雷纹,圈足上饰有云缧纹组成的饕餮纹,并开十字形镂孔,这些都是殷商青铜器的常见特征。尽管它们与典型的殷商青铜器还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区别(如圆尊的圈足改外侈为内收、纹饰的排列方式不完全一致等),但很可能是在蜀地产生的一种以继承殷商传统为主体的地方变体”(注:霍巍:《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西亚文明》,《四川文物》1989年“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38页。)。随着这方面比较研究的深入,将会有更加透彻的了解。
总之,古蜀王国与殷商王朝的关系和文化交流,应该给予客观的恰如其分的认识。古蜀文化接受商文化的影响,主要来自湖北、湖南、江西等长江中游以及陕南地区。正如有的学者所述,古蜀与殷商的文化或民族的往来“到三星堆文化的晚期,也就是两个祭祀坑的时代,交流只有一定的限度,文化主体还是本土的,外来占极次要的地位,而且受长江中游的影响远比黄河流域深”。殷商崇尚礼容器,发展出一套繁复的系统,在全世界青铜文明中是绝无仅有的。古蜀王国也同样重视青铜,同样有礼容器,可是礼容器在整个资源运用系统的角色中只扮演次要的角色而已。宏观地看,古蜀所赋予青铜的意义与商王朝及其军事或文化势力所及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则相当不同,这里出土的青铜器,最主要的是大量的人形像和面具,“这是蜀国青铜最具自己特色,也是与东方最大不同的地方”(注:杜正胜:《人间神国——三星堆古蜀文明巡礼》37~38页,台湾太平洋文化基金会,1999年。)。
三星堆出土器物与殷商青铜器的比较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正是三星堆文化与殷商文化各自所具有的鲜明特色,展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南北两个文化系统的绚丽多彩。随着相互间的交流融合,它们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谱写了青铜时代杰出而又辉煌的篇章。
来源:《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
嘉陵龙:四川小型食草恐龙(长4米/距今1.5亿年前)
说到恐龙,食肉的总是备受关注,其中又以霸王龙、棘龙等为最。为了丰富大家的恐龙知识,小编今天为大家介绍一种小型食草恐龙,它就是嘉陵龙,出土于中国四川,一起去认识看看。嘉陵龙基本资料嘉陵龙是一种中国的小型食草恐龙,它体长4米,与匈牙利龙、天镇龙差不多大,体型在已知774种恐龙中赞排第413位,生活在距今1.63亿-1.5亿年前的中侏罗世。嘉陵龙化石我要新鲜事2023-05-09 01:54:340000魏斐德:史景迁的学术之路:从温彻斯特学院到《追寻现代中国》
编者按:按照惯例,我们会委托熟悉杰斐逊讲座学者成就的人写一篇新文章,即所谓“赞辞”。今年的讲师史景迁建议我们转载他的老朋友和同事,已故的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史杰出教授魏斐德(FredericE.WakemanJr.)的这篇讲话。这篇演讲是在2004年发表的,当时史景迁成为美国历史协会的主席。他于2008年从全职教学中退休。这个版本经过了简单的编辑。我要新鲜事2023-05-31 21:01:530000梁云:早期秦文化探索
#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早期秦文化是两周考古的一大重大课题,而与这一课题有关的礼县大堡子山、清水县李崖遗址、甘谷毛家坪遗址、张家川马家塬西戎墓地都是当年入选年度十大考古的热门项目!在对这些遗址和早期秦文化的研究方面,西北大的梁云先生是这方面的佼佼者!我要新鲜事2023-05-29 13:15:380000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揭晓!20个项目入围终评
2月26日,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揭晓!根据投票结果,得票数前20位的项目入围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围终评项目名单(以时代早晚为序)1四川稻城皮洛遗址2山西夏县师村遗址3甘肃张家川圪垯川遗址4河南南阳黄山遗址5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6浙江余姚施岙遗址7山东滕州岗上遗址8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我要新鲜事2023-05-07 05:49:04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