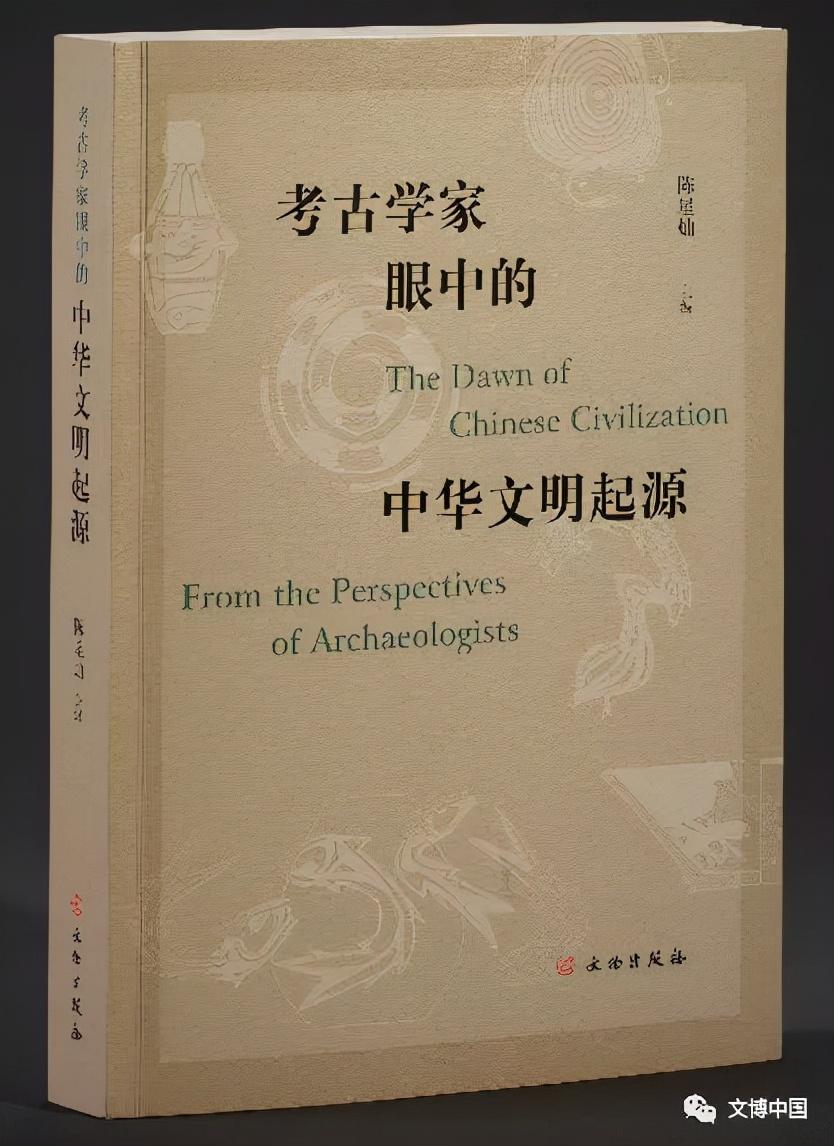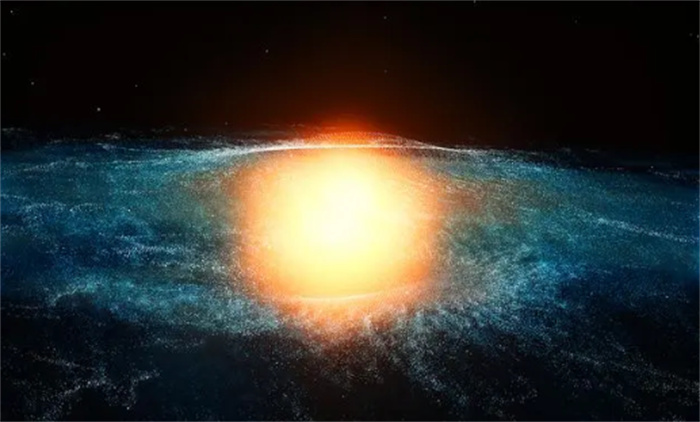董楚平:汉代的吴越文化
过去,研究吴越文化,人们都把精力集中于先秦时期,那只是狭义的吴越文化。广义的吴越文化,应包括古今。作为广义的吴越文化,汉代是文化转型的关键阶段,非着力研究不可。
先秦时期的吴越文化,虽受华夏文化的深度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夷越文化,是中国诸少数民族文化中最发达的一支。汉代的吴越文化,则是中国主流文化——汉族文化的一个区域型。吴越文化的这一转型过程,开始于楚威王败越,剧变于秦皇、汉武时期。这段时期,吴越地区的越人大量入海南奔,楚人与中原人先后进入吴越,由于主导人口与基本居民发生变换,使吴越文化的民族性随之激变。文化转型的趋向是由西向东、由北向南依次展开的。到西汉中后期,皖南、宁镇、太湖平原、宁绍平原已基本汉化。到六朝时期,浙江南部地区也由北向南渐次完成汉化。
一 中原人入主吴越
公元前222年,秦灭越。次年,秦统一中国,分全国为36郡。吴越地区设会稽与鄣二郡。会稽郡所在吴县(今苏州),辖境约当苏南太湖流域、浙江省仙霞岭、牛头山、天台山以北和安徽水阳江流域以东及新安江、率水流域之地,西汉时曾扩大到福建全省。鄣郡治所在浙江安吉西北,故城犹在,辖境约当苏南大茅山以西至皖南新安江以北之地。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将鄣郡更名为丹阳郡,治所在宛陵(今安徽宣城)。
各郡县官员基本上都由中原人担任。中原人南下取代了楚人、越人的统治地位。例如后来的东吴四大姓之一的吴县陆氏家族,原为中原世族,西汉时陆烈被委任为吴县令,子孙发展成为“江东大族”。东汉的陆续、陆康、陆绩,东吴第三任丞相陆逊及其孙陆机、陆云,皆为吴县陆氏家族中的名人。
东汉时山阴名人郑弘,其祖父本是齐国临淄望族,汉武帝徙强宗大姓,不准族居,他只得将第三个儿子移居山阴,遂发展成为会稽大姓。
文化名人王充,祖籍魏郡元城(今河北省大名市境),远祖从军有功,西汉时封于山阴阳亭(今绍兴市境)。
秦汉以后,越族后裔成为吴越大姓者,恐怕只有顾氏。郑樵《通志·氏族略二》说:“顾氏,己姓,伯爵,夏商之诸侯,今濮州范县东南二十八里有故顾城,是其地也,子孙以国为氏。又《顾氏谱》云:‘越王勾践七代孙闽君摇,汉封东瓯摇,别封其子为顾余侯。汉初居会稽,亦为顾氏。’”顾氏有南北二支,根源则一。因为夏代的己姓有南方越人的血统,[1]夏越本同源。吴郡顾氏也是东吴四大姓之一,顾雍在东吴任丞相19年,任职时间最长。其祖先顾综,东汉明帝时人,曾任御史大夫、尚书令。西晋灭吴后,陆机、陆云与顾雍之孙顾荣同入洛阳,被当时人称为“三俊”。八王之乱时,二陆身亡,顾荣返吴。晋室南渡后,吴郡顾氏与陆氏是东晋初年“王与马共天下”的重要支持者。至南朝四代,吴郡顾氏仍显赫不衰。
进入吴越的中原人,除士人、官吏、军队外,还有大量下层贫民。如西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汉书·武帝纪》)。据王鸣盛估计,这次迁入会稽郡的关东贫民,约为14万5千人(《十七史商榷》卷9),以填补越人迁出后留下的空白。
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都实行“强干弱枝”政策,迁天下豪富强族于京师,关中片面繁荣,东南落后停滞。《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自

、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西汉末年,群雄并起,基本上以士族大姓为主。余英时长篇论文《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列有《两汉之际各地豪杰起事表》[2],共列起事武装88支,起事地点88处,大多在黄河流域,陕西、河南、山东因经济发达,大姓林立,所以起事最为频繁,武装最为密集。长江流域的武装起事,自四川、湘北,最东止于安徽庐江与江西南昌(豫章)。淮河流域的武装起事最南止于临淮(江苏盱眙)。会稽郡未占一支。这说明到西汉末年,太湖与钱塘江流域人烟还很稀少,士族势力薄弱。这种情况,使太湖、钱塘江流域在两汉之际的战乱年代,成为中原人士的一个避难处所。
二 东汉时期的初步发展与进一步汉化
东汉更始元年(公元23年),任命任延为会稽都尉。《后汉书·循吏列传·任延》云:“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
王充《论衡·自纪篇》记建武十年(公元34年),他八岁就学时,“书馆小僮百人以上”。会稽教育已颇发达。
这些都是东汉初年情况。
到永建四年(公元129年),东汉政府将会稽郡分为吴郡与会稽郡。吴郡治所在吴县(今苏州),辖境约当苏南太湖流域、浙江长兴、吴兴、天目山以东,建德以下的钱塘江两岸。会稽郡治所在山阴(今绍兴),辖浙江以东之地。太湖、钱塘江流域由一郡分为二郡,说明到东汉时期,这里的人口增加了。
《汉书》为吴越地区人物立传者,仅严助、朱买臣、郑吉三人,严与朱都是太湖平原的吴人,郑吉是会稽人。《后汉书》为吴越地区人物立传者,有23人,其中,钱塘江以南有14人,主要集中在山阴、上虞、余姚一线。
到东汉时期,太湖、钱塘江流域不再是“无千金之家”的荒凉之地。
从西汉到东汉,吴越地区人口是增加了,但增加得并不很快。西汉时期,太湖、钱塘江地区称会稽郡,有223038户,1032604人。[3]东汉时期,这里分为吴郡与会稽郡,其中吴郡有164164户,700782人;会稽郡有123090户,481196人。[4]两郡合计共有287254户,1181978人。经历200多年的和平发展,只增加64216户,149374人。户的增长率是28.3%,人口的增长率是14.5%。这200多年的吴越地区情况与中原地区完全不同,中原遭战争严重破坏,人口外流;吴越地区和平发展,人口内流。经200多年的和平发展,人口只增长14.5%,除去原有户口的自然增长数,外来的户口不会很多。
查现有东汉资料,没有发现像西汉武帝元狩四年那样,由政府组织迁徙中原贫民充实吴越地区的记录。因为这时中原户口大减,急需充实。
上引《后汉书·任延列传》说:“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这条资料说明,两汉之际确有中原士人避乱会稽,但待中土安定之后,这些中原士人,尤其是其中的中上层分子还是要返“还中土”的。留下来的大多是下层人民。因为当时的吴越地区条件尚差,对中原中上层士人缺乏吸引力。
查东汉时期吴郡与会稽郡的名人大姓,基本上是西汉时期或西汉以前已经住在吴越地区。《后汉书》列传所列23人,没有一个是西汉末年避难而来的。
没有写入《后汉书》列传的富春孙氏,是“孙武之后”,[5]可算是最早进入吴越的华夏家族之一。中原孙氏是春秋时期陈国公子完的后裔。公元前672年,陈完因内乱逃奔齐国,后改称田完。陈、田古字通。孙武的祖父田书,因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孙武带着《兵书》13篇来到吴国,公元前512年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帮助吴军破楚入郢。“武生明,字景浩,以父功食采于富春,遂为富春孙氏。”[6]
西汉末年因世乱而进入吴越的北方士人,后又留居吴越而成为南方土著士族者,当然有,但不多。查正史资料,北方士人因避难来吴越,最后留下的,似乎只见一人。《晋书·儒林列传》记载:“范平,字子安,吴郡钱塘人,其先铚侯馥,避王莽之乱适吴,因家焉。”在地方史志中还可以找到一些类似资料,例如,嘉泰《吴兴志》卷16以及唐元和年间《吴兴丘氏碑》记载:乌程丘氏,本是齐鲁世族,丘俊持节安抚江淮,因王莽篡权,遂留江南,居乌程。子孙繁衍,成为吴兴郡一大显族,汉魏六朝出了不少人才。[7]
总之,太湖、钱塘江地区的种族大换班,到西汉中期已基本完成。东汉时期的户口增加,文化进步,基本上属本地区的自然增长与自身发展,主要不是依靠外来人口与外来文化的大规模涌入,这一点与后来的六朝时期根本不同。
以上说的是太湖、钱塘江地区。浙江南部地区开发很慢,只在西汉时增设一个回浦县(今临海),东汉时增设一个永宁县(今温州)。三国时,许靖致曹操书,说自己曾离开会稽,“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三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三国志·蜀书·许靖传》)其言可能过甚,不过,会稽郡虽辖有浙南、福建,汉人可能只住在县治附近,广大乡野,尚为越人天下。到永嘉之乱、晋室南渡后,这种情况才基本改观。
除浙南以外,还有个“山越”问题。“山越”是江东地区未被政府控制的山野居民的泛称,其民族成分,越人可能居多,主要聚居于今皖、浙、赣三省交界的山区。秦汉时期,中原汉人入主吴会平原,越人遁入西部山区,没有对汉人构成威胁。到三国时期,孙吴建都建业(今南京),丹阳郡一带的山越就成为心腹之患,也是西取荆州的第一块绊脚石,故势在必除。孙策时,江东山越较大的割据势力已全被孙氏所击溃,剩下的是依山阻险,抵抗孙氏的豪强武装。孙权加速步伐,“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三国志·吴主传》),侧重在丹阳、豫章、庐陵、会稽、鄱阳诸郡交界一带。[8]孙策、孙权每镇抚一地,即建郡县以治之,并编入军队。如讨平黟、歙一带的山越后,分黟、歙之地,以六县为新都郡,派名将贺齐坐镇其地。这是浙西、皖南开发史上的大事。
山越大多是古越人的后裔,两汉时期就已存在,到东吴时期,因对汉人政权构成威胁,而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孙吴政权讨平山越,设县管辖,编入军队,使山越迅速汉化。
三 文化转型
人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到西汉中期,太湖、钱塘江流域已基本实现种族大换班,主要居民与主导民族已由汉族取代越族,该地区的文化面貌也就为之大变,即汉文化取代了越文化。
越文化在考古学文化上的主要标志印纹陶,从此在该地区完全消失。古越族的特有乐器勾鑃也在该地区悄然隐退,而大量出现于广州的南越王墓中。“断发文身”等古越人的习俗也不再见诸载籍。除了这些以外,文化转型主要还表现于以下四个方面。
1 汉语代替越语
文化的民族性主要体现于语言上。先秦时期,长江下游分属于吴、越二国。公元前473年,越灭吴,长江下游尽归越国。吴越二国的基本居民是越族人和越化的东夷人,民间语言基本上是古越语。古越语属古侗台语,与中原、楚国的华夏语不同。楚国境内也有越人,他们是楚国的少数民族,而在吴越二国,越人是主要民族。
吴国王室是周族后裔,应该能说华夏语,但入境随俗,其名字都有古越语特征,应该同时能操古越语。犹满清皇族入关后,既能说满话,又学会说汉语。越国王室是夏族后裔,从山东迁来。而夏王室与南方越族本有血缘关系。“先是‘禹为越后’,然后是‘越为禹后’”。[1]
古越语的人名、地名甚具特色,首字多为勾、姑、无、夫、余、诸等。勾字古属侯韵,姑、夫、无、余、诸皆属鱼韵。侯韵与鱼韵是邻韵,古可旁转,通假之例甚多。“四千多年前,良渚文化北迁,给中原的夏族注入大量南方古越族成分。夏与越古音都属鱼韵。一世夏王‘禹’、七世夏王‘予’,以及六世夏王少康之少子‘无余’,也属鱼韵字。十一世夏王名‘不降’;后来的越王人名中有‘不寿’、‘不扬’。‘不’也是古越语发音之一。‘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娄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祀’(《史记·陈杞世家》)。娄是地名,是夏裔居地。娄古侯韵,与勾同部。《春秋经》襄公六年:‘杞伯姑容卒。’姑容更明显是古越语人名。”[9]
由于越国王室与古越族有如此根深蒂固的关系,所以越国王室比吴国王室更富有越文化特色。
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大败越”后,楚人开始自西而东、自北而南进入“故吴地”。楚人给吴越地区带来最初的华夏语影响。楚语是华夏语的南方方言,后来的吴语,有楚方言基础,时至现代,吴语与老湘语还有许多共同之处。
秦代与西汉时期,中原人大量入主吴越,华夏语成为吴越地区的官方语言,并逐渐深入民间。但古越语在民间仍残留相当时间。西汉晚期扬雄著《方言》,所记吴越方言主要是侗台语词汇。
吴越地区的华夏语,经东汉至西晋的三四百年演变,形成一种汉语方言:“吴语”。《世说新语·排调》记载:“刘真长(惔)始见王丞相(导),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惟闻作吴语耳。’”《南齐书·王敬则传》载:“敬则名位虽达,不以富贵自遇。危拱傍遑,略不衿裾。接士庶皆吴语,而殷勤周悉。”
这些“吴语”皆指当时吴地的汉语方言,与南下的北方士人所操官话略异。但都属华夏语(汉语),与先秦吴越“夷言”根本不同。
《左传》哀公十二年,卫出公被禁于吴,获释后,“卫侯归,效夷言。”西晋杜预注云:“夷言,吴语。”谨按,杜注欠确。《左传》“夷言”指的是先秦古越语。杜预是西晋人,当时所说的“吴语”,指吴地的汉语方言。古越语(“夷言”)与“吴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两者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吴越春秋》记载不少所谓吴越时期的诗歌,用的是汉语,文从字顺,毫无古越语痕迹。这些诗歌是汉代人创作,好比现代人编古代历史剧。
秦汉以后,见于载籍的吴会地区人名,已不见勾践、夫差、者旨於赐、不寿等古越语痕迹。但是古越语的地名仍保留下来,姑苏、无锡、芜湖、句(音勾)容、余杭、於潜、诸暨等,沿用至今。南方的柚子本是古越人栽种的水果,现在,浙江、福建、台湾以及西南地区的汉人称柚为“抛”,“抛”是古越语遗存。吴语有古越语的零星遗存,但就整体而言,它已是汉语的方言,而不是古越语的嬗变延续。
总之,秦汉以后的吴越文化,其民族性发生根本变化,文化的基本形态由越族文化变为汉族文化,语言由越语变为汉语。
2 由尚武变为崇文
《汉书·地理志下》说:“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这段话常被人们称引,说汉代的吴越民风仍与东周一样,尚武骁悍;并据此认为,直到永嘉之乱,北方士人大量南渡,才一举改变吴越文化的尚武特点。此说不但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与人类学、民族学原理相悖。
评说吴越文化的特征,应以吴、会平原为准。例如,上引《汉书·地理志》评说先秦的吴越风习,就以身居吴、会平原的“吴、粤之君”为其代表。说汉代的吴越风习,也应以吴、会平原为准,否则就没有可比性。此其一;其次,在时间段上,应以民族大换班基本完成以后,即西汉中后期、尤其是东汉时期为准。查古代文献资料,在这样的时间段与这样的地理范围内,很难发现吴越之民还“好勇”如前、“轻死易发”的事实。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吴越地区几乎是唯一的净土。东汉末年,唯勾章人许昌起事,当年即被孙坚削平。此后,孙坚并没有在“轻死易发”(?)的故土聚众割据,而是北上角逐。《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注引吴书云:“后雄杰并起,中州扰乱,肃乃命其属曰:‘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宁肯相随俱至乐土,以观时变乎?’其属皆从命。”试想:“其民”“轻死易发”的地方,怎能一再成为乱世中的“乐土”?
文献资料与田野考古表明,吴越地区的冶金业,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以剑等兵哭最为精致,到了汉代,则以铜镜为代表。西汉的丹阳郡,东汉的吴郡与会稽郡,是全国铜镜的著名产地,质量居全国前列。剑是凶器,镜是美容器具,冶金业的代表性产品由剑变为镜,从一个侧面反映吴越文化的特点已由尚武变为崇文。《汉书·地理志》说汉代的吴越之民仍“喜用剑”,而田野考古表明,吴越地区所出的汉代铁剑并不比别处多,也不比别处精,与东周时期的吴越铜剑根本无法攀比。班固恐怕是“刻舟求剑”,以旧成见窥测新形势,其言有失据之嫌。
3 文学与子学
转型后的吴越文化是汉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它与其它地区的汉文化比较,一开始就显示出自己的特点,下面以西汉的文学与东汉的子学为例,略见其端倪。
西汉初,见于正史的吴越士人,仅有严忌一人。忌本姓庄,《汉书》为避东汉明帝之讳而改为严。据《汉书·邹阳传》记载,严忌与邹阳、枚乘“皆以文辩著名”。初依吴王刘濞,后来,刘濞与景帝矛盾激化,他们三人北上投靠梁孝王。东汉王逸编撰的《楚辞章句》一书,有严忌《哀时命》一篇,这是今天所能看到的汉代吴越第一篇文学作品。
汉武帝时,会稽郡有严助、朱买臣位列九卿。据《汉书》本传记载,严助与朱买臣都是“吴人”。据《汉书·严助传》云,吴人严葱奇也得武帝“亲幸”。
上述四人,皆长于辞赋。《汉书·艺文志》记载:“庄夫子(严忌)赋二十四篇”、“常侍郎庄葱奇赋十一篇、庄助赋三十五篇、朱买臣赋三篇”。《汉书·地理志》说:“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他们在经学方面成就不显,《汉书·艺文志》仅记有“《庄助》四篇”,归为“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
吴越士人,西汉时期以辞赋见称于世,东汉时期,则以子学最为所重。
卢云先生根据东汉时期各地区所出的书籍种数、《后汉书》列传人数,以及五经博士、三公九卿、从事私家教授者的籍贯分布,这五类数字,制成“东汉时代的文化发达区域”图。[10]与“豫兖青徐司地区”、“三辅地区”、“巴蜀地区”相比,吴会地区经学书籍所占比例最小,而子学书籍比例特大,占到52%。吴会地区的子学著作不但数量特大,而且质量特高,汉代最重要的子学著作莫过于王充的《论衡》,它就出在吴会地区。
4 养生与隐逸
吴越地区远离国家的政治中心,战争较少,又有长江、钱塘江等天然屏障,是隔岸观火的好地方。这里土地肥美,气候宜人,只要家有薄产,可以静心做你的学问,玩你的艺术与科技。因此,经学不显,子学发达,文艺与科技人才特多,是此后二千年间吴越文化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在汉代就已显露出来。这样的地理环境,也是修身养生、藏匿隐士的理想地方。
古代最复杂的养生术莫如炼丹术。世界炼丹史上第一部理论著作《周易参同契》就产生于东汉时期会稽上虞人魏伯阳之手。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负盛名的炼丹家兼医药学家几乎全出于吴越地区。
“光武无寸土,子陵有钓台”。汉代最著名的拂袖高蹈的大隐士严子陵就出在东汉初年的吴越。《后汉书·逸民列传》记载:“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披羊裘钓泽中。”刘秀三番五次派人把他拉到洛阳,他还是不肯做官。刘秀与他“共卧”,他竟敢把腿压在皇帝老兄的肚子上。最后,皇帝屈服了,放他回家,“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今子陵钓台距江面约70米,使人有“放长线钓大鱼”之感。不过从钓台仰望,高山插云,俯瞰大江,春水融融。身临其境,确能喜忧俱忘,宠辱不惊。遥思之陵当年,垂钓处一定贴近江面,一定是后人把钓台越筑越高。看来,钓台的确比帝座牢固、永久,富春江更比洛阳城清静得多,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此后,吴越地区一直是“逸民”、高僧的天堂。每当北方游牧民族血洗中原时,这里尤其成为红尘中的一片绿荫。这片绿荫在东汉时就已长成,并不是永嘉之乱以后北方难民从血海中移植过来。
“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主要人生道路。这使他们失去独立的人格。要想人格独立,必须生活独立。吴越地区的文人生活独立的可能性较大,这使他们可能不学或少学直接为“帝王家”服务的经学,而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过自己喜欢过的生活,像《儒林外史》所描写的那样。《儒林外史》正是产生在吴越地区。从严子陵到《儒林外史》,一条非主流的文人生活道路,两千年不绝如缕,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吴越文化的一个特点。
参考文献:
[1]董楚平.夏王朝的苗蛮血缘[A].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37-243.[3]班固.汉书·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4]范晔.后汉书·郡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5.[5]陈寿.孙破虏讨逆传[A].三国志·吴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6]张维明.试谈新发现的《姚江孙氏世谱纪略》[A].吴地文化一万年[C].北京:中华书局.1994.129.[7]王志邦.吴兴郡与吴兴大族的文化现象[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38.[8]王志邦.六朝江东史论[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3.[9]董楚平.防风氏的历史与神话[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58-59.[10]卢云.东汉时期的文化区域与文化重心[A].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4辑[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158.
来源:《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1期
一名纺织女工是如何靠脸蛋迷住皇帝,继而上位的?一般女人学不来
原题:孙吴九大皇家陵墓之孙亮墓——疑遭鸩杀迁葬江宽赖乡本文作者倪方六政治权力争夺是残酷无情的,兄弟反目,君臣失和。三国时的吴国为什么在孙权死后,很快就出现衰败迹象?就是因为皇室问题太多,权臣弄权,为君不君,致政治权力起伏不定。这篇文章就来聊聊孙和被废后,继任者孙亮为什么也会被毒杀。我要新鲜事2023-05-27 14:36:590000NBA全明星赛编年史1994:鲨鱼票王,蝙蝠侠MVP
1994年全明星赛在明尼苏达的明尼阿波利斯举办,由于迈克尔-乔丹宣布退役,缺席了1994年的全明星赛,票王落到了沙奎尔-奥尼尔头上。我要新鲜事2023-05-31 22:17:27000170吨重的黄河铁牛捞出后 为何露天摆放不保护 考古专家 不敢动
文物是人类历史的见证和遗产,保护文物也是考古工作中的重要任务之一。文物的保护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其中最基本的就是控制温度和湿度。不过,有些文物竟然能够放在露天,被风吹日晒都不需要担心损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要新鲜事2023-05-13 03:44:140000荐书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
内容简介《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目录前言陈星灿我要新鲜事2023-05-07 08:29:560000皇帝陵墓中有一最神秘的地方,不能见光,非常隐秘,一般动不得
神秘的金井本文作者倪方六光绪皇帝陵墓被盗一事,发生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虽然是一伙不明身份的人,但从盗掘手段上分析,他们并非生手,盗墓经验丰富。但蹊跷的是,盗墓者将光绪皇帝与隆裕皇后的棺椁翻了个遍,甚至将光绪皇帝的棺材头凿了一个大洞,连尸体都拖了出来,但棺材下面的金井却没有动,这对经验丰富的盗墓者来说,太低级了!为什么,因为帝王陵金井内必有镇穴之宝!我要新鲜事2023-05-26 17:26:1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