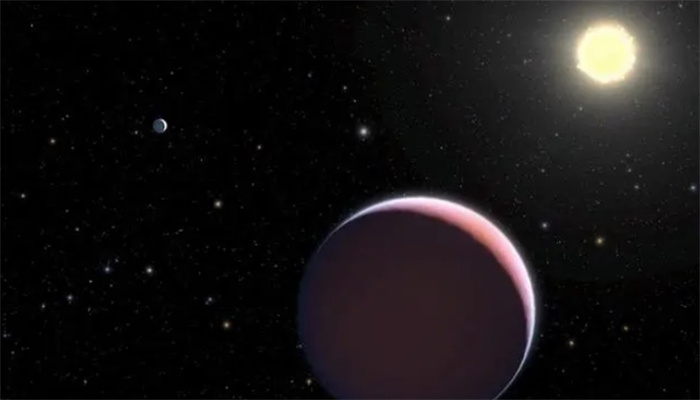周振鹤: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两汉风俗区划的变迁
一
我在《秦汉风俗地理区划》(载《历史地理》第十三辑)一文中,根据各地的风俗地域差异,将西汉各郡国分为三大风俗地域。这三大风俗地域的根本差异如果用更简单的话来说,大概可以归结为以下内容:黄河中下游地域是华夏风俗,塞上边郡是以华风为基础而习染胡俗,南方大体上还是偏向蛮夷风俗。换句话说,在南方基本上还有大量少数民族风俗的存留。《汉书·地理志》所表现的绚丽多采的风俗面貌,主要是中原地区华夏风俗内部的差异,而边郡之间的风俗差异并不特别突出,至于淮汉以南地区直到西汉后期还未有深入全面的了解,故其内部差异不显著。西汉后期起,移风易俗的过程次第展开,但这一过程主要是对中原地区有较大作用;对于南方只在个别地区如蜀地引起反响,大部分地区还未有大的变化,至于北边诸郡,大体上无大变化。东汉时期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移风易俗过程更加速进行,于是中原地区的风俗渐渐趋向一致,华风内部的地域差异逐步化解消除,南方蛮夷则渐次向华风演变,边郡风俗也有较大的移变。至东汉后期,虽不能说风俗地域差异已经不存,但如果说华夏风俗从表面上看来已在东汉各郡国中占了上风,风俗区域的界线已经相对模糊,却是大致不误的。换句话说,对于东汉后期,我们已经不能勾勒出如西汉后期那样明显的“九州异俗”的风俗地理区划来,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续汉书·郡国志》没有留下一篇如《汉书·地理志》那样的风俗资料,另一方面也的确表明其时在表面上已有“六合同风”的现象。
至于说到南方少数民族的全面华夏化或汉化,则是长达二千年的历史过程,并不是二三百年就能发生根本变迁的。尤其在南方的许多地区,中央政府的统治也是逐渐深入的,在政治上的统治尚未深入之时,风俗文化的变迁是微乎其微的。举一例言之,就在湖南地区,湘西的南北江蛮是直到北宋时期才真正有效地在中央政府的直接治理之下。因此所谓蛮夷风在南方也就一直长期存在,并且还使中原地区南移的华风受到蛮化,产生与中原地区有所不同的新的风俗样式。
中原地区所居为诸夏,诸夏周边民族泛称为夷狄戎蛮。这些称呼不但原本无大的贬斥意味,例如夷是人持弓的象形,并非贬义字。蛮虽有带虫字,但在古人看来,虫是动物的总称(如老虎是大虫,蛇是长虫),人也是虫,裸虫也。狄虽为犬旁,但狗可以是图腾,这在古代是很平常的事(后来发展至少数民族的名称都用犬旁,则是明显的歧视)。不但如此,诸夏也是逐步形成的族群,初与夷狄并无绝对的界限,所以孟子才说,舜是东夷之人,周文王是西夷之人,而这两人都是诸夏视为一等圣贤的人物。至于蛮夷自己也不认为就矮人一头,楚国不讳言是蛮夷之邦,赵佗据岭南自立,也自称为蛮夷大长老。所以所谓蛮夷风实是指与诸夏风习不同的另一类民族风俗而已。春秋以后,严夷夏之大防,而且诸夏在政治经济力量上逐渐占了优势,才在文化上有改造夷风的要求和可能。当春秋初年,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如线的时候,正不知南风压倒北风还是北风压倒南风,是不会有以华风同化夷风的提法的。齐桓、晋文以后,诸夏在中原地区牢牢立定了脚根,这以后才能进而改造夷俗,提出用夏变夷的口号。秦就是以夷狄而入中国的,秦风也就进而成为华风的一部分,而睥睨起南方的蛮夷之风了。进入两汉以后,华风自然处于正宗的地位,所谓蛮夷风就成为与中原地区风俗相对立的文化现象,也成为必须改造的对象。因为生产方式的先进,与地理环境的相对优越(在当时而言),使得中原地区的文化样式也有优于南方民族的地方,如礼制婚俗就比群婚、对偶婚先进。但应该看到中原夏人也有许多不好的风俗,如虚诈无情,夸奢朋党之类。因此华风并不一定比蛮夷风一概优越,但问题恰在于:在以华风同化蛮夷之风时,既把好风俗也把坏风俗都带到诸夏以外的地区了。例如上述拙文就提到朝鲜地区风俗因为辽东吏人的卑劣而由淳朴变为浇薄。再者蜀地本有蛮夷风,不好学,文翁提倡好学以后,虽提高了认识水平,但也产生了好文刺讥的新毛病。因此本文的所谓华风与蛮夷风的对立,纯粹是以夏人(直到隋代,仍称中原地区居民为夏人,而不是汉人)的视角来看华风的传播,而并非认为华风必然地优越于蛮夷之风。
文化的地域差异是任何时代都存在的,但在不同时代分异程度有所不同。有些时代各地文化要素显示强烈的差异,而有些时代却表现出较强的同一性。风俗作为文化的一个分支,也经常出现同一性与分异性的变迁反复。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因诸侯国各自为政,各地之间的风俗面貌存在不小的歧异,但由于各国之间会盟朝聘,来往频繁,加上战争冲突连绵不断,遂引起文化的交流,使西周年间各诸侯国相互隔绝的情况被打破,风俗的变迁也随之而起。据卢云研究,以婚姻形态而言,《汉书·地理志》中所说的燕地“宾客相过,以妇侍宿”以至“嫁娶之夕,男女无别”,齐地的长女不嫁,赵、中山之女“遍诸侯之后宫”,郑、卫男女亟聚会,分别是借妻婚以至杂婚的变形,对偶婚的象征,奔婚的样式,以及自由恋爱的表现。这些婚俗一开始并非只局限于上述这些地区,而是有较普遍的分布范围。只是后来由于礼制婚姻形态的广泛传播,使得这些古老的婚姻形态在大部分地区渐渐趋于消失,而残留在个别地区(其中有些比较偏远,如燕、齐)之中(见《汉晋文化地理研究》)。这种情况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风俗由旧的同一(非礼制)到新的同一(礼制)过渡的中途,由于新的同一过程尚未普及于整个王朝全境,于是就出现了异采纷呈的风俗地域差异面貌。西汉后期,以及整个东汉时期,礼制婚姻的传播比较迅速,新的同一过程在地域方面不断扩大,上述燕、齐、赵中山及郑卫的特殊婚俗就不再现了。如果说在西汉后期,由于非礼制婚姻形态在各地的残留,在中原地区形成了不同的婚姻风俗区,那么在东汉末年,这种婚俗的地域差异在中原地区就基本上不存在了。这个例子说明风俗区是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变迁的。
二
从先秦秦汉时期的发展看来,风俗的同一化过程不断地推进,《汉书·地理志》所反映的风俗地域差异恰好是大规模风俗变迁的前奏,到东汉末年地域差异已经相当程度地减弱,不再呈现西汉后期那种“八方殊风”的风俗马赛克图景,而表现出近似于“九州共贯,六合同风”的面貌。待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的风俗地域差异又出现,形成南北两大板块之间的差异。本文先来分析两汉之际的变化,而把六朝时期的变化放到另文去处理。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在文化方面做了两件大事,一是车同轨,二是书同文。前者是物质文化统一的标志,后者是非物质文化统一的象征。但是这两方面的统一远未彻底,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统一,更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事。所以当时并未提出行同伦的口号,因为行——即行为文化难于在短时间内取得融合。在非物质文化中只有制度文化是容易统一的。而宗教信仰、风俗等精神文化以及各地方言都是不能骤然同一化的。时至今日,仍然如此,就是明证。精神文化不但不能骤然统一,有时还得承认暂时无法统一的既成事实。秦始皇在称帝后,多次出巡全国各地,主要是宣威性质,表示他是东方六国旧地的新主人,但在同时又有不得不在文化方面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例如,在东方的齐地,秦始皇礼拜齐人的八神,表示承认齐地的信仰为秦代所继承。但在南方的会稽郡却又立石,表明要革除当地的恶俗。会稽刻石,在婚姻方面有“有子而嫁,肯死不贞”,“妻为逃嫁,子不得母”的条文,这是要求女方保持贞节,但同时也有“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的规定,保障妇女的权益,原宥她们杀死通奸的丈夫。
整齐风俗的做法自秦未一统天下时已经存在,秦简《语书》曰:“古者,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是以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僻,除其恶俗。……凡法律令者,以教道民,去其淫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于为善也。”所谓恶俗就是不利于国家稳定、社会安定的习俗与风气,包括热衷商贾,不务本业,包括奢靡之风、淫僻通奸,甚至包括刚武、尚气力等(这一习俗容易引起各种刑事犯罪)。去除恶俗的办法,是教民遵守法令。《韩非子·五蠹》云:“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这就是秦国的教化方式,其目的就是整齐风俗,维持社会秩序,保持社会安定。这个目的是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要做到的。但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并不尽相同。先秦的其他国家,如齐、如鲁,或尊以贤智,或教以礼义,各有不同。即使秦国以法为教的方针也是商鞅变法以后才完全确定下来的。这个方针由秦代至西汉中期相沿不替,只是在汉初被黄老之术掩盖了。
汉初的首要急务是与民休息,增加生产,保持社会安定,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就行。而无为之治恰恰是最上乘的选择。所以当时政府的政策数十年不变,对丞相而言是萧规曹随,对皇帝来说是垂拱而治。文景之治靠的是黄老之术,这不但是文帝之所好,也是景帝时掌有实权的窦太后的治国法宝,直到窦太皇太后死,汉武帝亲政,才有所更张。汉武帝虽然表面上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但实际上还是重视法治。尤其重视能以文法办事,而又能饰以儒术的人。如对公孙弘,“上察其行慎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说之,一岁中至左内史。”(《汉书·公孙弘传》)“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郡下。”(《黄霸传》)“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上”,“不堪从儒术,任用法律”(《元帝纪》)。甚至上溯至文景之时,也并不忽视法治。《汉书·儒林传》说:“孝文本好刑名之言”,景帝末文翁任蜀郡太守时,也是“教民读书法令”,既鼓励吏民子弟入学,又派人到长安学习法令,并不像后人所认为的那样纯用儒术干政。
无为而治当然对风俗的改变不起什么作用,以法为教,主要也是在去除恶俗,保证安定,虽然对于整齐风俗有所促进,但与有意识地,大规模地移风易俗有根本的差别。只有儒家是以风俗的同一化为己任的。但在汉宣帝以前,儒家的指导思想始终没有占据统治地位。直到西汉中期,统治者对于各地风俗文化面貌的差异并不急于改变,也无太多的余裕去作改变。虽然《汉书·儒林传》说:“至于文景,移风易俗”,那只不过是一个标志,表明有些地方官开始注意到这一工作而已。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各地风俗多采异相的情况,一直保留到西汉后期,以至汉宣帝时,据当时大臣王吉所言还是“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甚至于“户异政,人殊服”的“八方殊风”的风俗景观。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以王吉为代表的具有儒家思想的官员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移风易俗的教化工作,以期在整个西汉王朝造成“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局面(《王吉传》)。而这一建议正好因为宣帝时期重视吏治,使地方官在自己的辖区内可以大有作为而取得有效成果,更由于元帝以后重视儒术而使移风易俗过程侧重于(但不是全部)在儒家的指导思想下进行。
于是在西汉后期,如武帝时卧治东海的无为太守已经不见,代之而起的不是以儒就是用法。典型的地方官如韩延年与黄霸,两人先后为颍川太守,一用儒术,一明法令,都使颍川得到大治,并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汉书·韩延寿传》载其出身为郡文学,“上礼义,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贤士,以礼待用,广谋议,纳谏争,举行丧让财,表孝弟有行,修治学官,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隆揖让;及都试讲武,设斧钺旌旗,习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赋租,先明布告其曰,以期会为大事,吏民敬畏趋向之。又置正五长,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奸人。闾里仟佰有非常,吏辄闻知,奸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烦。后吏无追捕之苦,民无楚之忧,皆便安之。……其纳善听谏,皆此类也。”
黄霸则偏重于执法明令。《黄霸传》云:“霸少学律令,喜为吏。……为人明察内敏,又习文法”,“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将军霍光秉政,……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郡下,繇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而霸独用宽和为名。”宣帝时,霸为颍川太守,“为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问,劝以为善防奸之意,乃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蓄养,去食谷马。米盐靡密,初若烦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霸力行教化而后株罚,务在成就全安长吏。”
两人的治法无根本之异,都是以提倡本业,遵守法令为依归,至于移风易俗,则只择其可行者实行之而已,并不强制实行。故韩延寿在推行其教化之前,还担心颍川郡的老百姓反对,特意先对上层人物做好疏通工作:“延寿欲更改之,教以礼让。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消除怨咎之路。长老皆以为便,可施行,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延寿于是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卖偶车马下里伪物者,弃之市道。”而黄霸以法治,也做到“百姓乡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是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程度。
以韩延寿、黄霸为代表的有治绩,而治行又不严酷的地方官员,在汉代被称循吏。他们在政平讼理的前提下,还致力于整齐风俗的教化工作。如果从地域上来扯,西汉的循吏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将中国地区风俗文化的多样性逐渐融合为一,此外还有个别的改造南方蛮夷风的例子。东汉的循吏的突出作用则在于将中原的风俗文化慢慢传播到南方去,使蛮夷风逐渐同化于华风。由于两汉之际的动乱,不少中原地区人士暂时或永久地迁到南方,也对华风的南被起了不小的作用。
下面主要依据两《汉书》的材料,并以地方官移风易俗的工作来分析部分地区风俗的变迁情形,引文皆见于有关官员的本传。先说西汉。
西汉的风俗变迁主要在中原地区,淮汉以南只有蜀郡风俗变迁比较明显:
豫州颍川郡:
颍川郡原是战国时期韩国的中心,在历史上出现过申不害与韩非子等著名法家人物,在他们的影响下,形成“高仕宦,好文法”的社会风气,“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与此同时“豪杰大姓相与为婚姻,吏俗朋党。”这种风俗自然不利于中央集权统治,但西汉前期无法予以改变,直到宣帝初才逐渐发生变化。其时赵广汉在颍川当太守,他巧妙地使用计谋与法治来打破朋党的陋俗,使得“其后强宗大族家家结为仇雠,奸党散落,风俗大改。”但这一改虽然使得社会安定,却未使风俗变得淳朴,而是形成“吏民互相告讦”的坏风气。本来韩文化的遗存就是“好争讼分异”,赵文汉的办法无异火上加油。韩延寿继任以后即改以礼让的办法来教育百姓,告诉他们“和睦亲爱,消除怨咎”的途径,改变多怨仇的陋习,提倡行谦让、让资财、行孝弟的新风,使得社会风气大大好转。同时又鼓励学文习武,贯彻礼乐教育,并改革婚丧嫁娶制度,使之依照古礼而简化。之后黄霸又继任颍川太守,虽然他是以法为治,却并非像一般文法吏那样不教而诛,而是先让百姓明白必须遵守的法令的内容,“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这种“力行教化而后诛罚”的办法,行之也十分有效。两代太守变易风俗的基本手段,用《汉志》的话来说就是“化以笃厚”,颍川郡在他们的治理下风俗有显著变化,已如前文所述。
荆州南阳郡:
(荆州虽属南方,但其最北之南阳郡乃在淮水以北,应属中原)
在颍川郡以南的南阳郡本来也是韩国的领域,秦灭韩以后,又将天下不轨之民迁徙到南阳去,这就使得南阳产生“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的风气。秦汉相沿的政策都以事农为本,视重商为敝俗。于是宣帝时郑弘与召信臣相继为南阳太守,就着力改变这种风气。尤其是召信臣极其重视农业,亲自领导兴修水利的工作,造成重本弃末的风气。《汉书》本传说他“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同时对于“府县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为事”者,“辄斥罢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视好恶。”在这种治理方针下,使得南阳郡风气为这一变:“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此外,召信臣对于婚丧制度也有所改革,“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
兖州东郡:
东郡原来的风俗是不遵法度:“其俗刚武,上气力。”此俗于长治久安当然不利,故宣帝时韩延寿为东郡太守,有意于以改变。延寿之治东郡,总结起来是“承圣恩,崇礼义,尊谏争”三项。“承圣恩”是遵守中央法令(承皇帝意旨),“崇礼义”是遵从儒家的教化,“尊谏争”,一作纳谏争,即发扬民主,听从民意。韩延寿“在东郡三岁,令行禁止,断狱大减,为天下最。”既然能做到令行禁止,断狱大减,则东郡原有的刚武,上气力的旧俗,必然起了变化。
幽州渤海郡:
渤海郡位于战国的齐赵之间,具齐地重商轻农及奢侈之风。宣帝初龚遂被任为渤海太守,“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

、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曰:‘何为带牛佩犊!’春夏不得不趋田亩,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蓤芡。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积,吏民皆富实。狱讼止息。”龚遂在渤海郡的教化主要是在培养重本轻末的风气,不能说他的作用就使齐地风俗顿时改观,但这种教化在使齐地的风俗同化于他郡方面,无疑是有效果的。
司隶左冯翊:
左冯翊靠近京师,多达官显贵,高赀游侠,风俗不纯。韩延寿宣帝神爵间为左冯翊守,其施政方针与在颍川与东郡时不同。先之以无为之治,后又以自责精神来感化百姓,不但以此而止兄弟之讼,且“恩信周偏二十四县,莫复以辞讼自言者。推其至诚,吏民不忍欺绐。”
益州蜀郡:
蜀郡虽在秦岭以南,但战国末为秦国地,已接受秦岭以北秦文化的影响,虽有蛮夷风而与荆楚吴越有别,因此以文化地域而言,蜀地可算在南北之间。也因此蜀地风俗的变迁在南方各地区中最早。景帝末文翁任蜀郡太守时就着手移风易俗:“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又修起学官在成都市中,召下县子弟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王。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两个办法,一是派出去学习,二是在本地培训。不但提高官吏文化水平,并以学习培训后之年青人担任职务,以显耀之,禄之所在,人皆欲之。而且为全国典范,郡国皆立学校以培养官吏。
三
东汉时期,这种追求风俗齐一的做法继续不渝。加上光武帝以儒学为治理指导思想,儒生与循吏遂相结合,使移风易俗按儒家的规范进行。《后汉书·儒林传》说:“乃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整个东汉社会的前期养成尊儒之风气。直到邓后称制以后,儒学地位才有所下降。以是之故,东汉的文化是以儒学为中心,在地方教化方面,也以之为本。儒林之中复有多人任地方官,于是在统一文化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不但在北方使移风易俗的面更加扩大,而且将这一做法逐渐推行到南方去。东汉风俗变迁的记载多在南方与边郡,乃因北方自西汉后期以来已是渐归于一,而南方与缘边诸郡风俗则主要是在东汉时期才次第发生变化,故相形之下显得突出,其实北方的风俗也在继续变迁中,其著者有以下数例:
兖州山阳郡:
秦彭为扶风茂陵人,“建初元年(76年)迁山阳太守。以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飨射,辄升降揖让之仪。乃为人设四诫,以定六亲长幼之礼。有遵奉教化者,擢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吏有过咎,罢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怀爱,莫有欺犯。兴起稻田数千顷,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瘠,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乡县。于是奸吏跼

,无所容诈。”山阳在西汉时的风俗并不好,有“好为奸盗”的毛病,秦彭的举动即针对纠正旧俗而来。
并州太原郡:
周举在顺帝永建阳嘉之际(126—135)“迁并州刺史。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岁多死者。举既到州,乃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这是革除地区性陋俗之佳例。
荆州南阳郡:
南阳在东汉是所谓帝乡,贵戚豪右不法者众,历来的二千石都不称职。桓帝时,王畅任南阳太守,施以重典,豪右大震,但风俗并未大改,后“更崇宽政,慎刑简罚,教化遂行。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畅常布衣皮褥,车马赢政,以矫其敝。”
不止郡太守注意风俗的改革,即县令长也行教化之事。东汉末,应劭任齐郡营陵令,到任以后就下了改易风俗的命令(见《风俗通》所载营陵令到官移书申约束民):“到闻此俗,旧多淫祀,靡财妨农,长乱积惑,其侈可忿,其愚可闵。……今条下禁,申约吏民,为陈利害,其有犯者,使收朝廷。若私遗脱,弥弥不纪。主者髡截,叹无及已。……至于驾乘,烹杀倡优,男女杂错,是何谓也……礼兴在有,年饥则损。自今听岁再祀,备物而已。不得杀牛,远迎他倡。”虽然北方的淫祀不如南方狂热,但在某些地方仍然存在,甚至还有新产生的奉祀对象。如齐地淫祀之首是奉祀城阳景王,即汉初齐悼惠王之子刘章,就是西汉才兴起的新祀。应劭反对淫祀,认为这是愚昧而且不利于农事活动的表现,但他并不反对某些祭祀行为,如承认城阳景王应该受祀,但不准有越轨行为,如烹杀倡优,杀牛等行为,只要简单地表示礼仪即可。
县令长而外,乡亭小吏亦可以行教化。《仇览传》载,“(览)陈留考城人也。少为书生淳默,乡里无知者。年四十,县召补吏,选为蒲亭长。劝人生业,为制科令,至于果菜为限,鸡豕有数。农事既毕,乃令子弟群居,还就黉学。其剽轻游恣者,皆役以田桑,严设科罚。躬助丧事,赈恤穷寡。期年称大化。”又据《爰延传》,史昭为乡啬大,仁化大行,人但闻啬夫,不知郡县。不但小吏,甚至地方豪绅也可以行教化之责。《王丹传》载:丹“家累千金,隐居养志,好施周急。每岁农时,辄载酒肴于田间,候勤者而劳之。其惰懒者耻不致,丹皆兼功自厉。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轻黠游荡废业为患者,辄晓其父兄,使黜责之。没者则赙给,亲自将护。其有遭丧忧者,辄待丹为办,乡邻以为常。行之十余年,其化大洽,风俗以笃。”县令长以至乡亭小吏、地方豪绅的教化主要见于北方,表明风俗齐一的要求在中原地区已逐渐蔚为社会潮流。而在南方和边郡地区,改变风俗的行动主要还有赖于有见识的郡太守。尤其在南方,移风易俗的任务更加重大,因为在中原地区人士看来,北方边郡还只是习染胡俗而南方却全然是蛮俗。所以《汉书》概括西汉风俗地域差异特点时只提到关东出相,关西出将,这并不是说,西汉只有东西的差异,而不存在南北的区别,而是反映当时人认为南方是与中原地区是完全不同质的文化,一是华风,一是蛮俗,其差异是不待言而自明的。至于关东与关西的差异则是同一华夏风俗的地域差异。
西汉时蜀郡仍被视为有蛮夷风,吴越地区更不待言。到东汉时,除蜀郡外,广大的江汉以南地区仍然被中原人士看成是蛮夷之地。丹阳被认为是越俗,会稽、九江、豫章自不用说(参见下文之实例),即使离中原较近的江夏郡也是“蛮多士少”。《后汉书·黄琼传》说了这么一个故事:“司空盛以疾,琼遣琬(琼,江夏安陆人,琬为琼之子)候问,会江夏上蛮贼事副府,允发书视毕,微戏琬曰:‘江夏大邦,而蛮多士少。’”此虽为盛允戏语,却正道出了北方人士对江夏郡乃至于整个南方地区的看法。而实际上,直到南朝时,江夏南郡一带多有蛮郡、左郡僚郡的建立,说明其时该地多有少数民族聚居。至于东汉时有九江蛮,而庐江郡有南夷,则明见于丁同书《卢植传》。此诸郡都在江北,而江南之武陵、零陵等蛮,交州的蛮夷,益州的西南夷均载于南蛮西南夷传中,其风俗与中原地区有根本的不同,于是东汉地方官在这些地方的移风易俗工作也显得特别突出,以下兹举数例言之:
扬州丹阳郡:
李忠于建武六年(30年),迁丹阳太守,“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垦田增多,三岁间流民占著者五万余口。十四年,三公奏课为天下第一。”这里的“丹阳越俗”还不单是说丹阳有越俗,而是表示在两汉之际,中原人认为丹阳郡是越人居处,其风俗就是与华夏有明显区别的越俗,正如同西汉景帝时仍认为蜀郡有蛮夷风一样。因此李忠所推行的是儒家的教化,以期化越俗为华风。
扬州会稽郡:
会稽亦是越俗,其最大特点是多淫祀。《第五伦传》载:“会稽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财产以之困匮。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荐祠者,发病且死先为牛鸣,前后郡将莫敢禁。”第五伦于建武二十九年任会稽太守,“到官移书属县,晓告百姓。其巫祝有依托鬼神诈怖愚民,皆案论之。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民初颇恐惧,或祝诅妄言,伦案之愈急,后遂断绝。”
扬州九江郡:
九江郡也有淫祀,《宋均传》云:“浚遒县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众巫遂取百姓男女以为公妪,岁岁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后守令莫敢禁。”宋均于建武末年至永平元年(58年)间为九江太守,“乃下书曰:‘自今以后,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扰良民。’于是遂绝。”
扬州庐江郡:
王景于建初八年(83)迁庐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山是垦辟倍多,境内半给。遂铭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庐江郡离中原不远,而生产方式仍很落后,且有少数民族聚居(见上引《卢植传》),故王景在任以推广先进的生产方式为主。生产方式的变更本身即是风俗的变迁。王景其人多材多艺:“少学易,遂广窥众书,又好天文术数之事,沈深多伎艺”,后来在治理黄河方面又有很大贡献。
扬州豫章郡:
据《栾巴传》:“(豫章)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赀产以祈祷。巴素有道术,能役鬼神,乃悉毁坏房祀,翦理奸巫,于是妖异自消。百姓始颇为惧,终皆安之。”栾巴为豫章太守在顺帝桓帝间,“能役鬼神”当是虚说,目的是为了加强翦奸巫,毁淫祀的威力。
荆州武陵郡:
宋均于光武帝建武年间调补武陵郡辰阳长。东汉辰阳县当今湖南辰溪县地,“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均为立学校,禁绝淫祀,人皆安之。”又,数十年后,应奉在永兴元年(153年)任武陵太守,“兴学校, 举仄陋,政称变俗。”
荆州桂阳郡:
桂阳郡在南方诸郡的风俗变迁中最为突出,先后有六任太守在此有明显治绩,其中的卫飒、茨充、许荆、栾巴等人在改造当地风俗方面都有显著的建树。卫飒是河内修武人,建武十五年(39年)“迁桂阳太守。郡与交州接境,颇染其俗,不知礼则。飒下车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先是含洭、浈阳、曲江三县,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属桂阳。民居深山,滨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租。去郡远者,或且千里。吏事往来,辄发民乘船,名曰传役。每一吏出,徭及数家,百姓苦之。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于是役省劳息,奸吏杜绝。流民稍还,渐成聚邑,使输租赋,同之平民。又耒阳县出铁石,他郡民庶常依因聚会,私为冶铸,遂招来亡命,多致奸盗。飒乃上起铁官,罢斥私铸,岁所增入五百余。飒理恤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物宜。视事十年,郡内清理。”桂阳郡在荆州最南部,地跨岭南,在当时,岭南的交州地区被看成是越俗的范围,卫飒不但是从修学校,推广礼制婚姻入手改革桂阳风俗,而且以开辟交通、官营手工业为手段来杜绝奸吏,防止奸盗,使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保证教化得以取得成效。
卫飒在桂阳太守任上整整呆了十年,而后又为有同样声誉的茨充继任:“南阳茨充代飒为桂阳,亦善其政。教民种植桑柘麻紵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东观记》把茨充的政绩更加具体化了:“元和中(85年左右),荆州剌史上言:‘臣行部入长沙界,观者比徒跣。臣问御佐曰:人无履亦苦之否?御佐对曰:十二月盛寒时并多剖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温或脓溃。建武中,桂阳太守茨充教人种桑蚕,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颇知桑蚕织屦,皆充之化也。’”有人以为此则记载有些夸大,认为茨充之化不可能及于整个江南。其实秦汉时的江南乃以指湖南为主,并非今日江南的涵义,今日江南在当时称作江东(见拙文《释江南》),而其时之湖南不知织屦;恐是事实。且织履之俗由桂阳而扩散传播到长沙郡等江南地区是顺理成章的事。茨充虽无同化礼制风俗之记载,但生活风俗的改变也是重要的变迁,不可小看。
东汉中期,许荆继任桂阳太守。许荆是“会稽阳羡人。……和帝时(89—105年),稍迁桂阳太守。郡滨南州,风俗脆薄,不识学义。荆为设丧纪婚姻制度,使知礼禁。”又以自责的精神感动耒阳县争财两兄弟和好如初。许在职长达十二年,继续以改革婚丧嫁娶制度为已任。又过数十年,栾巴“西迁桂阳太守。以郡处南垂,不闲典训,为吏人定婚姻丧纪之礼,兴立学校,以奖进之。虽干吏卑末,皆课令习读,程试殿最,随能升授。政事明察。”栾巴为魏郡内黄人,并非习儒出身,《后汉书》说他“好道。……素有道术。”但他所行仍是立学校,定婚丧之礼的教化工作,可见其时,不论儒道法,都把改变不合华夏风俗的工作当成自己的天职。也反映其时在南方明显地存在与中原礼俗不同的习俗。所以只要从北方到南方来当官的人或是从南方较先进地区到后进地区当官的人都会有必须移风易俗的感受。栾巴在桂阳任职也有七年之久,对于推进与巩固华风自然有利。
交州九真郡:
九真在今越南中部,“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东观汉记》曰:九真俗烧草种田),民常告籴交趾,每致困乏。”建武初,任延任九真太守四年,“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聘,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是岁风雨顺节,谷稼丰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任延的最大功劳是在婚姻制度的确立。论者以为和真及其附近地区东汉以前还盛行族外群婚(上揭《汉晋文化地理》)。直到任延改革婚姻制度,令男女皆以年齿相配之后,“其产子者,始知种姓”,也就是说从此子不但知其母也知其父,这是从群婚制到专偶制的跳跃性变化,意义十分重大。
交州交趾郡:
交趾郡因为地处红河平原,自然条件优越于九真郡,故可以粮食粜于九真。但在风俗方面也还是与华夏不同,在两汉之际,锡光任交趾太守时进行改革,故《后汉书》在《任延传》中附带提到:“平帝时,汉中锡光为交趾太守,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化声侔于延。王莽末,闭境自守。建武初,遣使贡献。”
不但是交趾、九真两郡之风俗与中原有异,其实整个交趾刺史部所察各郡——即今两广与越南北、中部地区,在两汉之际都被视为化外之地,《后汉书·南蛮传》所说:“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不但指出衣着习俗(实际上代表着物质文明)的简陋,还意味着婚姻制度的原始状态以及语言与中土的差异。因此任延与锡光在九真与交趾移风易俗的行动历来为治史者所乐道,《南蛮传》将两人的功绩一并提及:“光武中兴,锡光为交趾,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在《任延传》中还把他们的政绩拔高到“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的高度。
益州蜀郡:
蜀郡因为富饶,故出现以钱买官之风气,第五伦于明帝间为蜀郡太守,革除此敝。据《后汉书·第五伦传》载:“蜀地肥饶,人吏富实,掾史家赀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以财货自达。伦悉简其丰赡者遣还之,更选孤贫志行之人以处曹任,于是争赇抑绝,文职修理。”这里改变的是社会风气,与上述革除陋俗,有所不同。
四
经过两百年的移风易俗过程,使西汉后期原有的八方殊俗异采纷呈的风俗渐渐地趋于六合同风的单一化形态,因此密集的多元的风俗文化区已经消失,尤其中原地区的那种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面貌已不再现。在东汉后期,我们已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划分新的风俗文化区。当然这也和文献的缺佚有关,《续汉书·郡国志》没有留下像《汉书·地理志》那样精彩的风俗地理资料。但可以肯定地说,东汉后期的风俗地域差异是显著地削弱了,尤其是在生产方式与婚姻制度方面,基本上已经是达到六合同风的状态了。不同的风俗内涵其变迁程度是不同的,生产方式的变更与礼制婚姻的传播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员最关心的,而且这两方面风俗的改变一般而言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一旦接受了先进的牛耕和其他耕作方式,就不会倒退到火耕水溽的状态去;同样,婚姻制度也是向前发展的,只要同化于礼制婚姻,也就不会退回到群婚、借妻婚等非礼制婚姻形态去。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在东汉后期,在生产方式与婚姻制度方面地区的差异性最小。
物质生活习俗,即衣食住行方式的变迁也较容易,这方面的趋同性也很明显。而社会风气的改变则需要较长时间,而且往往不是一蹴之功,有可能反复回潮。不过详细分析,其中又有区别。好学的风气较易培养,尚文尚武风气的变化要难些,至于奢侈之风颇难改易,必须三令五申,甚至严加禁止,才能取得成效。信仰风俗的变迁最不容易,如淫祀必定要用强制手段或另一种信仰来代替才能禁绝。因此在这一方面我们不能说到东汉后期,信仰风俗的地域差异已经消除,但从上述扬州所属诸郡淫祀废止的实例,可以觉察到从全国范围看来,这种差异已经远比西汉时期为小。
除了以上的基本结论外,从两汉风俗的地域变迁过程我们还可以得出其他一些想法:
1、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 风俗文化的内容应包括生产方式(耕种方式、水利设施)、生活习俗(衣食住行)、社会风气(重农重商、尚文尚武、奢靡勤俭)、礼仪制度(婚丧嫁娶)等方面。其中生产方式最为要紧,生产方式的改变会带动其他方面的变迁。所以几乎所有到南方任职的循吏都以改变生产方式为首要任务,从庐江郡到九真郡都有推行牛耕的纪录。在北方也以兴修水利开辟农田为第一要务。这是从上面所举的一些例子中可以明显看到的。因为温饱乃第一要义,不但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即孔子也主张富而后教。在北方注意实业的发展还有另一层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提倡以农为本,纠正弃本逐末的不良风气。如果农业不能使人致富,那么重农的风气就难以养成。
2、对于移风易俗的态度有两种,一是因其俗,简其礼;二是革其俗,变其礼。这是西周初年太公治齐与周公治鲁的差异。后者为儒家所推崇,故《孝经》引孔子的话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东汉所实行的正是革俗变礼的基本方针,但在具体实行过程中,地方官各有变通。《后汉书·史均传》载,均“迁上蔡令,时府下记,禁人丧葬不得侈长。均曰:‘夫送终逾制,失之累者。今有不义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罚过礼,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这说明郡级政府有意以行政命令来改变风俗,而不放任自流,甚至于把丧葬过礼当成犯法之事加以禁止,但宋均却认为过礼虽然错误,却只应施以教化,而不该操之过急,随便处罚。在移风易俗过程中,有时因势利导反而能起到比行政命令更好的效果,如廉范不改夜作之俗而加强防范火灾的事例即是。
3、移风易俗不是一时之事,要经过比较长期的变迁才能见效。例如颍川郡的风俗经过韩延寿与黄霸的努力已经由好讼而转为笃厚,但在东汉初,仍有剽轻之病(见《寇恂传》),蜀郡西汉时有“好文刺讥”的陋风,直到东汉中期仍有“其俗尚文辩,好相持短长”的记载(见《廉范传》)。因此上述的各郡风俗变迁并非说明这些郡都已经是风俗淳厚,别无弊病了。
4、循吏由儒生而来的现象很普遍。如韩延寿少为郡文学, 任延“年十二,为诸生,学于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遂使儒家移风易俗的观念普及于循吏之中,而造成东汉普遍地有风俗同一的趋势。其因俗简礼或革俗变礼,不过手段的不同而已,其改变风俗的基本意图是一致的。
5、 当然我们在上面是从地方官主动地进行移风易俗的角度来分析风俗文化区的变迁。其实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光是一二个人的教化是不大容易使风俗发生根本性变迁的。而且在文化传播方面,个别官吏的教化只能是墨渍式的,只有移民的文化扩散作用才能是席卷式地起到改变风俗的作用。譬如交趾部的风俗变迁除任延、锡光这样的循吏在起作用外,还有赖于当时的移民活动,故《后汉书·南蛮传》说:“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不仅交趾如此,即使比较先进的南方地区,北方移民的到来也一样要起到改变风俗的作用。《任延传》说,东汉初,“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东汉时会稽风俗的改变(见上)与移民的影响当有一定关系。
6、自然环境也是促使风俗同一的条件之一。平原地带交通方便, 人民往来频繁,势必利于风俗的同化。山区丘陵阻隔交往,也必促成风俗的差异。西汉时南方风俗似无大异,只因了解不够,至《隋书·地理志》,即看出南方各地风俗亦有差异,而北方风俗转而无大差异矣。
来源:《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4期
哈民忙哈遗址史前灾难成因的法医人类学证据
我要新鲜事2023-05-25 19:14:330000周大鸣:薪尽火传 万古流芳——深切缅怀黄淑娉教授
恩师黄淑娉不幸于日前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三,不惟门下弟子沉痛哀悼,中山大学乃至中国人类学界民族学界都深表哀悼。今天,我们在这里送别先生最后一程,缅怀先生为民族学人类学学术所做的贡献,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所做的贡献!先生之学,学贯东西,派兼南北,经世致用,历久弥新我要新鲜事2023-05-25 09:30:160002冯时:昆仑考
我要新鲜事2023-05-27 00:49:350002缙云甲龙:早期唯一带尾锤的甲龙(宽达45厘米)
缙云甲龙是一种甲龙亚科恐龙,诞生于1亿年前,是最原始的甲龙亚科恐龙。缙云甲龙最大的特点就是虽然是早期甲龙亚科,但是却长有宽达45厘米的尾锤。缙云甲龙的第一批化石是在中国的浙江省缙云县壶镇发现的。缙云甲龙的外形特征我要新鲜事2023-05-09 02:51:170000考古发现6.1亿年前的化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有答案了?
2013年12月13日,南京博物馆展出了一批具有2800多年历史的“西周鸡蛋”。这些出土文物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和研究热情,同时也引发了一个有趣的哲学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要新鲜事2023-04-22 03:03:11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