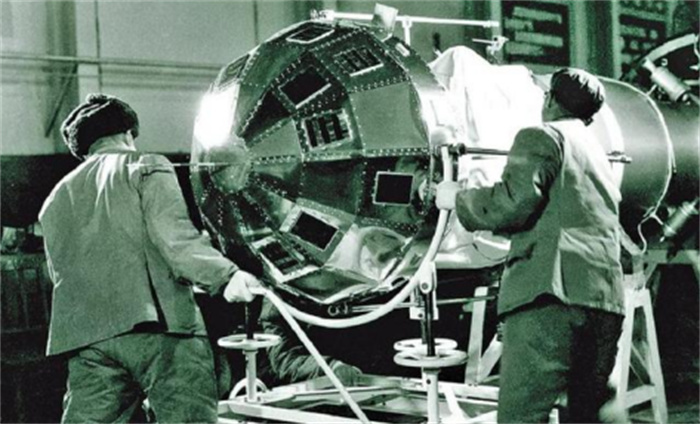施劲松:国家形成的进程与理论模式——读《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
一
探讨国家的形成,需要考察国家形成的进程并构建相关的理论模式。
国家形成的进程是一个客观的过程。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形成进程,但这个进程并不会自己显现出来,它只能透过考古资料所蕴含的信息反映出来。因此,对于国家形成的进程,需要我们依据考古材料去将它描述出来。相比之下,描述具有主观性和片面性,所以描述的工作需要在不同的理论框架内利用各种考古材料从多角度不断地进行。而国家形成的模式,则是指我们对国家在形成进程所表现出的某些规律和共性的认识和由此而构建的理论。这些规律与共性可能体现在国家的政治组织、经济结构和城市的功能等方面。之所以需要构建理论模式,那是因为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只是国家形成进程的片断,只有依靠理论模式,我们才可能对进程进行更为深入的描述和认识。同时,与进程的惟一性不同,构建模式的方式是多样的,所以只有通过多种理论模式,我们对进程的描述才会更全面。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在一个国家形成的进程中或许并不存在明显的规律,或者其规律并不为人们所认识,因此我们并不一定能根据任何一个进程都构建出模式。一个理论模式的得出也不能只是孤立地考察某一个具体的进程,既使根据某一个进程我们能够得出一个模式,那也是因为该进程相对于其他进程而言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因此,构建一个国家形成的理论模式,还需要将其纳入到世界范围内进行考察。
阐明国家形成的进程和模式这两个概念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种探索国家形成的思路与方法。那就是根据已有理论模式,利用考古材料对国家形成的进程进行描述,在此基础之上对已有模式加以批判,然后再得出新的认识。正是不断地通过这种描述、构建和批判,描述的进程与真实的进程才有可能逐渐接近。
二
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这一研究领域中,最值得关注的新成果是刘莉和陈星灿所著、2003年由英国达克沃斯(Duckworth)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一书。这部专著所做的工作就是对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进程的描述和对理论模式的构建。
世界上不同地区的早期国家,其进程各不相同。目前关于早期国家形成进程的主要模式有城市国家(注:Trigger,Bruce,Early Civilizations:Ancient Egypt in Context,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1993.)、银河星团政体(注:Southall,Aidan,Alur Society:A Study in Processes and Types of Domination,Heffer,Cambridge,1956.)、地域国家(注:同(Trigger,Bruce,Early Civilizations:Ancient Egypt in Context,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1993.))和乡村国家(注:Charles Maisels,Models of Social Evolution:Trajectories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State,Man,22,1987.The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From Hunting and Gathering to Agriculture,Cities,and the State in the Near East,Routledge,London,1990.)等。这些模式是否可以用来解释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或者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进程中是否还可以构建出其他模式呢?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利用考古材料来对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进程加以考察和描述。
为了有效地利用众多的考古材料,同时也考虑到早商国家和晚商国家可能存在着的差别,《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一书将考察的重点集中在二里头和二里冈时期的聚落形态和政治经济方面。为此,该书着重讨论了对于认识国家形成进程至关重要的一系列因素,它们主要包括二里头时期发生的社会变化、重要资源的分布和主要的流通路线、与资源分布和流通路线相关的聚落形态特征、都城和主要地区性中心之间的聚落分布模式。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以及各地区性中心的相互关系、国家对重要产品的生产与分配的专控以及相应的政治控制程度等。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又主要依据这样一个理论:为了解决早期国家的社会分层、财富再分配、人口压力等发生在复杂社会核心地区的问题,统治者通常用占领边缘地区寻找新资源以平衡核心地区的财富再分配来加以解决,因此,对资源的获取决定了聚落分布和早期国家扩张的模式。由此,考古学就可以通过考察重要资源的分布、资源的主要流通路线,以及都城和各级地区性中心的分布等,来揭示由这些因素所决定的早期国家的政治经济活动和控制、运输资源的能力,并最终对国家的形成进程做出描述。
根据该书的考察,二里头时期社会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主要体现在此时的聚落已由此前的二级或三级结构变成了四级结构。同时,人口的集中和城市化、与政治一体化相关的陶器生产的标准化,以及青铜冶铸业和长途贸易等均已出现。这些变化与新石器时代晚期所存在的现象不同,它们的同时出现表明一种新的社会的形成。二里头遗址本身的规模,遗址上宫殿、宗庙建筑和不同等级的墓葬,以及国家专控手工业的产生和领土扩张的开始,也都说明早期国家出现在二里头文化二期。二里头国家的形成离不开各种资源。在作为二里头文化核心区域的伊洛地区并不丰富、但对于早期国家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资源,主要包括铜、锡、铅等金属矿和盐矿。金属资源除中原及附近地区外,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盐矿则主要位于山西南部的运城盆地。在这些矿源所在地和伊洛平原之间都有以水路为主的交通线。为了控制和运输这些资源,在核心地区的伊洛平原及其边缘地区,都出现了次一级的中心。如核心地区的巩义稍柴和偃师灰嘴,边缘地区的山西夏县东下冯和垣曲南关、陕西商州东龙山,以及长江中游的黄陂盘龙城。这些次一级中心除提供瓷土、石料、农产品和生产某些石器和青铜制品等外,它们都联系着核心地区与资源产地,是早期国家用以获取和运输金属和盐等重要资源的地区性中心。边缘地区考古遗存的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文化相近,与当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别,正说明这些地区的文化发生了由于早期国家的扩张、殖民或文化传播所导致的迅速变化。由此可以认为,二里头文化的扩张可能是国家政治经济战略的物化形式。为获取资源而进行的领土扩张成为二里头文化的特点,边缘地区中心聚落的发展可能是核心地区人口扩张的结果,而二里头文化的聚落形态也受制于早期国家对边缘地区重要资源的获取与运输。
在二里冈文化时期,早商文化遗址的分布区又有新的扩展,并出现了五级聚落结构。青铜冶铸中心和主要的政治、宗教中心直接从二里头转移到郑州后,郑州成为国家的支配中心。偃师商城在其早期阶段的功能主要是军事的而非经济的,随着郑州成为都城,偃师商城成为一个控制伊洛地区和丹江地区资源的次级中心。在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二里头时期的一些地区性中心仍然是青铜器、陶器的生产中心,同时也继续发挥着控制资源的功能。但二里冈时期的聚落也出现一些变化,比如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核心地区的稍柴成为了三级中心,河南的焦作府城成为一个二级中心。边缘地区的东下冯和南关变成了设防的聚落,垣曲商城则延续了二里头时期南关的角色。另外,在河南西部商文化遗址突然增多也可能与当地有着相对丰富的资源相关。在陕西北部、内蒙古南部、山西北部和河北西部都可以看到二里冈文化的影响。在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出现了商代中期的大遗址。在陕西中部和南部,除了东龙山外,与二里冈文化相关的遗迹还见于老牛坡、怀珍坊和城固。在山东,大辛庄等地的发现可能反映了商人为得到沿海地区包括海盐在内的自然资源而对东部边疆所进行的殖民活动。山东西南部则成为商人为获得长江下游的资源而进行扩张的地区。在长江中下游,盘龙城和吴城是二里冈国家建立的用来控制当地资源的地区性中心。甚至在湖南澧水流域也发现有早商的文化遗存。
早商政权的迅速扩张可以从商文化取代二里头文化,以及商文化对边缘地区的文化侵略中显现出来。这一扩张的政治经济动力也一样是为了获取重要资源。但在二里冈文化上层时期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社会变化过程。一是商人从西方撤退,表现为东龙山遗址在二里冈之后的消失,以及山西南部诸遗址因盐业生产和采矿、冶铸活动的中止与转移而出现的衰落和废弃。二是商文化同时迅速向东、向南扩张,这是二里冈国家为了获得沿海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金属、海盐和其他自然资源而进行的生产中心和人口的转移。二里冈时期的扩张还显现出两种情况,一是在接近核心地区的边缘地区,如东下冯、垣曲商城、东龙山、老牛坡、大辛庄、盘龙城、吴城等通往重要资源地的地区性中心,其物质文化全部或主要体现为商文化;二是在距核心地区较远的边缘地区,如内蒙古的朱开沟、陕西城固和澧水流域等,它们位于通往更远的资源的交通线上,其文化面貌以当地文化为主,二里冈文化并不占据支配地位。
基于如上考察和描述,《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最后提出了一个反映早期国家政治经济图景的“中心—边缘关系”的模式。这个模式认为,早期国家出现后,以获取资源为动力的从核心地区到边缘地区的扩张模式,可能由一系列的环境的和社会的因素造成。它们包括自然地理因素,即聚落分布区的自然地理特征和与自然资源密切相关的水路交通,形成了中国早期国家的文化和政治景观。由于青铜礼器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权力的象征意义,使得追逐金属资源这一国家扩张的动力背后还蕴含着更深的意识形态因素。王室贵族对青铜礼器的生产和技术所进行的专控,使得二里头和二里冈国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系统具有“贡赋生产方式”的特征。在这样的生产系统中,社会上层通过政治和军事的手段从最初的生产者手中获得贡物,而生产贡品的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也由政治权威进行部署。中国早期国家的“中心—边缘关系”正是以这种贡赋制度为特征:最低级的聚落通过边缘地区的中心向核心地区提供原料和贵重的贵族用品,以支持首都的城市发展和手工业生产,并进而促进社会等级结构的形成;而首都则将青铜礼器这样具有神圣性质的手工业产品和盐、原始瓷器等从边缘地区获得的珍贵物品再分配到最低一级的地区性中心。贵重物品和生计物品的生产和流通模式,共同构成了早期国家的经济主干,满足了人们的经济需求,支持了等级制度的运行,并使宗教信仰制度化。最后,在二里冈末期,这个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系统随着核心和边缘地区的地区性中心的衰落而瓦解。
通过对二里头和二里冈国家形成进程所进行的描述,该书最后认为前述四种常见的关于国家形成的理论模式都不适用于二里头和二里冈时期的早期国家。但相对而言,地域国家的模式与中国早期国家的进程是较为契合的。
三
《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是探讨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首先,这部书展现了一个从已有理论模式、到利用考古材料对国家形成进程进行描述、然后再对模式加以批判的整个研究过程,以及将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纳入一个更为广阔的范围内进行研究比较的视野。这样一种研究,正是探讨国家形成并将研究引向深入的有效途径。
其次,这部书着重探索的是国家形成的动态进程及其动力,在利用获取资源是国家形成的推动力这一理论的同时,还强调技术、生态、人口与经济等因素。这些研究目标和理论是西方考古学界自过程考古学以来就十分重视的。一些西方学者甚至也利用与“中心—边缘关系”模式相似的理论来作为分析考古材料的理论基础,即认为在一个超国家的空间和跨地区的劳动分工体系内,边缘地区向中心地区输送原材料,并在政治和经济上受中心地区控制,而所有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均有赖于其在该体系内角色的变化(注:参见托马斯·C·帕特森:《美国考古学六十年》,见《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张光直先生也曾利用这类理论来解释中国的考古材料,以求达到上述目标(注:比如张光直先生曾从资源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的青铜时代、中国早期的都城和商代文明等。具体可参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从强调资源的理论视角来描述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显然与传统的探讨不同。虽然这部书所提出的也只是国家形成的诸种理论模式中的一种,但当我们习惯于用私有制的出现和阶级的形成等来探讨国家的形成,或是习惯于将那些被认为是反映了国家形成的各种考古和文献材料做静态描述的时候,这部书的意义便在于它突破了我们的思维定式。无疑,这将有利于促进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多元化。
第三,青铜器在中国早期国家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以及因此而存在的大规模的青铜冶业,不仅为我们遗留下大量的相关遗物和遗迹,也决定了这部书所依据的理论在用来考察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时具有更多的合理性和适用性。通过这些理论可以将二里头和二里冈时期的绝大多数重要的考古发现串连起来,而且理论和考古资料也得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为了获取资源而进行领土和人口扩张,在扩张的过程中国家进一步形成,这一思想可以使对国家形成进程的描述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合理性。由此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进程,也因此而显得清晰可见。而对“中心—边缘关系”模式的提出和对已有国家形成模式的批判,则使我们对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进程的特殊性与规律性都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第四,在对国家形成进程进行描述时,该书广泛并有效地运用了包括考古学、文献学、地质学、文化地理学等不同学科的材料。其结果是,一方面国家的形成进程因这些材料而显得生动;另一方面,从资源的分布与聚落形态特征到各聚落的文化面貌及其变迁,从手工业产品的生产与流通到中心与边缘地区的关系,这些问题以及很多具体的考古材料和现象也都可以从进程中找出合理的解释。
这部专著在对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做了很好的描述与解释的同时,也留下并提出了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是在该书的理论框架和模式中,有一些研究似乎还可以进一步深入。
比如聚落等级,二里头时期和二里冈时期分别出现了四级和五级聚落结构,由此可以认为国家已形成。但聚落应分化为几级才标志着国家的形成?其理论依据是什么?另外,二里头二期以前已有三级聚落,但并末出现国家,而二里冈时期的五级结构较之二里头二期以后的四级结构又多出一级,那么国家的政治组织形态是否又有新的变化?对此我认为,在考察聚落等级的同时,或许还可以更为深入地考察最高一级的聚落即都城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所具有的支配作用。又比如,有一些地区性中心在二里头时期和二里冈时期都发挥着完全相同的功能,但另外一些地区性中心则发生了变化:由不设防的中心变成了设防中心,或是功能出现差别。这些变化是否反映出二里头国家和二里冈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异?有很多地区性中心的产生和消亡与核心地区的兴衰相一致,但也有一些地区性中心却在二里冈之后依旧延续下来,其原因何在?再比如,按照贵重物品的生产和分配模式,以青铜礼器为主的贵重物品只分配到最低一级的地区性中心。但在边缘地区,比如在江淮一带,就曾发现有不少零散的青铜器,它们不出自墓葬,也不出自聚落,甚至没有确切的层位。如何用上述生产与分配的模式来解释这些零散出土的青铜器?
第二是在该书的理论框架下还有一些相关的重要问题没有涉及或涉及不多。
比如从考古材料看,在二里头二期前后社会组织发生了明显变化,由此可以认为在当时一个具有国家水平的社会诞生了。这也就是说,早期国家的诞生可能是非常迅速的。为获取资源而进行扩张,这实际上只是促进了二里头和二里冈国家的进一步形成。但一个酋邦社会是如何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地域国家的,其进程和推动这个进程的动力又是什么?这是同样值得我们追问的。再比如,该书认为就政治组织和经济系统而言,早商和晚商之间显然存在一个社会结构组织的转换过程,甚至连国家形成的模式都有可能存在差别。那么早商和晚商之间转变的过程和原因又是什么?对此,该书在不同情况下分别提出了几种不同的可能的原因,包括地方自治力量的兴起,商王室因继承权等内部原因而引发的内乱,以及对贵重物品经济的过分依赖等。但这些不同的原因很可能相互关联并且具有因果关系。这其中,哪种因素才是决定性的?当然,这一类问题的提出并不是对这部书的质疑,因为内在的、决定性的因素很可能是我们永远无法获知的,尽管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永远怀着希望。该书曾明确提出考古学为二里头和早商国家文化扩张和衰落的过程提供了信息,但却没有为过程发生的内在原因提供多少准确的资料。也许这里面体现出的恰好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第三是在该书的理论框架下,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似乎还存在局限性。
在该书的描述中,核心地区的偃师商城作为二级聚落在早期具有军事功能,之后其功能主要是为了控制伊洛地区和丹江地区的资源。但从偃师商城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建筑过程,以及城内存在的各种建筑遗存看,这座商城所发挥的功能可能并不如此简单。所以目前学术界一种主要的观点就认为偃师商城绝不是存在很短时间的单纯的军事据点,也并非王室的离宫别馆,而是一座具有国家政治中心地位的商代早期都城(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2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如果偃师商城具有政治和宗教中心的功能,那么二里冈时期的聚落形态和主要中心之间的关系,以及早期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等都将会突破上述的理论模式。
而就边缘地区而言,该书认为长江中游的盘龙城和吴城都是商王国为获取资源而设立的两个据点;不仅如此,盘龙城的衰落和吴城的兴起还被视为是互相关联的事件,即在晚商时期盘龙城的人口向南迁至吴城地区。类似的看法也见于学术界其他一些相关研究中。不过,我认为盘龙城和吴城的关系并不一定那么简单和直接。二里冈时期的盘龙城,从城址的形制、布局到建筑技术,从葬俗到青铜制品等,几乎都与在郑州的同类发现相同。这体现了两地的人拥有一致的知识和价值体系,由此也可以说当时的盘龙城应当是二里冈国家的疆土。但吴城并不如此,吴城的发现不仅与郑州的发现有很多差异,而且与盘龙城相比也明显不同。并且,吴城与郑州和盘龙城的差异并不能完全用时代差距来解释,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的材料还来自属于吴城文化的新干大墓。新干大墓出土的青铜器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时代可能相当于二里冈时期,对此学术界许多学者也都持相同看法(注:自新干大墓被发现后,有很多学者都认为新干大墓中部分青铜器的时代相当于二里冈时期。对此,还可参见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在新干发现的部分青铜器,比如方鼎和扁足鼎,其二里冈时期的时代特征非常明显。但同时,这些铜器又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使得新干的二里冈时期的青铜器与郑州和盘龙城的同时期铜器存在明显差别。其实除了器形和纹饰方面的差异外,更为重要的是盘龙城常见的包括酒器在内的许多器类并没有在新干出现,而新干最为突出的方鼎等又不见于盘龙城。这些现象或许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二里冈时期盘龙城的文化与郑州一致,而吴城并非如此;二是吴城、特别是新干铜器中的二里冈文化因素可能直接来自郑州而非盘龙城。因此,是否可以将吴城视为一个与盘龙城一样的由商人设立的据点?如果认为二里冈时期的盘龙城与吴城都与早商国家控制资源相关,那么这两者的存在及其相互间的差别,至少显示出二里冈国家在边缘地区的扩张形式与结果,或者说对获取边缘地区重要资源所进行的努力也都是多样的。
也正是基于各地出土的青铜礼器都具有二里头或二里冈风格的认识,《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一书假设这些青铜器基本上是在同一个地方铸造的,并进而认为二里头和二里冈时期青铜礼器的生产和分配可能由都城垄断。这一假设可以得到有关铸范的考古发现的支持,即在二里头和二里冈时期,用于铸造青铜礼器的陶范目前仅发现于二里头遗址和郑州商城遗址,其他地区只发现了铸造工具和兵器的石范。但如上所述,新干大墓中有一部分相当于二里冈时期的具有地方特色的铜器,而且这些地方特点在新干大墓相当于殷墟时期的铜器中仍然存在。因此,恐难以将这些铜器解释为是由都城为地方性中心生产的,在郑州或殷墟也没有发现铸造这类地方性铜器的陶范。这说明在用“中心—边缘关系”模式来解释周边地区出土的铜器时,文化面貌的分析仍然是必要的。同时这种解释也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考古资料。
与边缘地区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早期国家的疆域。该书已清楚地意识到物质文化的分布范围与政治疆域的范围并不重合,但如何确定早期国家的疆域呢?书中用以描述国家形成进程的相关理论以及“中心—边缘关系”模式,都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对于早期国家的疆域,该书也不能确定,只是指出它可能到达了那些比较接近核心地区且物质文化全部或主要体现为商文化的边缘地区。
提出第三类问题,同样不是对《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这部专著的诘难。当我们在运用一种理论模式对国家形成进程进行严密并富有逻辑性的描述时,我们必然也会付出相应的代价,那就是研究视角和解释的可能性将受到限制,对进程的描述也会变得简单化和程式化。所以上述问题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对该书相关理论模式的价值和意义的否定,相反,这只是说明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不完善的,它所能解决的问题也都是有限的。衡量一种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并不是看它是否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是看这一理论是否具有可证伪性、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注: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第5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国家形成进程所具有的复杂性,直接决定了没有任何一种科学的理论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并且解释一切考古材料。正因为科学的理论具有“局限性”,所以我们才需要发展和完善已有的理论,并不断构建新的理论。只有依据不同的理论对国家进程做不同角度的描述,对进程的认识才会深入,我们也才能获得更多的相关知识。
四
利用考古材料来描述一段进程,构建一个理论模式,再对模式加以批判,这些对于探讨国家的形成来说仍是不够的。因为在这里,我们还面对着一个更为本原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是“国家”。
“国家”这个概念本身并不能从考古材料中归纳出来,也不能从对进程的描述和对模式的构建中得出。在我们利用考古资料来描述“国家”形成的进程和构建相关的模式之前,“国家”的概念就已经存在了。如果不先具备“国家”的概念和衡量“国家”的标准,我们显然无法就考古材料做任何比较,也丧失了描述“国家”形成进程和构建相关理论模式的可能。
什么是“国家”,“国家”应具有哪些要素,判定“国家”是否形成应依据什么标准,对此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观点。但这些观点具体如何,不同观点间又有什么共识或分歧,这些在这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这一概念以及衡量“国家”形成的标准是如何产生的。恩格斯对“国家”起源的研究并没有借助今天的考古材料,其有关“国家”起源和“国家”形态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思辨的结果。当代考古学家对于“国家”的种种认识,同样离不开思辨。《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也提出了衡量“国家”出现的标准,即一个社会至少具有统治阶层和普通阶层两个等级,社会组织通常发展为四级或更多等级的地区性聚落,而这又意味着三级或更多等级的行政管理机构的出现。通过对考古资料的考察,该书认为在二里头文化中社会等级已经出现,集权的、专门化的政府已经产生,四级聚落已经形成。因此,对照“国家”的标准,可以认为二里头国家业已形成。在这里,同样是先对“国家”做出了界定。
其实不只是“国家”,其他如“酋邦”、“复杂社会”等与国家产生与形成相关的表述社会发展阶段的一系列概念也莫不如此,它们都是先验的。如果缺少了先验的概念,很多科学研究是无从进行的。
在考古学的很多具体研究中,研究的对象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物。我们可以借助科学的方法、理论和逻辑推导对这些物进行系统的观察并得出解释。此外,还有很多事物是不能直接观察到的,所以随着考古学对自然科学方法的运用,不同类型的考古材料被带入实验室,许多本不能从实物中直接观察到的事物由此可以从实验中获得。但是还有很多考古学所希望获得的知识并不来自观察和实验,本文讨论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国家”就是一个例子。我认为如果要探讨诸如此类的问题,经验是不够的,考古学还需要同其他的人文学科相结合。至少,考古学离不开思辨。
来源:《考古》2005年第9期
王巍: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展示辉煌中华文明
我要新鲜事2023-05-07 10:26:460000许永杰:史前三种重要的粮食加工工具
史前时期,先民们是如何加工粮食的?加工粮食用的是什么工具?考古学家们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了答案:石磨盘和石磨棒、杵和臼、擂钵这三套组合是史前粮食加工的主流工具,有些甚至使用至今。在距今7000年前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过88个储存有粮食的窖穴,所存储的谷物以十万计。如此多谷物,磁山先民是怎样吃的?我要新鲜事2023-05-26 16:28:060000考古专家发现了一件织锦,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伟大发现之一
谈起精绝国,相信许多人都未必知道这个国家的历史,可能还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只存在于神话小说中的国家。其实不然,精绝国是我国西汉时期中国西部的一个比较弱小的城邦国家。大致位置处于尼雅河畔的一处绿洲之上。该国主要以农业为主,是当时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我要新鲜事2023-05-16 19:40:440000国军大墓顶挖防空洞,考古人员坑底拾到玉衣片,得出重要考古发现
东汉灵帝文陵考古调查本文作者倪方六这篇“梧桐树下戏凤凰”头条号,来说一个座皇帝陵。其陵主可以说既幸运,又倒霉。幸运的是生前,他不是皇子,却被选中当了皇帝。倒霉的是死后下葬不久,朝代还未灭亡呢,墓中随葬品就被盗出了。这位皇帝叫刘宏,是汉桓帝刘志的接班人。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正月庚子,刘宏即皇帝位,史称“汉灵帝”——东汉第11位、倒数第3位皇帝。我要新鲜事2023-05-26 17:40:4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