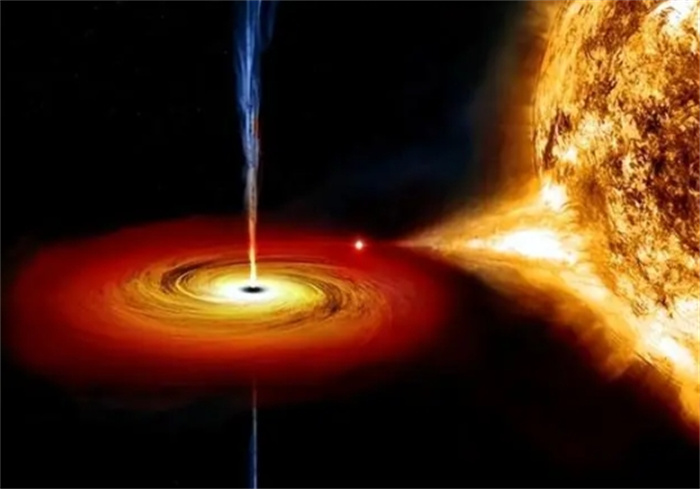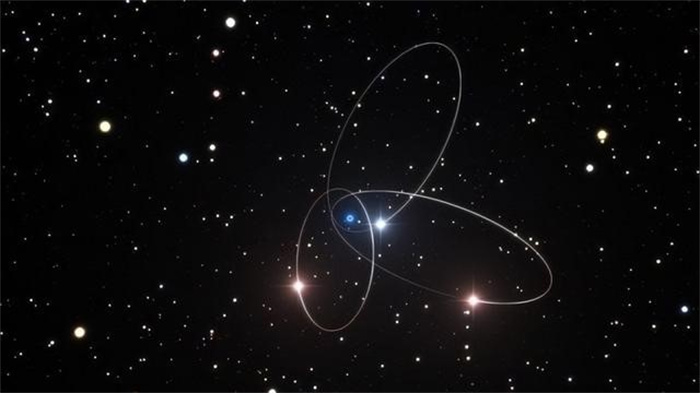雷戈:社会转型与史学变革
一
人们公认,中国目前的社会正处于史无前例的转型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人文科学的“龙头”——历史学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而且,危机一直持续至今。于是,在“史学危机”余音袅袅的氛围中,人们又合乎情理地提出了“史学改革”的呼声。对此,学者们的普遍看法是:一方面,史学与社会脱节了,即史学越来越无法满足社会转型期所提出来的多种多样的复杂需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阶段,社会本身对史学研究的需求量必然是趋于越来越小。
这两方面因素结合起来,就只能使人们认为:史学除了忍受冷落,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也就是说,在社会转型期,史学的社会功能只能是一句无法落实的“空话”,史学的学术功能更是一句不着边际的“大话”。而“大话”加“空话”似乎向来就是史学语言基本风格。只不过,这种传统风格在目前的社会转型期的新形势下遇到了未曾预料到的有力质疑和全面挑战。
因为社会转型期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是一个痛苦而又复杂的过程,它排斥一切虚假和空洞。而惯于“弃虚作假”的历史学便第一次碰上了这个转型期的社会“克星”。可以说,历史学的千年辉煌至些才算正式终结,历史学的不朽盛世至此才算正式结束,历史学的喜剧至此才算落下帷幕,历史学的历史至此才算划上句号。在此之前,历史学一直以“学界老大”的身份自居,自恃甚高,甚至一度还自诩为“唯一的社会科学”。而社会转型期的特点是:根本不理睬历史学的虚张声势和陈腐说教,而专注于那些最能为社会改革提供直接而有效帮助的科学知识。
社会不会再为自己的未来与出路,去不耻下问地求教于历史学的训示和指导。曾几何时的繁荣变成了现时的冷落,车水马龙的热闹变成了门可罗雀的寂寞。众星捧月的得意变成了无人问津的屈辱。惯于记忆的历史学现在再也不愿轻易回忆什么。昨天还得宠于政治和权力,今天却被毫不怜惜地跑向市场和商业。风光几千年的历史学,诚然是老大不小了。可谁能想到,垂垂暮年的历史学竟然又要改换门庭,别投新主,落到这般田地。中国历史的传统之一就是“重义轻利”,保国历史学更是把这一传统推崇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
所以,“二十四史”对道德作用的夸张和吹嘘绝对要远远超过对实际利益的认真分析。从不言利的历史学今天不得不要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奔走呼号,耻于言利的历史学今天不得不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四处钻营了。以言义始,以求利终,这莫非就是历史学的命运?这难道就是历史学的福祉?从衮衮荣耀沦为可怜兮兮的历史学什么滋味都有,又什么滋味都是感觉不出来。这就是麻木(这也被称为“史学危机”。尽管这只是史学危机的一部分内容或一种表现)。当然,这种麻木是暂时性的、间歇性的、阵发性的。
尽管如此,它依然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它在理论上包含有这样一个逻辑。这个逻辑就是:史学危机(也就是史学研究这门职业的不景气)主要是由社会造成的,而这个社会又处于非常时期,一旦社会走上正轨,恢复常态,即社会转型期完成之后,就会为历史学的发展与繁荣提供充分的条件。基于这个逻辑,人们乐观地预言,现在的社会不是历史学大显身手的场所,只有等到社会转型期基本完成之后,社会才会重新对历史学产生大规模的需求,到那个时候,历史学才能东山再起,一展宏图。因为新的社会结构将会对历史学提出新的要求,同时,新的社会秩序也能为历史研究提供充足的物质资助。这样,历史学就可以立足于新的社会基础去全面发挥自己的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去总结人类的全部经验,去重新探索历史的所有规律。而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是顾不上照顾和保护历史学了。
在这里,我不想过多批评这个看法的局限与片面,而只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即,我试图提出这样三个问题,那就是:第一,在社会转型期中,史学与社会的联系是更紧密了,还是更松散了?第二,史学应对社会转型持什么态度?社会应对史学变革提出什么要求?第三,社会转型期能给史学变革提供什么帮助?史学变革又能给社会转型提供什么帮助?
提出这三个问题,就意味着要求历史学必须彻底转换自己的认识视角和观念维度,学会适应社会,也就是学会适应生存。“适者生存”,这个大自然的进化原则,对人类社会不例外,对科学知识也不例外,对研究人类社会进化与发展的历史学更不例外。如果历史学不能很快地做到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那么,历史学就必然要被转型期的社会所淘汰。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如果意识不到它的严重性,依然沉溺于幼稚可笑的想入非非之中,把转型之后的社会误认为是历史学的又一个“黄金时代”,是历史学的“天堂”,是历史学的“福音”,就未免太煞风景了。所以,全面认识史学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是重建史学观,也就是建立新的史学观的一项重要任务。
下面我们就按照刚才提出的三个问题来依次展开分析。
二
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可以简洁地归结为:史学必须不断调整自己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种调整就意味着,史学必须善于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尽快找到自己的社会位置,必须彻底弄清自己的社会角色。就现实而言,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是变得越来越松散了。这反倒为史学回归自我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因为,在相对松弛的状态下,历史学不应该放松对自身的全方位思考,而应该抓住机遇去更深入地思考自身的本质与基础。
在此之前,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很奇特很不正常的。它主要表现在:史学一直忙于应付越来越急迫的政治要求,而根本无暇顾及对史学自身本质的反思与批判。而且,在那种政治高于一切,政治压倒一切,政治就是一切的时代,还根本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所谓“社会”只能是政治的外壳和形式。社会只有一种功能,那就是政治功能。社会只能是政治社会、政治化的社会。由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社会,故而史学就不可能与社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社会只是依附于政治而与史学之间发生某种极为有限的关系。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主要通过史学与政治的关系表现出来,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只是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的一部分。
由于在社会转型之前,中国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故而那个时候所谓的史学的“社会功能”,只不过是政治功能的放大或扩张。这样,由于政治的高压和强制,史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就是一个空白。所以,根本谈不上史学对社会有用还是没用,只能说史学对政治有用还是没用。在这个历史意义上,所谓社会转型本质上就是社会独立。所谓社会独立,本质上就是社会独立于政治,就是社会从政治独立出来,这意味着中国开始形成了一个不受政治绝对控制的开放社会。这个开放社会比单一化的政治社会更有活力,更有影响,更能改变现实事物的方方面面。
其中,历史学就是受到这一开放社会影响的事物之一。以前,没有完全自主的社会,社会对史学也就说不上有什么要求,而史学也根本不必考虑社会的需要,史学只服从政治的安排,只按照政治的指示去研究历史。现在,社会转型使社会产生了独立的要求,这种社会要求可以说是全新的,它完全不同于社会转型之前那种一统式的政治要求。简单地说,社会要求较之于政治要求更广泛,更灵活,更松散,更多样化,更少强制性。
不过,由于中国目前的社会在独立伊始就进入了一个急需转型的阶段,就使社会本身变得更加复杂和窘迫。社会从依附于政治变为独立于政治,从政治社会变为非政治社会,这就决定了社会转型的特点是非政治化。非政治化就是多元化、自主化和市场化。对于目前阶段来说,市场化在社会转型中表现得最为集中和突出,似乎社会转型就意味着要把社会弄成一个大市场。社会转型的目的和方向诚然是要建立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并不等于市场就能(所有权)主宰一切。
至少,历史学就不应该心甘情愿地去接受市场的全权统治。如果这样的话,历史学的处境和社会转型之前又有什么区别呢?与其受市场的金钱奴役,不如受政治的权力奴役。所以,史学必须对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全盘市场化”倾向予以坚决拒绝和严肃批判。因为这不单单涉及到历史学目前的危机处境,而且更关系到历史学未来的发展命运。事实上,史学危机就是在无法选择状态下产生的被迫选择。完全依附政治和完全依附市场,都不可取,也都不现实。就其本质而言,完全依附政治和完全依附市场,没有什么不同,都是缺乏自主性的表现。如果历史学不想这么做,而又在没有更好地选择的情况下,就会必然产生困惑。片面依附政治的弊端,历史学家们已经看到了,但片面依附市场的痛苦,他们又实在难以承受。这就自然产生了变革史学的要求。
这种要求的实质既不是要回归政治,也不是要投靠市场,而是要立足自身、走向自身、完善自身、创造自身。总之,它是要求历史学在政治与市场之间寻找一条独立的途径,以确保史学的自主和自由。这样,史学的自我意识就诞生了。史学意识的诞生,为新史学观的形成创造了一个根本的可能,而这一可能恰恰是在社会转型期中产生出来的。这就直接涉及到史学与社会的本质关系,这个关系只能是互动的、多元的、自由的。从形式上看,史学与社会转型期的关系较之于史学与社会转型之前的社会(实际上是政治)即政治社会的关系,无疑是松散多了、开放多了。这种松散的开放的关系就为史学在多元选择中确立自己的本质与基础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正因为如此,社会转型对历史学的正面影响要远大于负面影响,积极作用要远大于消极作用,有利因素要远多于不利因素。
三
社会转型是一次社会解放和社会革命,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但这些影响又不是一时半刻就能看出来的。至少,人们还不可能完全从正面的角度去看待这些变化和认识这些变化。由于传统的束缚和习惯的偏见,乃至一些习以为常的职业性观念,都会严重影响人们对社会转型的革命性和进步性作出公正的评价和深刻的理解。所以,史学界的一些人对社会转型总是持一种观望、等待的保守态度。他们要么怨声载道,要么杞人忧天,仿佛历史学天生就只能享受政治社会的重用,而不能接受开放社会的冷遇。
历史学总是要求转型中的社会为自己做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一旦社会不做,或做不到,历史学家就会牢骚满腹地抱怨社会的歧视与偏见,就会怒气冲冲地指责社会的堕落和愚昧。历史学诚然有理由质问社会为什么不重用自己,但社会更有理由质问历史学对社会究竟有什么用处。当然,这种笔墨官司毫无任何实质意义,它只能耗费人们的精力,而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所以,历史学不应问转型期的社会能为自己做些什么,而要问自己能为社会转型做些什么,即历史学不应消极地等待社会转型期的完成,而应积极地参与社会的转型。
只有这样,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史学才能获得社会的依赖和尊重,才能成为有社会影响和社会价值的知识形态。这就要求历史学必须抓住社会转型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加速实现自身的彻底变革。这次史学变革是把史学从政治附庸状态解放出来的伟大理性运动,它要求史学必须由过去那种对政治的辩护转变为对社会的服务,必须由过去对政治社会的效忠转变为对开放社会的批判。这不仅是史学观的深刻革命,而且也是史学职能的深刻革命。
历史学必须抓住这次机遇,借助于社会转型的强大推动力和刺激,从里到外地使自己变成一个新的体系,具有一种新的形式,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新史学。如果失去这次机遇,历史学本身所固有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情结将永远无法得到根除,历史学将永远无法获得自立的本质力量,历史学将永远无法成长为一种感人的人文精神,历史学将只能屈服于市场的强大压力而丧失自身的学术品格和批判价值。这样,历史学就会患上“软骨病”,永远无法堂堂正正地站立在政治与市场之间,成为具有自由思想和独立意志的第三种存在。辩证地看,史学变革与社会转型应该是同步性的。
因为,正像社会转型的本质是从对政治的依附转变为社会的自主,从政治社会转变为开放社会一样,史学变革的本质也是从对政治的附庸转变为史学的自立,从政治史学转变为批判史学。基于这个判断,我认为,历史学绝对没有理由去消极地等待社会转型完成之后,再来实现自身的变革。因为,如果不与社会转型同步,如果没有社会转型,历史学的变革就必然缺少一个来自于现实社会的强大动力。
这就要求历史学必须对社会转型采取一种全面参与的积极立场,这样做不仅是为了社会,而且也是为了史学,因为史学变革与社会转型已成为利益相关的统一体。在参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历史学也将获得自己的内在本质。也可以说,真正的史学变革(只能)从社会转型开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对于史学变革非但不是某种外在的限制,反而构成一种内在的需要。它意味着,彻底的史学变革只有在社会转型中才能进行,因而历史学只有在全面认识社会转型的本质之后,才能充分理解自己的本质。
只有通过这种理解,历史学才能建构起一种新的理性史学观,历史学才能合理摆正自己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社会是历史学的认识对象,也是历史学的服务对象。当然,这种“服务”决不是“投其所好”式地满足社会转型中所产生的形形色色的庸俗需要,而是一种批判性的审视,它意味着史学需要社会,但并不依附社会。这就是说,史学需要服务社会,但不是无条件的、无原则的,史学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考虑,史学依据自身的理性准则去为社会提供服务。毫无疑问,这种服务正是史学有目的有意识地影响社会发展的一部分,这种影响越大,社会就越是需要史学。
诚然,一旦社会迫切需要史学的帮助时,它就会主动地给历史学提供相应的条件和便利,以作为对史学工作的支持和回报。因为,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其实,任何社会都是这样,即便社会在转型完成之后也是这样),首先考虑的只能是利益原则,利益总是第一。社会不会不考虑利益的实际需要而去盲目为史学投资或赞助,社会永远都是现实的。社会只有在有所求的情况下,才会有所予,社会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地给予史学什么。社会给予史学什么,其目的就是希望从史学那里得到些什么,双方是互惠互利的关系,也是相互利用的关系,谁也谈不上高尚或卑鄙、慷慨或自私,双方都是受到利益的驱使而走到一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双方的这种利益关系实际上就像一种契约,当然这种契约是在双方的长期合作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它对双方都构成一种约束和压力。
所以,当史学要求社会为自己提供丰厚的物质条件时,它必须首先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在任何时候,片面要求社会来为史学做什么事情,都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理的。这就要求史学必须自立,必须在社会转型中实现自身的彻底变革,必须与社会保持平等和独立,必须摆脱对社会的依附和乞求。史学必须走向自身,但走向自身不是不关心社会,而是力求摆脱社会的物质束缚。因为,就其本质而言,史学对社会总有一种潜在的反抗欲望和造反冲动。史学像任何一种精神活动一样,永远不会满足现状,对现状的质疑与批判正是史学独立于社会的根据与标志。
这就决定了史学在同社会合作的过程中,也不会忘记自己的存在与本质。我相信,社会转型与史学变革一旦构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合作关系时,史学危机就有可能得到缓解和消除。同时,我也非常清楚,史学危机的产生不是一朝一夕,史学危机的消失更非一朝一夕,史学危机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对历史学家的忍耐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也是对历史学局限性的一次全面曝光。
总之,史学危机只有通过史学变革才能得到克服,而史学变革只有在社会转型中才能有效进行。因为社会转型给历史学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弹性的生存活动空间,它较之于政治社会对历史学进行的僵硬限制,无疑要更为开通和文明一些。基于此,历史学对社会转型必然抱以赞成和支持的态度,并以自己的方式去关心和思考这场旷古未遇的社会革命。一旦史学做到了这一点,那么社会就决无任何理由去拒绝史学的热忱与厚爱。
四
诚如前面所说,社会转型是一次深刻而又全面的社会革命,它涉及到社会整个结构的转换,它所产生的问题之多,内容之广泛,都是史无前例的。这就为史学认识社会、研究社会,提供了一个深远的背景。由于社会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全方位的开放状态,使得历史学有可能深入到社会内部去对社会结构加以系统和细致的观察和分析,这对史学是非常有利的。而这个有利条件也是极其罕见的,只有在历史上的某些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才会出现类似这种情况,这就为历史学的创造性和批判性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推动和有力的启示。
社会转型迫切要求历史学去思考新的问题,去研究新的问题,这对历史学变革自身的思维定势和传统观念是很有好处的。它促使历史学从现实社会吸取灵感,发现矛盾,使历史学的研究更富时代气息。同时,历史学依据社会转型提出的新课题和新要求,去研究历史,就会对历史作出迥然不同于传统的新解释新认识。所以,历史学的变革得益于社会转型之处甚多,尽管有时这种益处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是思想的、而非物质的,但对于历史学来说,社会转型所提供的思想帮助比物质援助更有价值,它对历史学的自身建设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精神启示,它要求历史学必须保持一种独立的姿态去对社会加以思考,它要求历史学必须以全面批判的立场去对社会的整体加以深刻认识。
比如,社会转型要建立市场经济,这就要求历史学必须对中国历史上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作出新的解释,必须对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的发展、特点以及为何迟迟没有产生出近代资本主义进行新的分析;同时,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这就要求历史学必须对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体系的构成、功能、本质、影响进行全面研究,并分析中国古代的法律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正负面作用,分析中国历史上法律与经济之间的复杂联系,分析中国古代法律对中国历史停滞不前所起到的帮凶作用。
又如,在社会转型期,人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公德”还是“私德”,都与以往大不相同。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己”,人们都有意识地同传统拉开距离,要么干脆是赤裸裸地反叛传统。这种社会现实无疑对历史学有着极大的刺激和启示,它要求历史学必须善于把这种社会现象同历史联系起来加以综合认识,它要求历史学必须面对社会转型的现实道德状况,去对历史上的道德价值与特性进行认真分析;它要求全面评估历史上的道德作用;它要求重新探讨道德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具体影响;它要求从道德角度去思考为什么中国社会迟迟没有发展到现代文明阶段;它要求历史学必须从社会转型的实际需要出发,尽可能地从古代道德传统中开发出可供现代人选择和利用的伦理资源;它要求历史学必须把道德水准同经济水准结合起来统一思考,是否经济的发展一定要以道德的退步为其必然代价,是否道德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之间永远是不平衡的、不同步的,是否道德与社会之间只能构成一种紧张的对峙,是否社会与道德之间的二律背反必然构成一个历史规律。
再如,社会转型期频繁出现的大面积的深层次的数量惊人的政府腐败现象,不能不引起历史学的严肃思考,且历史学的这种思考还不是局限于一时一地的思考,而是放眼整个历史的通盘思考,并通过对历史上的各种腐败现象的科学研究,来剖析社会转型期中腐败现象的历史根源。这样的历史研究才是一种深度的历史研究。
综上所述,社会转型实在是为历史研究打开了一道观察社会、洞察未来的天然门户。透过它,历史学有可能看到在此之前,即社会转型之前根本无法看到的种种现象、事实和秘密。这无疑有助于健全历史学家的心智,提高他对社会转型中产生的种种丑恶现象和巨大痛苦所必须具有的心理承受能力。事实上,社会转型有可能使历史学家变得成熟起来,而不再轻信什么和迷信什么。在此之前,历史学家对政治社会的过分轻信和狂热迷信往往正是导致历史研究陷入危机的重要原因。历史学家一旦理智起来,就会自觉划清史学与社会之间的界限,就会立足史学去批判社会,就会用历史科学的实实在在的研究成果去贡献于社会,以使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社会受到深刻的教益。
史学变革要想着手进行,就必须首先建立新的理性史学观。有了理性史学观,历史学与社会转型之间的界限就有了一个本体论的可靠依据,历史学就可以在自己的天地里大显身手,大胆探索,社会对史学就不再是一种威胁和障碍,而成为一条开放的通道。历史学顺着这条通道,就能走近历史,就能走进历史深处。在历史深处,历史学所作出的种种研究,无论是关于政治的,还是关于经济的;无论是关于文化的,还是关于自然的;无论是关于个人的,还是关于群体的;不管是对一朝一代的研究,还是对一草一木的研究;不管是对文明兴衰的研究,还是对生态演化的分析,都足以对社会转型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因为这是从历史深处发出的轰鸣和回响,而这轰鸣和回响则是由历史学传播出来的。所以,尽管表面上看,历史学全神贯注地集中于对历史的探索,但这种探索却依据于两个前提:一是史学自身的独立,二是社会本身的独立。社会的独立是独立于政治,史学的独立则是既独立于政治,又独立于社会。有了这两个基本前提,历史学的任何研究都必然具有一种内在的纯粹性,而这一纯粹性恰恰是史学满足社会需要的最好证明。
来源:《学术月刊》1997年第1期
禄丰龙:亚洲出土的唯一板龙科恐龙化石(体长6米)
禄丰龙是一种原蜥脚类的板龙科恐龙,体长只有6-7米,诞生于1.9亿年前的侏罗纪初期,第一批化石是在中国云南省禄丰县发现的,因此才以此得名。禄丰龙的化石中发现了一块罕见的保有蛋白质的恐龙化石,其中血管和神经都能够看到。禄丰龙的体型我要新鲜事2023-05-09 10:29:360001空地找到一口红色棺材 左青龙右白虎守护(送礼阎王)
墓主人给阎王带来财宝希望安排个好去处。2012年,江苏一挖掘机工人挖土时无意间挖出一口红色棺材,闻讯赶来的考古队立即对棺木进行抢救性发掘,血红色的棺材崭新的就像刚刚下葬一般。随后经过初步判断,发现棺材保存的十分完好,未被盗墓贼盗掘过,这让在场的考古专家异常兴奋。因为他们推测里面肯定有很多宝贝陪葬。左青龙右白虎我要新鲜事2023-10-20 20:44:390002【考古词条】铁器时代 · 三门峡栈道遗迹
东汉至北宋在黄河三门峡地段修造的栈道、人工航道、粮仓等遗迹。分布在今河南省陕县三门峡市境内。黄河三门峡地段河床窄而水流急湍,航运艰险。汉至北宋,特别在唐代,为使关东漕粮渡此险阻而安抵关中,在此修治栈道,凿开元新河,修筑北岸18里陆道及在两端修建粮仓。1955~1957年,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勘查、纪录了这些遗迹。这是研究三门峡漕运历史和汉唐时期工程技术的重要资料。我要新鲜事2023-05-26 00:19:490001海外国宝:卡尔霍恩在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藏品
至1909年,博物馆对中国艺术的收藏日趋专业。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威廉·詹姆斯·卡尔霍恩(WilliamJamesCalhoun,公元1848~1916年)曾为芝加哥律师,大使夫人露西·门罗·卡尔霍恩(LucyMonroeCalhoun,公元1865~1950年)曾任芝加哥报艺术评论家。我要新鲜事2023-05-28 01:57:160001盗墓者在江苏徐州一座山上准确找到贵族墓,他们咋知这里有墓的?
“秦埋岭,汉墓坡”本文作者倪方六盗墓贼中有一句口头语,叫“秦埋岭,汉墓坡”。这是盗墓贼长期盗墓活动的一个总结,与古代葬俗和现代考古发现的情况相当吻合。这种“葬山不葬顶,埋坡不埋岭”的汉代葬俗,一直影响到现在。在民国盗墓活跃地区之一的湖南长沙,这一带的土夫子便对当地各个朝代葬俗相当熟悉,并用之指导盗墓,上面说的蔡姓盗墓高人就是其中之一。我要新鲜事2023-05-27 11:34:120000